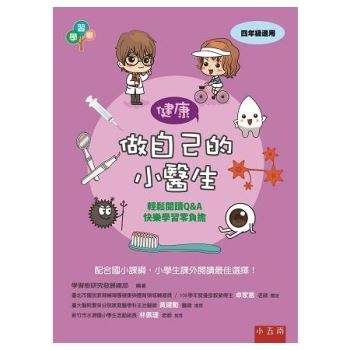本書由探討三組環環相扣的議題組成:首先,英美國家的人文研究何以發展出目前這種書寫模式?其次,特別是面對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更廣大的跨文化交流與交織的影響,我們應如何評價這種書寫模式?再者,當我們把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與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這些看似各自獨立,然而發展過程都和戰後北美(尤其是美國)息息相關的學術領域放在一起討論,能夠獲得什麼啟示?
所謂「書寫模式」指的是後結構主義理論興起之後,帶動了使用批判語言書寫的趨勢,不僅在文學研究領域蔚為風潮,在史學、哲學、電影研究、性別研究與文化研究等其他人文學科也明顯可見。這種批判書寫迥異於報導性質刊物與其他大眾出版品中通俗易讀的文章。因此,非人文學科(以及不贊成這種書寫的人文主義者)經常嘲笑和輕視我們這些受到後結構主義理論影響的人文學科研究者,認為我們的書寫中充斥著艱澀、隱晦又難懂的語彙、句法和迂迴論證。不過,至少對某些學者來說(當然包括筆者在內),放棄清晰愉快的理想溝通方式,轉而採取這種難以理解的書寫策略,與其說是仿效時下流行的學術寫作風格,不如說是為了自我防衛,不得不在我們與世界之間劃出一條界線。
文學的自我指涉性(或自我監禁〔self-incarceration〕)的出現,是現代時期語言地位遭到「貶抑」的結果,可以理解成某種外在性功能的展現,造成某些(批判和創作)書寫上的封閉,這個封閉的空間裡只住了瘋人與詩人,(也許還可以加上)後結構主義理論家,至於監禁本身只是次要結果。德勒茲進一步指出:「在傅柯論述中,沒有什麼是真正關閉的」; 問題在於重新開啟或揭露文學的語言轉向,正如傅柯自己曾經說過:「自我封閉於一種徹底的不及物性。」才是問題所在。
後結構主義理論的措辭使現代性下的語言與意指作用從此無法擺脫自我指涉的烙印,而自我指涉性似乎也成為西方思想史發展必然的結果與困境。所謂的必然,指的是必須藉由某些語言與意義模式來扺抗現代工具主義與科層化現象的侵害與收編;至於困境,則是因為反抗這種明目張膽的自我擴張與自利傾向似乎徒然無功,例如,跨文化交流往往是在根本欠缺公平的前提之下進行。然而,除了上述這個難題,我們還要進一步思索,後結構主義理論究竟有哪些論點至今仍然是有用與適用的?是否有一種自我意識能夠(不只是為了批判壓迫勢力)不斷地像傅柯所(誤)認的「文學本身」那樣自我皺摺,發展出帶有自我指涉、自我監禁性質的非溝通語言(non-communicative language)?第二章〈指涉性的中斷〉中討論這些問題,並且簡短回顧「後結構主義的誕生」這件學界大事的幾個重要轉折:例如,後結構主義如何進行(卻未完成)小布爾喬亞階級(petty bourgeois)的大眾文化分析?後結構主義如何改變與深化我們長期以來處理「文學性」等問題的方式,並且提供了關切弱勢文化與身分議題的學者豐富卻自相矛盾的討論方向?此外,作者還會特別探討後結構主義理論最有影響力卻也最具爭議性的貢獻,也就是對所謂的指涉性存而不論。
作者簡介
周蕾(Rey Chow)
出生於香港,在美國史丹福大學先後獲得碩士、博士學位,曾任教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現為美國布朗大學Andrew Mellon人文學講座教授,為華裔文化研究領域最重要的學者之一。研究領域為:現代中國文學、當代女性主義理論、中國電影、後殖民理論及文化研究。
譯者簡介
陳衍秀
交通大學語言與文化研究所碩士,擅於英語教學,文化研究,中英筆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