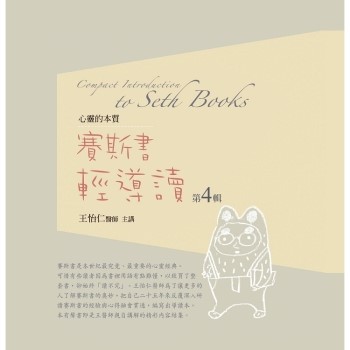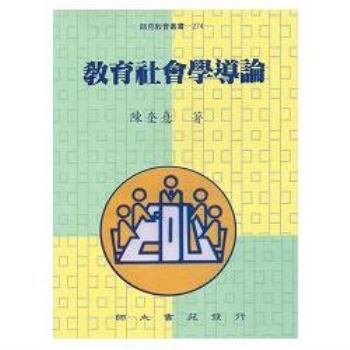第一章
我從小就不聰明。不是天資差智商低,而是思考慢、反應慢、做事慢,因為這三慢的緣故,經常吃了虧不知道,等想清楚了,一肚子委屈無處可訴,於是大發脾氣,但早已事過境遷。這種不在該發脾氣的時間發脾氣的紀錄多了,就更顯得我個性暴躁、倔強古怪。
但我媽說,我不是不聰明,只是不愛用腦袋。
我媽的言外之音就是──笨是妳自己的問題,和生妳的我沒有任何關係。
更簡單的意思就是,她在撇清。
等我想通了這句話明喻暗喻之間的關係後,我就知道,我不聰明的問題,歸根就底算起來,和我媽大有關係,不但有關係,搞不好就是她害我這麼不聰明。做賊的永遠喊得比捉賊的還大聲。
我分析得頭頭是道,但我媽每次一聽我說什麼頭頭是道的話,就會大發脾氣,這次也不例外。她直接提著菜刀從廚房裡氣勢洶洶地奔出來,我爸看情況不妙,趕緊飛撲到我身前,肉身相護,陪著笑臉勸說:「別生氣,小孩子說話不知輕重,妳千萬別跟她認真!消消氣,我幫妳切菜洗碗!」
我媽對我爸的態度比對我還差,理都不理,指著我怒吼,「程秀翎,妳給老娘說清楚,誰害妳了?誰讓妳不聰明了?不聰明是妳自己的問題,和妳媽有什麼關係?啊!」
我本是那種在逆境中更顯堅強的人,但看我媽氣勢雄渾地撲出來,一副要拿菜刀把我大卸八塊的樣子,一時英雄氣短,嚇得說不出話,再看我爸擋在前頭,知道要死死他絕不會死我,膽子就像吹氣球一樣地又膨脹了起來,扯著嗓門喊回去,「妳不每次都和人家說,自己很聰明,卻生了我這麼笨的女兒?我就覺得,那是妳的問題。一定是我在妳肚子裡的時候,妳把我的智商吸收走了,所以我才笨,妳才聰明!」
我媽聽了,手抖了半天。
我媽常常抖,每次我爸拿著百貨公司的袋子問她「這鞋子買了多少錢」時,我媽都得或大或小地渾身抖一下。
我雖然氣她吸收了我的智商,但媽媽畢竟是媽媽,我還是愛她的,看她這樣,我有點不忍,發自內心的關心。「媽,妳要冷的話,多穿件衣服,要是中風,我跟爸爸送妳去醫院?」
她聽了這話,菜刀「噹」地一聲掉在地上,狠瞪我一眼,掉頭就走,一面走一面罵,「生妳還不如生隻豬!」
媽走開了,爸過來把菜刀撿起來,對我低聲說:「翎翎,怎麼這樣跟妳媽媽說話呢?妳媽媽她那麼愛妳,好的東西都給妳,怎麼會害妳?妳這樣讓媽媽傷心,很不好啊。」
我是不聰明,但也並不傻,該知道的事情我都是知道的,譬如說我知道,媽媽雖然老拿指頭戳著我的腦袋罵「妳怎麼那麼笨啊」,但晚餐桌上的炸肉排,我總是吃最大塊的,如果我吃得很香,我媽還會把她的那塊夾到我碗裡來。
我在百貨公司裡看到一件好幾千塊的專櫃童裝,看得眼睛發直不肯走,逼得我媽和櫃姐殺價。她指著我說:「妳這件衣服穿在我女兒身上像條破抹布,要不是她眼光爛,老娘還不屑買!」
我愛吃糖果,蛀得一嘴爛牙,看牙醫時嚇得鬼哭神號,我媽在一旁對醫生吼,「你給我好好治她這嘴牙!我家翎翎人笨已經沒藥醫,但牙齒壞了,臉垮了,以後嫁不出去,我拆了你這家爛牙科!」
很奇怪,仔細想想,我媽愛我和作賤我總是同步進行,但我心寬人善,總記得好事,壞事就當成是周董含糊的副歌,聽久了,就算不明白,也都順耳了。
我把過去的回憶百轉千回地想過一遍,自己感動自己、自己譴責自己,最後,含著眼淚跟我爸懺悔,「我真不應該。」
家父乃鐵血漢子、性情中人,平生最見不得眼淚,尤其是女兒的眼淚。在感動和父愛中他混亂了心智,沒跟我把話對過一遍,衝動地推著我說:「那趕快去跟妳媽媽道歉去。」
我進了廚房,看見我媽在那邊開著水嘩啦啦地洗白菜葉子,眼角已經瞥見了我,但一聲不吭。
我清一下嗓子,她洗一片葉子。
我靠近一步,她把青菜瀝了水。
最後我扯扯她的衣角,她把水關了,轉過頭來看我。
我低頭認錯,「媽媽,妳不要生氣了,都是翎翎不乖不聽話,我真不應該。」
媽咬著嘴唇不說話。
說軟話還不夠力,只得使出絕招求她,「我知道媽媽最愛我的,妳生我的氣,我就難過了,難過我就要哭了,就不吃晚飯,要生病了。」
我媽狠狠地「哼」了一聲,鼻音特別重,「妳媽煮的飯妳敢不吃?還敢生病?生了病妳就得去看醫生打針了!」
我媽就是這樣,嘴巴很惡毒,但心其實很軟,她肯對我說話,就表示雨過天青了。
我轉過頭去看看,爸躲在門邊對我偷笑。
我放下了心,還黏著我媽問東問西,突然想起什麼,又扯了一下她的衣襬。
我說:「媽、媽,妳剛剛說錯話了妳知道不知道?」
我媽好脾氣地問:「說錯了什麼話?」
我說:「妳說生我還不如生條豬,可是,人生的是人,豬才生豬,人是生不出豬來的,除非有例外。」
我媽一愣,「什麼例外?」
我指著她說:「除非妳是隻豬。」
那天晚上,我就因為那句衝口而出的真心話,沒能吃到一口晚飯。
這件事情過去十幾年後的某一天,我把它講給杜子泉聽。
那時候的他正在繪圖教室裡,燃燒他的熱血青春,用一把美工刀對著一堆紙頭割啊劃啊的,做他那據說50:1的立體建築模型圖,而我則在旁邊看武俠小說。
起初我不吵他,但等看完喬峰死去,阿紫抱著他跌入萬丈深谷的那一段,心神激盪,抬頭一看,只見窗外午後陽光正好,青春正燦爛,江湖上人間烽火,而我們卻蹲在教室裡對著模型消磨大好時光……他消耗他的也就罷了,居然連我也得跟著消耗,怎麼想,都很冤。
我推了他一把,「杜子泉,我講個故事給你聽好不好?」
他抬頭看了我一眼。就一眼,絕不多,也不少,然後又別過臉去,不吭聲。
別人怎麼解讀那一眼的意思,我不知道,但在我來看,我就覺得那是他默許我可以繼續說下去的意思。
我於是把陳年舊事挖出來開講,加油添醋一番,說得很熱鬧,說完以後,自己笑了半天,又推他問:「喂,你說好不好笑?」
他給我的回應,就是又抬頭瞟我一眼。
我雖然成績不好,但並不是個看不懂人臉色的孩子。杜子泉的那一眼,什麼意思,不語自明,我心中立刻聯想到的就是喬峰對阿紫的態度。
掏心挖肺,卻被喜歡的人冷淡,難怪阿紫會變態!
我內心長吁短嘆,正在思考該去哪弄點毒針把杜子泉的眼睛戳瞎,看能不能讓他變成游坦之?忽然聽見隔壁拋出一句話,只有三個字。
「然後呢?」
我趕緊看他,確信這三個字和問號都是從杜子泉的嘴裡吐出來的,不是我腦中過度妄想製造出來的幻聽,心裡立刻生出一種莫名的幸福感。
啊哈,你可理我了!
「沒有然後了,然後故事就結束了。」
「我不是說這個,」他耐心地引導,「我是說,然後妳從這件事情上面得到了什麼教訓?」
我想了想,試探地丟出答案,「真心話總是最傷人?」
他搖頭,手上的美工刀推推退退,發出「咑咑咑」的聲響。
我問:「最愛的人總是傷我最深?」
還搖頭。
我說:「不要對媽媽的氣話認真?」
繼續搖頭。
我不耐煩了,用力一推,把桌上的那些個紙片都掃到地上去。「我想不出來。這就一個過去的故事,又不是牛頓的蘋果,你配合我笑一笑也就完了,有什麼好想的。」
杜子泉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地上散落的紙片,不吭聲,不說話,臉上陰惻惻的,真可怕。
他的臉在平常,從任何角度、什麼時候看,都很保養眼睛,但一沉下來,就像妖魔鬼怪一樣陰森森的可怕。
我惡人無膽,趕緊彎到桌下去把紙片都撿了起來,拂去灰塵,一張一張排好,恭恭敬敬地雙手奉呈上去。
杜子泉把東西接過,放到一邊,臉上恢復如常面色,又陷入他的模型製作,又不理我了。
我有些不甘心。口沫橫飛地說了童年的糗事給他聽,最後只得到這傢伙威嚇的一眼……我悲傷地想,我此生當不成阿朱,但距離阿紫卻已不遠矣。
好在杜子泉還沒這麼沒人性,擺弄了一會兒他的建築模型後,又想到了我們未完的對話,轉過臉來看我。
「這個故事的教訓就是告訴妳:該閉嘴的時候,不要多話。程秀翎,妳話很多妳知不知道?」他說完,對我做出一個拉上嘴巴拉鍊,外加掐脖子的威脅性動作。
我看著窗外的陽光,對於這個結果,默默地想了半天。
最後我想通了,得到了一個重要的結論:其實,一切都是錯覺。
杜子泉從來就不是喬峰,而我既不是阿朱,更不是阿紫。他才是阿紫,而我就是喜歡阿紫那個變態的蠢蛋游坦之。
不過在我這樣互相譬喻、自我安慰的同時,我可沒想過,不管是阿紫還是阿朱,都和喬峰此生無緣。把變態阿紫當成寶一樣看待的笨蛋游坦之,即使犧牲一切,最後也成不了阿紫喜歡的那盤菜。
人生就是這樣的事。
我喜歡的,未必喜歡我。
我和杜子泉也一樣。
※※※
現在,按下快轉鍵,跳過八歲時我和媽媽的無聊爭吵,跳過十八歲時我和杜子泉在圖書館裡消耗辰光,往後往後,再往後……春風得意馬蹄疾啊,青春小鳥一去不回頭……落在我二十八歲這一年的此時此刻,農曆除夕的下午。
我是開車返家過年的,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只有傻子笨蛋才會在全台灣的車都擠上高速公路時,把自己的車頭尾隨著人家的車屁股開上去。
從台北開回台中,整整五個小時,就是一個「塞」字,塞到我都閉著眼睛睡了一覺醒來,還發現自己停在原地動都沒動。我挫敗地心想,就是一隻螞蟻沿著公路爬,這個時候也該到家了,四輪車還不如一隻螞蟻呢!
什麼叫做大錯特錯?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裡,總要跟隨著其他更多的錯誤,才能顯得它是如何地無藥可救!車近泰安時,我受到人體自然的感召,想開進休息區找個廁所。沒想到路上塞就算了,休息站前五公里也在大塞車,一路塞進休息區、塞進停車場,好不容易把車停好,遠遠看見廁所,我的眼淚就下來了……
梟雄曹操有篇著名的《短歌行》,裡頭有句話很符合此時休息區廁所的景象:繞樹三匝,何枝可依。意思是說一群烏鴉繞著樹木飛了三圈,找不到可以落腳的樹枝。
換成我眼前的情況就是,等廁所的人把裡外圍了何止三圈,每個人臉上的表情蕭條鬱悶。換得更生活化點的形容,就是一臉忍無可忍的大便色。
我在廁所外頭等了半小時,前進的速度不比高速公路好到哪裡去。總之,在絕望中我做了更絕望的決定──,把車重新開回公路上頭,,,前進的速度不比高速公路上路上頭,抱著如果非得花時間排隊等廁所,還不如上高速公路上排隊,回去上我家的廁所。
我於是把把車又開上公路,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內進行坐立難安、天人交戰的意志力戰鬥,原以為煎熬沒完沒了,誰知在天近黃昏前,居然開下了老家附近的交流道。
回家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隨著周邊的景物愈來愈熟悉,人就愈來愈興奮,那種近鄉情怯的感覺是很微妙。
其實,和人生一樣,很多事情都是重複的。
譬如說,老媽雖然總含蓄地說「人回來就好,還給什麼紅包」,但她抽走紅包的手法之快狠準,又比去年更勝一籌。好像她整年不見,就是躲在山裡練這手功夫。
年夜飯的菜色,今年和去年差不多,去年和前年也差不多,前年和大前年、大大前年,和妳有生以來的記憶放在一起,大概只有盤子換過的差別……
親戚不外乎是那幾個,缺一點增一點多一點少一點,缺的是趕不及回來的,增的是從外頭帶回來的,多的是生出來的,少的是永遠不會再回來的。但不管怎麼增減缺補,本質上並沒有太大變化,並不會有人類變身成納美人。
唯一與時俱進變化的是餐桌上的話題。
學生時代回家吃年夜飯,爸爸說的是「好好讀書啊,別貪玩」。
畢業後回家吃年夜飯,爸爸說的是「好好找工作啊,別貪玩」。
工作幾年回家吃年夜飯,爸爸不說話了,換媽媽說「好好找對象啊,別貪玩」……
我猜,等我老了回家,他們會說「好好找間養老院啊,別貪玩」。
說也奇怪,每個大人,或者每個老人,總以為我們這些小的,總躲在他們看不見的地方玩玩玩,可是蒼天為證,我人生中最缺的東西就是玩。
玩和讀書一樣,都要花時間。這個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就是生命有長有短,但最公平的是每個人一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時。在玩上頭多花點時間,在讀書上頭就少點時間。最好的人是勞逸平均,但這種事情就算拿出勞基法來也沒辦法保障。
大多數的人都是勞多於逸,但我比較慘,我是勞大大多於逸、嚴重多於逸,有勞沒有逸。
誰教我碰上了杜子泉!
我和他的關係,一言難盡,如果非得要找個譬喻詞,大概可以用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冤家路窄、仇深似海來形容我倆之間,既簡單又複雜,既單純又微妙的關係……
不過,那些都是過去的事情了。
現在最適合我們的用詞也是四個字──形同陌路。
右轉拐進我家門前的巷子時,我還下意識計算著,和杜子泉到底有多久沒見了?答案下一秒鐘就得出來:四年八個月又十三天!我之所以記得這麼清楚,不是因為數學多好,而是因為從他離開以後,我就沒辦法停止每天幹同一件事:早上起床對著鏡子洗臉,把時間加上去,然後一面刷牙一面含糊地罵「杜子泉,你這個狼心狗肺喪盡天良的王八蛋」!
剛開始我罵得很恨,但甚麼事情放久了就沒意思了,譬如今天早上我說的是「杜子泉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是我在咬牙刷的聲音。
我想一想,就把這件事情甩到腦後去了。沒把事情想深,不是因為我灑脫,而是因為憋尿實在太難受!憋尿是一種相當符合莫非定律的學問,你離馬桶愈遠,就愈不會去想上廁所的問題,但離得愈近,就愈忍不下去。
開到家門外時,我已經進入生死關頭,只等著把車子停好就踹門而入直奔廁所,這條路上誰擋我路,誰就是我此生不共戴天的敵人!
說敵人,敵人就出現了。
我家門前的巷弄狹窄,兩邊停滿車,中間留的空隙恰好能容一輛汽車通過。車子多,車位少,找停車位和上天摘月亮是差不多的難度。
這雖是我第一次開車返家,卻早有準備,拿起手機就往家裡撥,沒響兩聲,被我媽接起。
「媽,我快到了!」
「到哪了?」
「離門不遠。我的車位呢?」
「就在門對面呀。昨天我和妳爸把大花盆推過去佔了位子,妳爸的腰都拉傷了……喂,妳看見位子了沒有?」
我往前張望,右手邊是我家的白鐵大門,左手邊果然有個空位,被我爸用他那盆寶貝玉蘭花佔著。
「看見了看見了。」
我媽在電話那頭叮囑,「小心停車,別把你爸那盆花給撞壞了!不行不要勉強,我叫妳爸出去幫妳。」
「我可以!」一聽到質疑,我的嗓門就不由自主大了起來,「我在台北開車停車都沒問題。」
「那妳注意點,不行就叫妳爸。」
我媽把電話掛了,我把車向前開。
其實我跟我媽吼的那句話裡面有相當多灌水和唬爛的成分。譬如說,我在台北是開車沒錯,但次數屈指可數,開的路程永遠是一樣的,就是從家到學校、從學校回家。永遠都是固定好的,一點都不能出錯。
有次開車去學校,進了校門,發現我的車位給人佔了,偏偏停車的人老不回來開走,害得我在那裡等啊等、等啊等,等到心灰意冷日月無光,只好又把車掉頭開回家去,叫計程車趕去學校上第一堂課。
總而言之,我就是那種有變化就要硬化的人。所以說,這次我堅持把車子開回家,是多麼英勇過人的行徑。
可能因為一路憋尿的緣故,過度強化的個人慾望,就會相對削弱自身敏感度,所以對於我自己是在如何艱難不可能的情況下,把車子連人從台北乾坤大挪移弄到台中這件事情,我並沒有太深的感受。
我現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趕快把車子停進車位,去找廁所。
但我前面那輛車不給我這個機會。
我猜它也是在找車位,因為它用比平常車輛行進還慢的速度在巷弄之間繞來繞去,最後,在我家門前停了下來,旁邊就是我媽我爸給我留的那個空位。
我按了兩下喇叭,宣示主權,可是對方弄錯了我的意思,它開始打左轉燈,示意它要停車。
然後我就急了!
很多年以前,杜子泉就曾告誡過我,凡事不能急。他說:「妳一急起來就會犯更多的錯。」
我矢口否認,「哪有!」
「真的,妳的問題是,沒有辦法一心二用,同時處理兩件事。」
我說:「誰說的,我經常同時處理兩件事,我還可以同時處理三件事。」
「譬如說?」
我想了一下。「我可以邊看電視邊講電話邊吃零食,必要的時候還能偷聽我媽和我爸講隔壁鄰居的八卦。」
他臉陰下來,掉頭就走,一面走一面無限悔恨地說:「我就不應該浪費時間跟妳講這些廢話。」
那些話言猶在耳,但眼下誰也阻止不了我犯錯。
我看前頭那輛車就要停進我的車位,邊按喇叭的同時,邊搖下車窗,探頭嚷嚷,「等等!這位子是我的──」
我沒能把話說完,因為在探頭時,重心一偏,腳下一鬆,原本踩著的煞車放開來,然後……
我就連人帶車,「砰」地一下撞上了前面那輛的車屁股。
我撞了車,自己嚇了一跳,渾身抖了一下。那瞬間我的理智告訴我:快把煞車踩住!
可是忙中有錯,就像是在趕著出門時,永遠找不到鑰匙或手機一樣的道理。在那瞬間,在我驚慌的同時,我的右腳摸到了一個踏板,往下又用力一踩──
恭喜,那是油門!
於是我那輛二手的Toyota就像猛虎出閘一樣地蓄積了全部的氣力,排氣管發出「轟」的一聲虎吼,視死如歸義無反顧地往前再撞了一次!
接下來,就是同樣錯誤的重複:撞上,緊張,想踩煞車,猛踩油門,往前再撞,更緊張,更想踩煞車,更用力地踩油門……
在這個過程中我聽見有人「唰」地用力開窗的聲音,聽見我爸在那邊喊:「老婆快來看,車禍耶!」
但下一秒鐘我就聽見我媽在那邊喊,「老頭,開車的是你女兒啊!」
你有沒有犯過錯?不是那種考零蛋、打破別人家窗子的小麻煩,而是犯了超過正常人能夠負荷承擔的大錯?
犯錯之後,你會有什麼感覺?我的感覺就是乾乾淨淨的空白。
在那段空白裡面我到底反覆地把前面那輛車撞了幾次,我真不知道。總之,最後一次撞它時,我看見我的引擎蓋跳了起來,噴出白色的水花。
那瞬間我的世界突然變得很安靜,耳邊好像什麼聲音都聽不見,腦海裡只有一個問題!讓我停下來間我的世界突然變得很安靜,耳邊好像什麼聲音都聽不見。──怎麼才能停下來?
但你知道的,不管怎樣混亂的場面,都要有結束的時候。就像是電影裡當地球面臨末日,總得有一個英雄挺身而出。
此刻,這終結末日任重道遠的責任,就落在我身上了!
所以,當不知道第幾次,我把車頭撞上前車的車尾,又反彈退後的時候,我用力轉動方向盤,把車頭往停車位裡擠進去。
透過擋風玻璃,我看見我爸的玉蘭樹,離我愈來愈近、愈來愈近……
總之,在最後一次驚天動地的碰撞聲後,玉蘭樹攔腰折斷,而我的車終於不動了,而撞擊力讓車頭的氣囊爆開,把我卡在駕駛座上,動彈不得。
壞掉的喇叭發出扭曲的怪音,引擎也是,嘶嘶作響,好像沸騰的水壺。
我開始聽見其他人的聲音,就像流行歌曲的副歌一樣嗡嗡嗡地在我耳邊亂轉。
有人過來開我的車門,動作很大,門把被拉扯得像是要支解開來一樣,最後他把窗戶給砸破了,開了門鎖,把我從安全帶的挾持中解開,整個人往車外拖。
我雖然號稱膽大無畏,但也被這場意外嚇得魂飛魄散,站都站不住,坐在地上直發抖。
拖我下車的那人吼了我的名字,「程秀翎,妳找死啊,這樣開車!」
我後知後覺反應很慢地抬頭看他。
我跟你說,我最恨言情小說那種號稱巧合的安排,譬如說,世界這麼大,六、七十億人口中的一個男人,總能和六、七十億人口之中的那個女人,在不可能的地方見上一面。
而且見面時,總恰恰是女孩子身心受創,最軟弱的時候。
我每每看到這類橋段,總氣得砸書。試想,這種巧合的相遇,比中大樂透頭彩的機率還低,但怎麼每本書都少不了這一套!
但這一刻我該砸誰好呢?
我坐在粗粗的柏油路面上,杜子泉彎身蹲在我面前,夕陽西下,落日的餘光穿過他的髮梢,風輕輕吹,吹著他軟軟的頭髮。
他的眼睛在夕陽下像是兩簇熊熊火光,怒氣衝天地瞪著我。
我猜我一定是被剛剛那幾下猛撞,撞得有點腦損傷了──雖然我才是肇禍的凶手,而且從頭到尾都沒有碰到腦袋一下──眼前生出幻覺來,我居然看到他火冒三丈的目光底下,藏著點些微且經常被人誤認為麻木不仁的隱藏版笑容。
我想,我得說點什麼,才不辜負這四年八個月又十三天的時差,才能扳回我現在身處的窘境,還有我那丟失許久的、寶貴的、價值連城的自尊心。
我得說點狠話,愈狠愈好、愈毒辣愈好、愈翻臉不認人愈好。
我很快就找到了那句話。
我決定用最鄙夷不屑藐視輕忽的語氣,對這王八蛋說:「原來這樣都沒能撞死你啊!」
但我忘記了一件事,就是在這個世界上,我可以上罵天下罵地左罵政客又罵學生,我可以對著鏡子罵我自己罵到豬狗不如的地步,但我就是沒辦法對杜子泉說什麼生生死死的重話。
我對他說過最重的話就是「我們分手」,而就連這句話,我也只說過一次而已。
所以當我用最鄙夷不屑藐視輕忽的語氣,咬牙切齒地說出「原來」兩個字之後,我就再也說不下去了。
然後,然後……沒有什麼然後,然後我就淚眼汪汪地大哭了。
(待續)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流光中的小確幸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5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50 |
愛情小說 |
$ 158 |
華文愛情小說 |
$ 158 |
網路愛情小說 |
$ 158 |
大眾文學 |
$ 158 |
愛情小說 |
$ 176 |
中文書 |
$ 18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流光中的小確幸
愛與恨,不過是一線之隔。
在這個故事裡,我扮演的一直是羊的角色。披了狼皮或虎皮,還是一隻羊,就算把毛色染出花紋,也不會變成一隻豹。我可以用變聲器發出狼嚎或虎嘯,但去掉外力,還是只會咩咩叫。是什麼促使一隻羊去追逐老虎和飛天遨翔的獵鷹?是什麼力量讓我相信自己無所不能?是什麼讓我無悔的走到今天?如果不是因為我恨你,就是因為我愛你。
作者簡介:
ABOUT 霜子
1977年8月出生於台北,華梵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
有獅子座要命的驕傲,但生活智能低落,忘性嚴重。
最大的樂趣是買書和讀書,還有說故事。
現在是兩隻貓咪的監護人。
*特色、信用
曾出版《破襪子》、《搭便車》、《離魂》、《流光》、《黛華‧有蓉》等書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我從小就不聰明。不是天資差智商低,而是思考慢、反應慢、做事慢,因為這三慢的緣故,經常吃了虧不知道,等想清楚了,一肚子委屈無處可訴,於是大發脾氣,但早已事過境遷。這種不在該發脾氣的時間發脾氣的紀錄多了,就更顯得我個性暴躁、倔強古怪。
但我媽說,我不是不聰明,只是不愛用腦袋。
我媽的言外之音就是──笨是妳自己的問題,和生妳的我沒有任何關係。
更簡單的意思就是,她在撇清。
等我想通了這句話明喻暗喻之間的關係後,我就知道,我不聰明的問題,歸根就底算起來,和我媽大有關係,不但有...
我從小就不聰明。不是天資差智商低,而是思考慢、反應慢、做事慢,因為這三慢的緣故,經常吃了虧不知道,等想清楚了,一肚子委屈無處可訴,於是大發脾氣,但早已事過境遷。這種不在該發脾氣的時間發脾氣的紀錄多了,就更顯得我個性暴躁、倔強古怪。
但我媽說,我不是不聰明,只是不愛用腦袋。
我媽的言外之音就是──笨是妳自己的問題,和生妳的我沒有任何關係。
更簡單的意思就是,她在撇清。
等我想通了這句話明喻暗喻之間的關係後,我就知道,我不聰明的問題,歸根就底算起來,和我媽大有關係,不但有...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霜子
- 出版社: 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1-04-10 ISBN/ISSN:978986120701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輕小說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 |||
|
|


 2017/06/13
2017/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