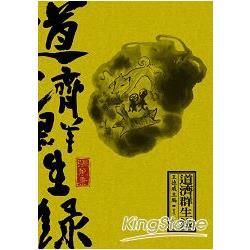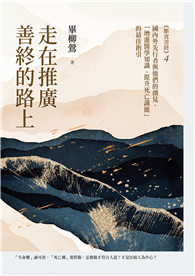序論
我要我爹活下去!—小說二十五孝之《道濟群生錄》
《道濟群生錄》是一本奇書。話說公元二○一○年初夏,九十歲的老榮民張濟跌傷送醫,未料胃出血引發肺炎。醫師不察,努力歡送出院,等到再度急診時病象已經極度凶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檢查發現張濟已經是胰臟癌末期。
這張濟有子名萬康,雖然哈拉成性,卻是個為孝不欲人知的奇葩。老父蒙難,小萬康心急如焚,竟然驚動神魔世界,引發一場陰陽大戰。不但佛道儒各派齊力發功,天主摩門基督也友情加盟。這邊有保生大帝、藥師如來、關雲長, 那邊有炎魔大王、腫王、惡水娘娘,神鬼交鋒,端的是無煙不烏,有氣皆瘴。張氏父子聯手抵抗病魔,鏖戰連場,怎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終究功敗垂成。
我們很久沒有這樣看小說的經驗了。《道濟群生錄》是本悼亡之書,但寫來如此不按牌理出牌,以致讓你欲哭無淚,反倒駭笑連連。作者—好巧,也叫張萬康—直面自己和親人生命最不堪聞問的層面,卻又同時拉開距離,放肆種種匪夷所思的奇觀。張萬康筆下有大悲傷也有大歡喜,臨到生離死別還不忘嗑牙搞笑,不由得我們不好奇是怎樣的一種小說倫理在支撐他的創作演出。
上個世紀末各種名目小說實驗層出不窮,幾乎要讓我們懷疑還可能冒出什麼新花樣。像《道濟群生錄》這樣的作品再次見證小說家的想像力永遠領先任何史觀和理論。談張萬康解構了寫實主義「有始有終」的敘事宿命,或發出巴赫金(Bakhtin)嘉年華狂歡式笑聲、顛覆身體和信仰的法則,都能言之成理。(註1)但這本小說同時也是本發憤療傷之書。在極盡荒謬之能事的背後,它敘事的底線是一則有關病的隱喻。
張萬康何許人也?他雖然名不見經傳,卻不是文壇新人,二○○六年甚至憑〈大陶島〉得到《聯合報》小說獎的首獎。這年頭文學創作式微,文學獎項浮濫,得獎未必就能走紅,何況張顯然也不符合市場的主流路數。好在他自甘平淡,創作不輟,而且時出奇招。平心而論,張的作品風格參差,文字的駕馭易放難收,外加一股野氣(看看他的部落格吧),正經八百的讀者可能要側目以對。但也許正因此,他蓄積了一股無所拘束的能量,彷彿就是為《道濟群生錄》作準備。
《道濟群生錄》的雙卡司是九十歲的爸爸和四十二歲的兒子。張濟一九四九年隨軍來台,娶了個羅東姑娘,生兒育女,官拜士官退伍。他樂天知命,老來以省水節電為能事,半杯水就能沖馬桶,打牌作小弊,餵狗吃大肉,行有餘力就看叩應節目清涼影片。這是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老兵故事,「最後的黃埔」那樣的好戲輪不到他。可有一點值得注意,張爸生命力特強,即使到了加護病房依然不甘就範:「這萬爸沒啥了不起的生死觀,你如果問他為什麼要活?他可能反問你為什麼要死?」
有其父必有其子,張萬康號稱大隱於市,說穿了宅男一名。他舞文弄墨為業,放言無忌、痞味十足 ,骨子裡卻不失天真,頗有滯留青春期過久的嫌疑。以老張小張父子的歲數差距來看,很難想像他們如此投緣。但萬康對老爸的關心在在令人動容。眼看把拔在病房受苦,他日夜手縛《心經》以示感同身受;醫院人情磽薄,診斷結果每下愈況,卻不能搖撼他救父的決心。與此同時,他調動各種文學資源,以異想天開的形式救贖現實絕境於萬一,故事也由這裡起飛。
張濟、萬康父子抗病的故事以章回小說呈現,第一回〈萬康爸爸含冤蒙難,保生大帝道濟群生〉已經暗示敘事背景大有來頭。原來萬康孝心觸動地府判官、藥師如來,引發一場搶人大戰。現實生命的後面竟有如此龐大(而且官僚)的神魔體系左右,陡然讓故事的縱深加寬。第六回裡萬康以藥師佛傳授的「大力拍背掌」為父親灌注真氣,拍著拍著就進入老爸體內幻境,這幻境魔山惡水,妖氣瀰漫。父子兩人聯手出擊,只殺得炎魔兵團、野戰師、特戰旅東倒西歪。張家養的貓狗外加一隻野鴿子也來助陣,一時風雲變色,鴿飛狗跳,雞貓子喊叫,好不驚煞人也。萬康大喊「我們要反攻!」萬爸高呼「仗要打就要打贏!」到了第七回情節急轉直下,單看回目〈魔王雪竇山難發簡訊,娘娘婊裡山河會情郎〉就可以思過半矣。
張萬康的靈感包括民間宗教,以及神魔小說(像是《西遊記》、《封神榜》)、鬼怪小說(像是《三遂平妖傳》)等。這類小說演義另一個世界的神奇冒險,卻不乏世俗人間情懷,更重要的,它從不避諱一種憊賴的喜劇精神。炎魔大王和惡水娘娘不就讓我們想到牛魔王和鐵扇公主?只是這對魔頭渾身台味,壞得彷彿出身民視八點檔。
張萬康運用這些情節人物來探討病的本質和醫療倫理。當父親的病已經到了山窮水盡,人子要如何面對必然的死生關口?而當病人和家屬在絕望中找希望的時侯,醫護單位、健保機構又如何提供診治和安慰?這是小說的底線。張萬康對張爸入住的醫院不無微詞,因為誤診在先,又繼之以連串治療瑕疵。其中部分描寫也許出於張求全責備的心情,但死生事大,任何讀者,尤其是從事醫療工作者,能不將心比心?
然而張萬康是小說家,他寫疾病和死亡不僅限於和醫院斤斤計較。來回在冰冷的加護病房和十萬八千里外的神魔世界間,他有意無意的投射出不同知識、信仰,和社會體系的衝撞。誠如傅柯(Foucault) 所言,醫院是現代社會裡重要的異托邦 (heterotopia),是收容和診療病人的專屬空間,用以確保醫院以外「健康」社會的「正常」運作。(註2)但就像任何異托邦一樣,醫院不能排除其中介、權宜的位置,它的進口和出口總開向其他形形色色的空間設置。在《道濟群生錄》裡,它至少和三種空間相與為用。第一,如上所述,從萬康個人和家人對宗教信仰、民俗療法的管道來看,醫院難以自命為處理身體和病厄的絕對權威,而總是吸納和排斥種種人為的、偶然的、甚至非理性的因素。換句話說,醫院是個欲潔何曾潔的有機體,本身的體制—和體質—必須隨時付諸辯證和檢驗。小說第十一回〈花判官串戲三岔口,野山豬大鬧ICU〉幻想冥府判官潛入病房色誘護士醫生,讓他們慾仙慾死(嚴重的還有了屍斑),正是對醫院謔而且虐的攻擊。
其次,住院治療的萬爸雖然病入膏肓,但是壯心未已,醫院成了他最後的戰場。比照萬爸的榮民背景,小說儼然有了一層國族寓言色彩。病床上萬爸一息尚存,隨侍一旁的萬康為他加油打氣,一時神遊天外,「我們要反攻!」,「仗要打就要打贏!」。但反攻到哪裡去?俱往矣,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敵人不在別處,就在醫院內,病床上,自己的身體裡。我不認為張萬康刻意安插任何政治隱喻,唯其如此,反而道盡父親那一輩臨死也揮之不去的政治潛意識。
更值得注意的是《道濟群生錄》的寫成方式。張萬康動筆時正是張爸病況膠著之際。我們可以想像小張在醫院裡無能為力,只能另闢蹊徑,「寫」出一條生路。前面提過,他糅合了報導文學、神魔小說、家族私密各色文類,形成獨特的敘事風格。然而這只是起步。小說的進展與父親的病況相輔相成,同時在部落格上開始連載,引起眾多回響。張又據此添枝加葉,一方面與君同樂,一方面自我解憂。網上的虛擬空間形成一個與醫院抗衡的地盤。在這裡身體暫時架空,時間得以延伸,人我關係變得無比豐富多元。小說連載到第九回時張爸去世;萬康日後完成二十回,卻仍以第九回的時間點作結。如此,文本內外互動頻仍,張爸出虛入實,不斷起死回生。
《道濟群生錄》也是張萬康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小說。除此他雖然創作多年,卻只有一部短篇小說集《W.C. Zhang:張萬康小說》以自費方式印行。這本小說集收錄張最近十年的作品,其中部分可以看出《道濟群生錄》的線索。大抵而言,這些作品的敘事主體是一個蟄伏在城市裡的文藝中年,他或者觀察無聊的生活律動,或者陷入某種荒謬的邂逅。他的小說往往這樣開場:「我開始幻想,在我發呆很久之後。」(〈山脈〉),「起先,我以為我走在蛇的肚子裡,後來我發現是在鯨魚的肚子裡。」(〈史尼逛〉),「我被包圍了,不知道他們什麼時間會發起攻堅。」(〈落跑者〉),「我沒睡好。買完車票,來到南方小廣場抽菸。」(〈半吊子〉),這些字句很容易讓我們聯想起現代主義修辭,儘管張自稱沒看過幾本世界名著。孤獨、白日夢、晃盪,徒勞的突圍表演,都是他荒謬劇場裡的要素。但張無意經營高調,很快亮出自嘲或是賭爛的姿態。他的敘事充滿不穩定性,故事多半不了了之。
這個期間張萬康又熱衷寫性,而且刻意誇大其辭。不論是萍水相逢(〈電動〉、〈半吊子〉)還是泡妞把妹(〈天使2001〉、〈國劇與我〉),他跳過談情說愛,下筆盡是摳揉搓舔、哈棒打槍。這夠刺激了吧,卻總給人虛張聲勢的感覺,因為缺乏任何情緒發展的自信和自覺。他的人物作老鳥狀,其實都是孤鳥。
一直要到得獎的作品〈大陶島〉,張萬康才將他這些執念整合起來。小說的主人翁是個研究所輟學生,正港台灣人,因為患了「神經病」被送醫治療。二○○四年總統大選發生三一九槍擊案,他走上街頭,在抗議人群中與「大陳義胞」老陶結識。這一老一小在各種場子裡衝鋒陷陣,說不盡的壯懷激烈。不作戰的時候他們以同樣的熱血精神消耗A片;老陶曰:「管他槍擊案,A光本來就是要看的啊!」一場神祕的大洪水掩至,兩人坐在桌上漂出光棍宿舍,同時不忘盯著電視檢驗新到A片。當桌子航向大陳島的方向,電視長出魚鰭,老陶變成斑花海豚,泅泳了幾遭後,朝電視一望:「還沒射啊!」
〈大陶島〉寫「神經病」的狂想、寫漂泊,寫沒有名目的欲望、自瀆式的痛╱快,都是張萬康小說常見的題材。而這一回他找到一個引爆點,也間接安頓了自己的創作意識。三一九槍擊案將他狂亂的敘事線索政治化也合理化了。主義、運動、抗爭高潮迭起,不就是春夢,不,春宮一場?老陶最後也是槍擊案的犧牲者—某A片之夜他打完手槍,意外跌倒,就地成仁。
〈大陶島〉出沒性與政治符號間,讀者不難作出歷史隱喻的解讀。但張萬康真正令人矚目的是他對文字的橫徵暴斂,對形式的一意孤行。這使他向當代的異質小說家從王文興到舞鶴的譜系靠攏。這些作家為了完成自己孤絕的美學,往往不惜犧牲敘事的可讀性,也因此必須付出曲高和寡的代價。張萬康佳作尚少,也許難以和前輩相提並論,但他的發展值得注意。
這讓我們再回到《道濟群生錄》。這本小說不妨看作是〈大陶島〉的溫馨家庭版。張萬康曾寫過一篇〈大小鋼杯〉講述父親的生活瑣記,算是《道》書的熱身準備。張濟比老陶幸運,他結了婚,有了家,成了溫馴的老芋仔;三一九槍擊案他必定也義憤填膺,到底沒有老陶瘋狂。有一回淹大水,他也爬上書桌避難兼看電視,但看的不是A片,是港劇。
但張萬康明白老陶和老張本是同根生,他們過早歷經離散,都有不能言說的創傷,也都有不願就此罷休的韌性。老陶看A片看到鞠躬盡瘁,老張大戰炎魔死而後已。人生有多荒謬,他們就有多固執。他們是最令人意外的西西弗斯(Sisyphus )。
外省父親之死—尤其是具有軍職的父親—是近年台灣小說界的主題之一。張大春的《聆聽父親》、朱天心的《漫遊者》、駱以軍的《遠方》、郝譽翔的《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等作,都曾處理這一主題。這些父親們少小離家,渡海來台,他們是一個時代政權裂變最直接的見證,也同時體現了生命中太多莫可奈何的境況。歲歲年年,反攻大陸的號角迎來了陸客自由行,他們的信仰和肉身已經垂垂老去,以至消亡。
張大春的《聆聽父親》未完,姑且不論。在朱天心的《漫遊者》裡,父親所代表的血緣的、政教的、信仰的象徵體系一旦不再,她陷入了憂傷的無物之陣。漫遊者尋尋覓覓,無所依歸,連語言也開始漫漶起來。駱以軍的《遠方》敘述返鄉探親的父親突然罹病癱瘓,台灣出生的兒子匆匆趕來救難。龐大的病體、艱辛的旅程、荒謬的遭遇讓作家理解人子與父親的關係是怎樣一種離棄與錯過,一種無從說起的困境。郝譽翔的《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則寫出父親自殺「以後」的故事。父親終其一生不斷逃避責任、離開現場,留給女兒太多創傷。父親的死成為唯一解套方式,而且弔詭的重新開啟父女間溝通的可能。
是在這樣的譜系裡,《道濟群生錄》更能顯現自己的位置。張萬康何其有幸,和父親相親相愛,但兩人的關係又無須像《漫遊者》那樣無限上綱到一切意義體系的源頭。回到書寫層面,我要再次強調張萬康的異質風格。他沒有駱以軍的頹廢荒誕或朱天心的深沉鬱憤;他有的是挪用民間信仰、神魔小說,創造「偽史詩」(mock epic)的勇氣。滿天神佛盡為我用,這是何等僭越?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張萬康和他的老爸幾乎是理直氣壯的走入神魔世界,和菩薩魔王討價還價。
然而比起張萬康以前的作品,《道濟群生錄》最大的突破不在於他如何雜糅神話鬼話,創造醫院今古奇觀,而在於他因此所流露的真情—人子的孺慕孝親之情、傷逝惜生之情。張萬康的戲謔和犬儒也許可以用各種後現代理論解釋,但說到底他是有情之人;他所有花招後面是個簡單的心願—我要我爹活下去!這心願力道之大,可能讓張自己也嚇了一跳。古老的倫理歷久彌新,竟有了最酷的表述方式。臥冰求鯉、割股療親的二十四孝早過時了,新版第二十五孝是陪著老爸大戰炎魔王,和保生大帝計算命盤,還有最重要的,把往生的故事寫成慶生的故事。張萬康的敘事當然是駁雜的,他信馬由□的話頭也是紛亂的,但看他一路嬉笑怒罵到最後,我們不得不正襟危坐起來。可不是,連觀世音菩薩也讚嘆小張的「憨意與善情」。
《道濟群生錄》的最後四回寫神魔大戰。這場戰事殺得天地變色,日月無光。藥師如來手下頭號大將宮毘羅壯烈犧牲,呂洞賓施展美男計,惡水娘娘臨陣叛變,連關公也陣亡了。炎魔大王惡貫滿盈,佛軍落得慘勝。看官不禁要問,張濟何德何能,居然能夠引起這樣鬼哭神嚎的風暴?饒是這般,張濟還是不願歸天。最後勞駕阿彌陀佛、藥師如來、甚至觀音菩薩出馬溫情喊話,軟硬兼施,才好勉強上路。
張北杯走了,九十年浮生倥傯不過留下個臭皮囊。他肉身的消弭卻助成張萬康小說功力大進,寫出《道濟群生錄》。入死出生皆是夢幻泡影,喝佛罵祖無非方便法門。有子如萬康,張爸可以無憾。願他老人家在極樂世界每天繼續嗑活包蛋,外加一杯卡布嘍囉。阿彌陀佛,有道是:
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身如琉璃,內外明澈,淨無瑕穢,光明廣大,功德巍巍,身善安住,燄網莊嚴,過於日月。
王德威
1見朱嘉漢精闢的分析,〈「狂轟爛入」嘉年華—讀張萬康《道濟群生錄》〉,見本書頁三五六—七二。
2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1967), “Heterotopias,” foucault.info/documents/heteroTopia/foucault.heteroTopia.e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