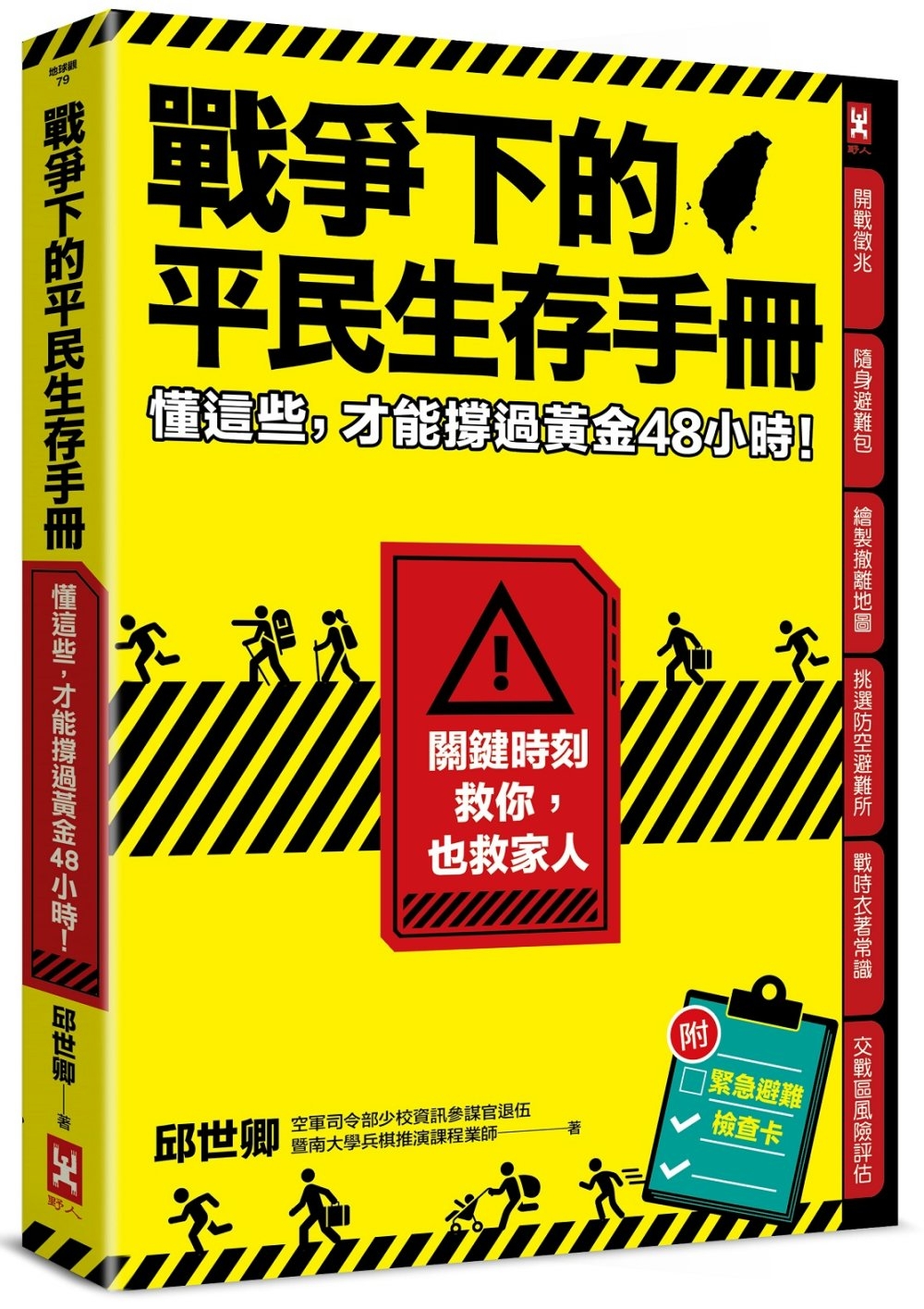名人推薦:
★亞馬遜網路書店5顆星評鑑!
★《政變實務手冊》一書再版無數次,被翻譯成14國語言
名人推薦
馬家輝(香港明報總主筆)、尹乃菁(New98電台主持人)、南方朔(知名評論家)、胡忠信(歷史學者)、陳一新(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教授)、黃介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鍾佳濱(屏東縣政府副縣長)
國外媒體好評
★「這本小書邪惡、揭發事實,且相當具娛樂效果。在一步一步說明發動政變的步驟後,作者分析了現代(二戰後)的政變,同時指出為何有些人可以成功,而有些人則否。──《紐約客》雜誌
★一部相當傑出且切合主題的作品,展現了去規劃無論成敗的政變所需的龐大知識。──《時代雜誌》文學別刊
★《完全政變手冊》一書證明了學術分析可以是相當傑出的社會學作品,同時也讓讀者閱讀時樂在其中。文體平易近人,沒有艱澀難懂的術語……同時,書中清楚展現了魯瓦克對政治學基本概念以及問題的熟稔。在處理敘述主題時,他既不浮誇也不過度著墨無用的小細節。因此,這本書對於所有對於頻繁發生的推翻政府行動有興趣的讀者來說,相當具有一讀的價值……我們在閱讀這本說明清楚又充滿智慧巧思的小書時,樂在其中。──《薇吉尼亞書評季刊》(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文人戰士——魯瓦克素描
撰文:江春男(新新聞創辦人、曾任國家安全會議副主席)
伊朗對西方是一個謎樣的國家,但它的改變,不只影響中東政治,對穆斯林世界,從阿富汗到埃及,從伊拉克到印度,都會受到很大衝擊。這次大選引起動亂,整個氣氛有點巷八零年代東歐自由化前夕,西方戰略專家紛紛撰文發表高見,其中最引起我興趣的是美國的魯瓦克(Edward N. Luttwak),不是他的見解特別深入,只因為他為我打開另一扇門窗,帶我走進另一個世界。
魯瓦克現在華府戰略安全研究中心(CSIS)擔任資深研究員,他是一位博學多聞,才氣洋溢的軍事歷史和戰略專家,他除了擁有典型猶太知識份子所應該具備的數種語言專長,經常在報上發表文章,出版十多本有關戰略安全方面的書,而且是一位行動家,和許多國家的情報和國防部門有密切關係。他實際參與反恐和軍售,介入阿富汗、以色列、伊朗、義大利、拉丁美洲的許多秘密活動。他和中國軍方和司法單位也有顧問關係,前年好萊塢反恐電影《蓋世奇才》(Charlie Wilson’s War),據說是他的親身故事。
他在華府近郊Cherry Chase的家,是一座維多利亞式的建築,從地板到天花板,四周都是書,希臘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歷史、戰略、情報、武器、戰機、導彈,多得令人頭昏。進到他家裡的人,還必須先把手機電池拿掉,以免被人追蹤,除了這一點以外,他健談熱情,有時像歷史專家,談論波斯文明和猶太人的淵源,有時像軍事專家,分析每場戰役決戰關鍵。他連中國古代的賦稅制度也做過研究,這一點實在唬人,他的意見不一定對,但保證新鮮有趣。每次聽他說話,都覺得趣味無窮,他的腦細胞排列組合方式一定與眾不同,否則怎麼裝得下這麼多東西。
我在三十年前就認識他,當時他應自由基金會的黃不撓邀請來台訪問。他演講時,好像是由陳長文先生擔任翻譯,當時的陳長文是國防部法律總顧問,參與所有軍購談判,賺了很多錢,成為全國繳稅最多的人之一,國防預算有一部份進入他事務所的口袋,與他現在反戰的鮮明立場,有如隔世。當時台灣被趕出聯合國,來自香港的黃不撓是愛國商人,他在紐約時報大登廣告替台灣發言,被稱為今之弦高。魯瓦克經過當時國科會國際工作組長王紀五介紹給杭立武,他才與台灣結緣。
當時他意氣風發,他寫的一本書《政變手冊》(Coup d’Etat, a Practical Handbook),在那個政變頻傳的年代,幾乎成為經典,搞政治者奉為聖經,獨裁者把它當作教戰手則。年輕無知的我,對此十分著迷,抱著字典一個字一個字讀完,以為從中可以找到推翻國民黨的方法。
這本書對政變的過程,從籌劃到執行,舉例說明附有圖表,分析各種變數和不同想定,富有創造力和想像力,文字洗鍊,一點都不枯燥。魯瓦克在英國倫敦大學念完書就寫完這本書,當時他只有二十六歲,這本書被翻成十五種語言,他一舉成名,後來被國防部長史勒辛格找去當助理,從此開始他數十多年的軍事戰略專家生涯。從阿富汗到喀什米爾、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到拉丁美洲,都有他的足跡,而他身為猶太人,對以色列、敘利亞、伊朗、埃及問題更是如數家珍,這些經驗成就他百科全書般的知識。在苦悶的年代,他的書引導我走入另一個世界,我跑去倫敦尋找他的足跡。
美麗島事件之後的台灣,一片肅殺氣氛。黨外人士發現對國民黨的軍情特務系統毫無所知,才會犯下致命錯誤。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到歐洲參加一個有關第三世界問題的研討會,懷著緊張興奮的心情,天天躲在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圖書館,那裡是研究革命與政變最權威的地方。晚上跑到泰晤士河邊的電影中心猛看第三世界電影,在那裡的舊書攤上發現一本「阿拉伯的勞倫斯」所寫的《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那是三零年代出版的老書,書皮剝落泛黃,我用三英磅買下,當晚興奮得睡不著。
在那些年頭,有兩片電影令人難忘,一片是《阿爾及爾戰爭》(The Battle of Algiers),拍得像紀錄片一樣逼真,法軍的追捕刑求和阿爾及爾人的反抗、暗殺、暴動,緊張得另人透不過氣。另一片是德國左派女革命家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erg)的傳記片,她寫作、演講、愛情、革命,後來被秘密殺害,一生高潮迭起,迴腸盪氣。在那個苦悶的年代,這類電影具有勵志與移情效果。
有一年,應美國政府邀請訪問,主要目的是軍事與國防,在華府的五角大廈聽簡報,在戰略空軍總部看星際作戰的操作,認識多位美國軍事記者,最有趣的是訪問幾位文人出身的軍事專家,看到他們書房裡堆積的軍事書籍,才慢慢瞭解這是一門人人都有機會窺其堂奧的心天地。在專制獨裁國家,情報戰略是高深莫測的領域,是統治階級的專利,但在民主國家,人人都可成為軍事戰略專家。有沒有軍事背景並不重要,魯瓦克就是一個典型。
魯瓦克是出生於羅馬尼亞的猶太人,為逃避納粹和共產黨的迫害移民義大利,後來去倫敦念書,做為猶太人的生存者和流亡者,他永遠要比敵人更聰明。他對軍事情報方面的興趣,來自於生存與自衛的需要,後來變為專業謀生工具。
有一次談到猶太人問題,他說歷史上的猶太人沒有安全感,拚命賺錢,沒有人研究戰爭與政治,命運永遠被人擺布。其實,弱小民族更應該研究戰爭與軍事,反對運動者更應該研究情報與戰略。擁有這方面的知識,小者可以加強反抗能力,大者可以掌握命運。不幸的是,反對運動者把這種知識當作統治者的專利,他們不知道這是一種「公民保衛」(civil defense),民主社會資訊發達,要瞭解戰爭與和平之道,一點都不困難。民主與人權是高貴的目標,但不瞭解軍事與戰略,就無法保衛自己。
魯瓦克是文人戰士的典型,他對各種黑暗勢力都有研究,他曾幫助義大利政府和西西里的黑手黨打交道,在墨西哥與毒犯談判,在阿富汗、土耳其、伊朗各地參與秘密活動。他有一半的時間在國外旅行,他在玻利維亞有一座牧場,研究、行動、寫作、諮詢、顧問、美酒、文化、吹牛,生活過得多彩多姿。
在伊朗問題上,他是強硬派,他批評歐巴馬對伊朗一廂情願,其實他自己對伊朗文化頗有好感,他說伊朗的古城Isfahan美得令人摒息,伊朗人的詩歌令人陶醉,可惜伊朗教士辜負他們的文明和人民。
不過,他對伊朗前途很有信心,因為戰爭與軍事的知識不是伊朗當權派的專利,改革派對此也有豐富經驗,這是最有效的制衡。知識就是力量,擁有這方面的知識,才有當家作主的機會。
本文發表自20090702《壹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