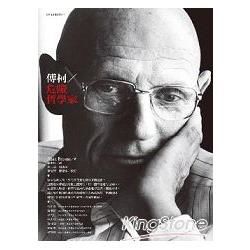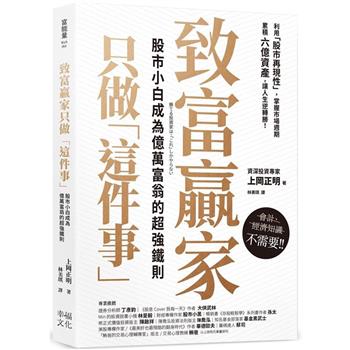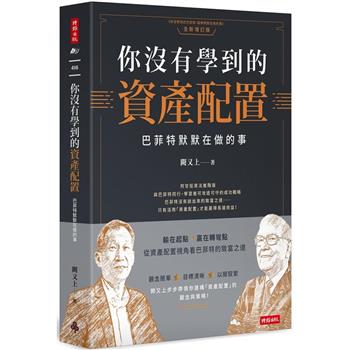★探討傅柯最著名的三個概念:歷史、權力與政治,Alain Brossat不僅能散發左翼知識分子的挑釁意味,也呈現出對社會的愛與關懷。
★對於傅柯及其時代,Alain Brossat既曾在場又富含後設,正是這樣非比尋常的位置,傅柯的反抗與革命滿懷感情的復活,成為哲學的活體。
做個危險人物,努力存在並化身為某個危險,這將意味著處於某種主體稟性,和一個不穩定的立場中。在這個立場裡,我們有最大的機會進行差異,擺脫束縛;而此地所展現的也並非某種替代方案或某種「大拒絕」,而恰好是能量倒置的可能性、異議與斷裂。――Alain Brossat
朱元鴻‧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專文推薦
苑舉正‧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李尚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志明‧國北教大學藝設系教授、
黃冠閔‧中研院中國文哲所副研究員、
劉紀蕙‧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楊凱麟‧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教授/聯合推薦
我一直期待臺灣能出現一本有關傅柯的書,它不但能散發來自巴黎左翼知識分子慣有的挑釁意味,也能夠在閱讀後留下深深的哲學反思。來自巴黎的Alain滿足了我的期待。本書中的所有文章環繞在傅柯最著名的三個概念:歷史、權力與政治。我卻在閱讀本書後發現,這三個概念共同呈現了超越社會的理解:對社會的愛與關懷;這也是我對於人倫的理解。――苑舉正‧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Brossat的傅柯再次讓我們見識到對傅柯的真正思考不可能是陳腔濫調。哲學的涉險、問題性的舖陳、差異的能量、布置性的思辯……成為重新構思傅柯的清新啟發。
對於傅柯及其時代,Brossat既曾在場又富含後設,正是這樣非比尋常的位置,傅柯的反抗與革命滿懷感情的復活,成為哲學的活體。――楊凱麟‧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教授
這並非一本研究傅柯的論文集,而是「跟著傅柯」一起探索,猶如一場持續進行的「對話」。這種「處於進行式中」的對話關係,可比擬傅柯所謂的「診斷」,更可說是Alain Brossat在「現時中」進行哲學研究的實踐。
1968年夏季,傅柯受邀在巴黎附近建立一所新的哲學系,先後數年之間加入諸如德勒茲、李歐塔、巴迪烏,以及本書作者Alain Brossat等多位學者,在二十世紀的人文社會思想界發揮了廣泛且深遠的影響力。
這本論文集之所以難得,不因為是另一部傅柯的研究,而是因為作者明確地用「跟著他」(avec lui)的方式,而得到源源不絕的啟發。
對於當代哲學家,存在著兩種研究方式:「對他」(sur lui),寫下專論;或是「跟著他」,一起探索研究。這本書顯然屬於後者。
所有集結的文章凸顯了一種方法:以某個獨特的時空環境,連結現時中某個問題。雖然問題並沒有獲得解決,卻在這種持續進行的對話中,得以清晰、被探討,進而重新組構。
本書篇篇論文都穿越了傅柯所曾給出的線索,在哲學思想的探究上,注入一股激盪與鼓舞的力量。
作者簡介:
Alain Brossat,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所名譽教授,專攻政治哲學。
相關著作
《傅柯:危險哲學家》
譯者簡介:
羅惠珍,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碩士,文字工作者,資深媒體人,素人演員。著有《法國沙龍巡禮》(星定石,2001)、《築夢洛維尼》(星定石,2001)、《餐旅專業法文》(華杏,2004)、《巴黎生活派》(華成 ,2005)、《台灣媽咪在法國》(華成,2006)。
章節試閱
危險哲學家?
我們發現傅柯經常使用「危險」、「危險的」,甚至「危險性」等字眼,在傅柯的各類著作中,「危險」這個字總是不斷出現。傅柯經常將「危險」這個負面的字眼顛覆為正面的;例如他評論有關亞陶的書寫已瀕臨瘋狂邊緣,充滿著危險,他在此其實是歌頌危險。例如在他提到克羅索斯基文章中的那些惡作劇的成分相當危險時,他總是帶著某種正面肯定的意味。再如傅柯談論現實社會中的治安問題時,也使用「危險」這個語彙,但字裡行間卻一點都讓人感受不到危險的威脅。他在不同的文本中都賦予了「危險」正面的意義。傅柯持續將危險隱藏在正面的意義裡,連哲學思維也依此分門別類;他設定了某些具危險性的哲學(首先是尼采哲學),有的危險性低一點,還有一點都不危險的。在布達佩斯時,他寧可到博物館欣賞莫內的畫作,也拒絕與盧卡奇見面,因為那一點都不危險。喬姆斯基對他而言,可能也不夠危險吧,傅柯在荷蘭與喬姆斯基對談時,氣氛非常沉悶,喬姆斯基激不起他的興趣,兩位大師的對話全程了無生氣、枯燥乏味。從這個「危險」的取向一路發展,當然,他對史坦納的嚴厲批評,更是前所未見。作為哲學危險人物的代表,傅柯展顯了一種哲學實踐的效應。在這種思考下,德勒茲夠危險,我們甚至能確認這就是傅柯與德勒茲彼此親近的基礎。相反地,德希達就不然了,他掉進了某種海德格式的情緒狀態中,或者說,他根本跨越不了主體與良心的古典理論。
我的企圖並非用質疑某個哲學的「危險性」判準的效力,來提高傅柯的重要性。我只單純聚焦在傅柯使用的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概念工具,以吸引注意力。他將哲學研究、權力議題(那些有關公共空間、政治的活動)與現實性互相扣連在一起;就此,我要對傅柯危險觀點的演進與現狀,提出幾個簡短的反思。
傅柯的精神思維其實是危險,或被一個社會「感知到是危險的」。所有可能的倒置點、論述秩序的可逆性、權力關係,一些明顯事務的分歧看法等,我們可以說這些都是某種「裝飾的倒置」,都會被這個社會感知到是危險的,並對某些範疇和個體貼上危險的標籤,所有那些朝向其移動便會引起有關秩序爭論的「邊緣」或界限,尤其是走到了根深柢固的秩序形式之臨界點,便會被視為危險。危險!危險人物到處都有:危險的作家,他動搖了作者的地位,將文章該有的起承轉合寫成一片朝天叫喊。危險的歇斯底里患者,他識破了精神醫學權力的進程。危險的工人,他倔強頑強地對抗工廠的規訓。危險的罪犯,他不屈服於招供的儀式,甚或爬上監獄的屋頂。還有危險的大學教授,他越過了大學教師的規範底線,如滴水穿石般地分隔了種種規訓的界線……。
危險,全都是危險的,因為在所處的時代,展現為唯一、必要、理所當然,與不可超越的,乃是維內所謂的「怪異」,或佛洛依德稱之為「擾人的怪異」的東西。因此,危險首先乃是這在實踐的知覺或諸多實際的再現中導入「懷疑」這個要素的東西。居於拆解合理性的真實狀況中,懷疑的這個要素乃是必要且獨一無二的。所有的人物都是危險,所有的管理都是危險的;有關現存、正當和被制度化的永存能力,這些主題間的某種「可能差異」的不可能性之陳述等,只要稍具疑點便是危險的。支撐著「危險」態勢的修辭表達法的乃是傅柯著名的「而如果??」。而如果,與其說女性的歇斯底里是神經系統的疾病,終究會因醫學進步而被識破與受規範,這會不會只是精神醫學全力發展的倒置效應呢?而如果,離成為現代社會所面對的永遠的危險人物還很遠,罪犯原來只不過是證明著警察大量繁殖的一個必要的建構呢?而如果,從十九世紀起,所謂的性壓抑,只不過是性氾濫無限擴張的倒置呢?而如果,大學與高中的哲學教學,與其是個體自律自主與公民性格的培育,原來只不過帶來支離破碎的思維,像一個堆放雜物的儲藏室,其目的在於讓年輕人更容易適應這個充滿規訓的世界呢?還有,如果這個由大寫字母所尊稱的人,原來只不過是個紋章圖案裡如同動物般的形貌,如同存在我們現行的歷史與哲學沙灘上的刻痕,只要輕風撫過一瞬間就消逝得無影無蹤呢?
因此,在一個充滿秩序的社會中,傅柯的哲學與政治上帶著危險觀點的「遊戲」第一時間便解構了一系列被定義的危險,以展現出它的實用或「實踐」性格。這些危險凸顯了社會與推論的結構,完全改變了危險所具備的負面否定特徵。傅柯不斷地使用同樣的隱晦證明:秩序滋養著危險與災難,並使危險與災難爆發。一九七○年代,針對監獄、不平等主義、西方現代社會中罪犯的形貌與「危險的階級」等,傅柯不斷地反覆提出這樣的理由:為了使規訓、警察、司法與監獄找到足夠的正當性,犯罪是必要的,治安虞犯是必要的、關監那些無可救藥的敗類是必要的。因此,危險完全不是我們所信以為真的那樣;危險是分布、規範和常態化的操作者,是階序化的樣態,也是歧視與必要的排除。這種對危險的使用只與現代或當代社會有關。如果我們以這個角度閱讀《瘋狂史》,我們會發現某些有關瘋狂的「危險」的嶄新知覺,加上其他的拼湊,就成了醫療收容所得以誕生的首要條件。
由此將展開一個有限的通道,而這完全是傅柯的風格(他那種「幾近犯罪」的方式,我們今天已經有點忘了……),帶著挑釁與矛盾的處方——危險一點,再加把勁成為真正的危險人物!形成這個姿態的推論將大致是:既然我們的社會不會發生危險,既然這些都是假設的危險,既然這些圍繞在秩序邏輯周邊的各種爭論,既然所有的權力遊戲都經過精心設計,既然無論使用哪種方式,這些其實都是圍繞在許許多多的危險問題及其爆發之上所作的安排,因此,這難道不是為了支撐一個大學圍牆外的哲學,支援那個以「危險」為理想,並拆除了規訓基石的知識分子嗎?
作個危險人物,努力存在並化身為某個危險,這將意味著處於某種主體稟性,和一個不穩定的立場中。在這個立場裡,我們有最大的機會進行「差異」,擺脫束縛;而此地所展現的也並非某種替代方案或某種「大拒絕」,而恰好是能量倒置的可能性、異議與斷裂。
這是建立在成為危險人物永遠意味著被「意識」、被「標籤」和被「譴責」這件事之上的關係和主體性的遊戲。世界宛如一座舞台,大家應該還記得傅柯這個出現在《詞與物》首章的引述,在他對維拉斯奎的畫的長篇註解中,這個引述其實說明了傅柯對危險的態度。而在《言與文》的第4冊的第781頁中,有一段傅柯在1982年間與一位美國學者所進行的訪談,標題為「真理,權力,自我」,傅柯說:「有些人認為,我是大學生與大學教授智識健康的危險人物之代表,對此,我深感驕傲。當知識界開始以健康觀點進行思考時,那就是說,有些事已經不會再繞回原點了。對他們而言,我是個危險人物,因為我是個潛在的馬克思主義者,非理性主義者、虛無主義者。」
能同時在政治與哲學上作個「危險人物」真是太理想了,但傅柯會在其所選擇的戰鬥中拒絕這點:傅柯所在意的是尋找「擊破」點,那些能暴露出種種美麗的斷裂和響亮的異議的感性地帶:例如,他堅決反對當時蔚為風尚的沙特的存在主義,以及加洛狄的人道馬克思主義的意見,挺身而出,以「不可寬容」的符號為由,批評法國監獄內的種種狀況,並抨擊堅絕不放棄死刑的政府與司法機構。1981年12月,為鎮壓波蘭團結工聯,波蘭的國家領導人賈盧史勒斯基將軍發表宣言採取軍事戒嚴,傅柯嚴厲斥責當時社會黨的第一書記喬斯賓與《世界報》的總編佛維特的回應過於軟弱。「作個危險人物」乃是展現衝突,並在接受對峙洗禮的狀況下建立一個舞台,而這也意味著,重新將生命與意義賦予政治和哲學實踐,並恢復某個早已遺落在學術殿堂和國會曲折的權力遊戲中的價值。
與我們所能想像的相反,危險這個論點的過渡,一如往昔,並非與傅柯思想的接受毫不相關。事實上,長久以來,從他還在世到死後遺著,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傅柯已完成了某種「危險性的計畫」,而這也因此使他被大學哲學體制的壁壘歸類至分裂主義者與狂熱分子(那些以傅柯學說為博士論文的研究者,或被貼上「傅柯」學派標籤的人,真是倒楣透頂!)之列,或簡單地說,被輿論視為了某種左派哲學家,那最令人討厭的「68思維」之殘餘。這也就是說,傅柯不僅危險,而且還成了不可理解,甚至不可信任的。一方面,本世紀初,在政治與哲學領域,當各種政治上的人道-司法和免疫的研究已成為必要,當秩序的邏輯幾乎已不再有任何爭議之時,所有傅柯思想的「情調」已無異於無字天書。一九七○年代,經常出現在傅柯的言談或筆下,有關監獄、犯罪、正義等的說法,如今幾乎都聽不見了;現在這些都不過成了權利、安全和風險預防等的問題。讓我們看看他對於「監獄資訊團體」(簡稱 GIP)的呼籲:
「大家都這麼說:再也沒有監獄了。這些大量批評、講理的人、立法者、技術官僚、執政者等紛紛問道:那您到底要什麼?答覆是:配上哪一種醬汁,我們喜歡被吃掉,這種話不是對我們說的;我們再也不玩刑罰,我們再也不玩刑事懲治;我們再也不玩司法的遊戲了。」
當然,在這段遠離上述遊戲的期間,傅柯思想的所有面向不但產生了某種倒置運動,也變得奇特了起來。這主要發生在傅柯一些文本再版的編排階段(《言與文》,法蘭西學院的講稿);新著作的編排不但顯示了傅柯思想的真實面向,也激起了知識界的無比關注。長期以來,多少因大學哲學空間流放之故,傅柯的研究工作在人文科學和「規訓」領域,以一種少見的歷史嘲諷為代價,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坐落於亞容市的法國獄政學校,每期都有學員提出《規訓與懲罰》的研究報告。在法國的獄政界,越是職位重要的官員,越是會在必要的時候,很機械地背誦《規訓與懲罰》一書中幾個重要的完整段落。談到有關獄政空間,傅柯曾說,「戰役的轟隆聲響」令人血脈賁張……。
傅柯力圖推展的危險哲學或後哲學罕見的「危險的思維」也隨著這些小小的改變而進行了倒轉。目前他幾乎在所有知識分子的刊物上都占有一席之地,毒癮觀察者「重新研究」傅柯哲學、有關愛滋病與高風險行為的報告,諸多的「規訓」在現今都重新受到評價,在這個時代的「現實主義」狀況下,生命政治與生命權力都受到了掌控,這個現實主義以治理性運作來「讓人活」,且其運作與施行可能不全然在黑暗中進行??。
再者,為了紀念傅柯逝世20周年,數年前,巴黎舉辦了「傅柯24小時」的活動,活動由藝術家湯瑪斯.赫雄籌辦,24小時的活動包括電影、展覽、讀書會、專題講座、音樂演奏、戲劇表演,電台節目製作等,混合了學術研究論文發表、情色影像、廉價商品、檔案資料、當年的訪談原音等;這充滿藝術性、文化與哲學的「傅柯24小時」,無論嘲諷挖苦都成功展現了「文化上的稀有罕見」。如同在沙礫中淘金,如果還有力氣與慾望的話,大家各自努力去找回「危險的哲學」中的貴重金屬,希望傅柯的危險還能有個「哲學標籤」??。
傅柯語彙中的「民主」
在傅柯所著的《言與文》第4冊最後幾頁,在有關基本論點的索引,在違法犯罪與非理性間,在大量傅柯式的詞彙中少了一個字——「民主」。在我們這個時代,在「民主」的文字符號被接受的程度廣大深邃到宛如能創造時代時,傅柯基本論點索引中的這個欠缺、空白這個轟然的靜默猶如寧靜天空裡突然發生的一記響雷。
事實上, 這並非《言與文》編輯群的輕忽疏漏——相反地, 他們怎麼找, 也很難在傅柯的字彙裡找到民主、民主的、民主化……。而更嚴重的是,我們會被問道:一個如此龐大的哲學研究,如此關懷身處時代的現實問題,對周遭社會事務介入如此的細密與深刻,這麼專注努力的答覆這樣的問題:「在我們的這個時刻,我們究竟是誰?」這樣的研究著作,怎麼會如此大膽放肆地遺漏了「民主」一詞呢?也許還更嚴重呢:在傅柯豐富的陳述形式與模式中,無論訪談、論述或其他的論文發表裡,他幾乎從未用過「民主」一詞,怎麼會這樣呢?難道,他對民主一點興趣都沒有嗎?
傅柯的哲學研究介入對政治、社會時事的批評,怎麼可能在「問題化」了我們的現時性,尤其政治議題上,根植了許多我們當前現時性的爭議論點時,卻不經過「民主」這道關卡?
在我們所處的當前,所有的一切全然地奉獻在「民主」的儀式裡。在這個新興的民間宗教蓬勃發展的此刻提出這樣的問題的確會令人感到不快。近年來,傅科研究的重新編碼出土,他的學術權威形貌也前所未有的得到了強化:哲學家,「很勉強的民主鬥士」。這讓我想到了哲學研究者勒葛宏的一篇標題名為〈傅柯,民主的哨兵〉的文章。勒葛宏因傅柯的《治理自我與治理他人》與《康德人類學導論》這兩本書的出版而寫了這篇書評。勒葛宏寫道:「我們經常責備傅柯不思考民主議題,且更常見的是,我們對他的鄙視永不厭倦,他的授課講稿編輯成書問世,可讓我們了解,事實恰恰相反,他是對民主的警戒最具洞察力的理論家之一。」
如果還有比我更不慈悲的人,也許能從勒葛宏的書評理解,在我們當前的境況中包藏著某種不能吸收的毒藥。傅柯永遠是個危險與狂熱的人物,他過去被公認的康德派與史達林派所組成的論壇批評得體無完膚,他們打擊的焦點在於傅柯的不理性的和虛無主義者式的尼采主義。這樣的論斷,幾乎將傅柯與所有的「傅柯學」逐出大學校園。傅柯著作的重新編碼,在民主與現代人權主義的條件下,將如一曲優美的音樂伴隨著新書出版,受到盛大且隆重的歡迎,一掃過去在大學校園與當代思潮沙龍內的冷漠疏離。那些討厭的盤算估量,閃一邊去吧!然而,我們談的不是被平反或被重新梳理及刻意修飾的傅柯,真正讓我們感興趣的是被他所挑起的哲學問題,而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深思。
讓我們看看何諾、費希與其他同夥對傅柯所發動的種種指責。他們聲稱傅柯哲學的前提便足以使他成為民主的「政敵」。如果傅柯當時採取的是「民主」的敵對者立場,那麼他理應為這個處於弱勢、矛盾的立場辯護,而且「民主」這個字就應該會出現在基本論點的索引中。不,事情還更加混亂呢!亂得令人不安:在他那現時性思想的狀況和他在法蘭西學院講授的《論述的秩序》等著作中,民主一詞都未曾出現。在傅柯將現時性問題化的諸多行動中:無論在與監獄的關係、1980年代初期波蘭的政治危機、對抗警察的粗魯行為、為廢除死刑、為司法不公奮鬥等的過程裡,傅柯的工具箱中並沒有「民主」這個器械;他不使用它,「民主」一詞在他的語彙裡就無法具體成形。而現代人則經歷著種種的「民主」洗禮;在如此嚴重的落差與對立下,劇烈的衝突也一直存在。我因此認真仔細地重讀了四冊的《言與文》。為避免無意的遺漏,整個閱讀中,經過仔細檢查,我認為「民主」這個詞從未曾以思想的操作者姿態出現。簡言之,如同一個概念出現。更「糟糕」的是,無論是對列寧式或莫拉式的「民主」,傅柯也沒有隻字片語的拒絕或激烈批評,真是個沉重的缺席。民主這個鬆軟且毫無根據的詞,一旦關係到診斷現時或定義政治立場時,對我們來說,便成了某個「有力的字眼」。
而我必須強調的是,在《言與文》一書中,在有關監獄研究的幾個文本裡,我一次都沒有找到「民主」一詞。而在其中,最讓我感興趣的就是「傅柯課程」。在這個精采的課程裡浮現了許多問題,這個完全密封的魚缸的問題,這個論述體制中的斷裂問題,這個論述類型學的異質性問題,如果不是另一個認識論的類型學的話。令我感興趣的是,一個不久前的論述體制不僅已變得無法理解,同時也是難以想像的。當我們進行論述實踐,重新使用真實的陳述生產模式時,這些「有力的」陳述便必須重新編碼、翻譯、並將這些陳述常態化,使其與具正當性的陳述、常識和顯而易見的狀況相容。最常見的是,當「民主」一詞突然出現在傅柯的論述或書寫中時,很明顯地,他乃借用了「他人」,或有時是對手的用語。我在此重申,由「政治」衝突所產生的看法,令我感興趣的程度,還不如傅柯所拋出的挑戰——「批判」,也就是作為批判實踐的哲學。
傅柯的言論中很執拗的一點是,當他被導引至採取這個或那個立場之時,他會說:「我沒興趣」。就算我講的話很冷,我也會很突兀地說,「民主」一詞,傅柯沒「興趣」……
危險哲學家?
我們發現傅柯經常使用「危險」、「危險的」,甚至「危險性」等字眼,在傅柯的各類著作中,「危險」這個字總是不斷出現。傅柯經常將「危險」這個負面的字眼顛覆為正面的;例如他評論有關亞陶的書寫已瀕臨瘋狂邊緣,充滿著危險,他在此其實是歌頌危險。例如在他提到克羅索斯基文章中的那些惡作劇的成分相當危險時,他總是帶著某種正面肯定的意味。再如傅柯談論現實社會中的治安問題時,也使用「危險」這個語彙,但字裡行間卻一點都讓人感受不到危險的威脅。他在不同的文本中都賦予了「危險」正面的意義。傅柯持續將危險隱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