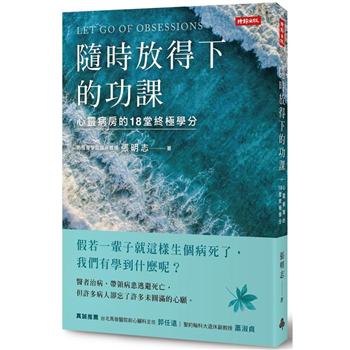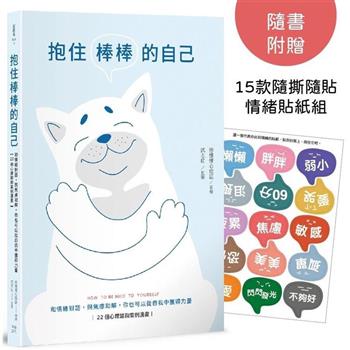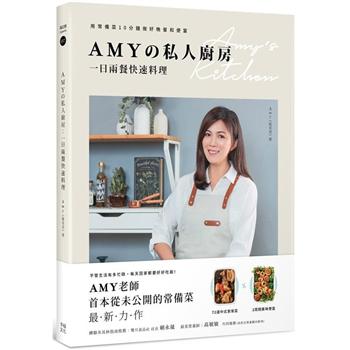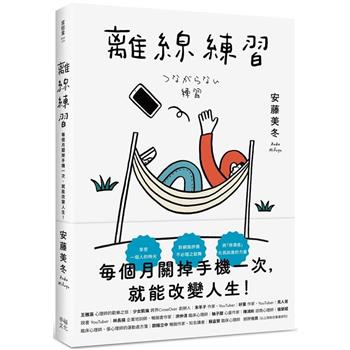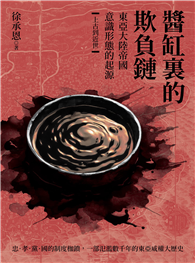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虹的圖書 |
 |
虹 作者:D. H. 勞倫斯 / 譯者:韓梅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06-10-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32頁 / 16k菊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70 |
翻譯文學 |
二手書 |
$ 180 |
二手中文書 |
$ 269 |
中文書 |
$ 269 |
小說 |
$ 269 |
歐美文學 |
$ 269 |
世界古典 |
$ 340 |
英美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虹
商品資料
- 作者: D.H.勞倫斯
- 出版社: 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06-09-28 ISBN/ISSN:9789861246055
-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560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