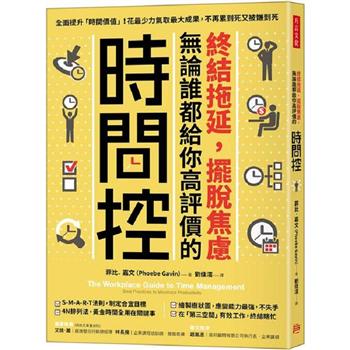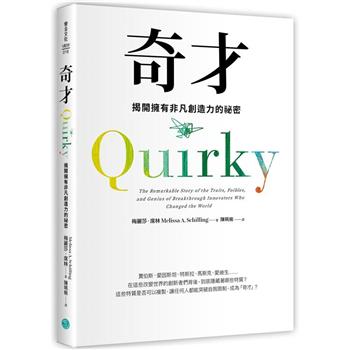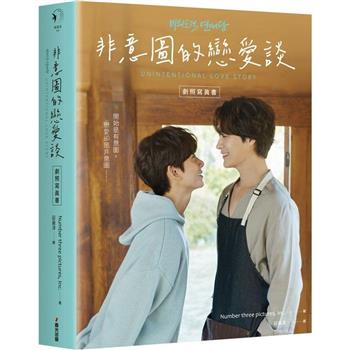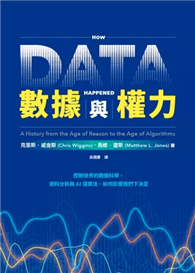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動物農莊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120 |
英美文學 |
$ 153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動物農莊
商品資料
- 作者: 喬治.歐威爾
- 出版社: 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06-08-14 ISBN/ISSN:9789861247144
-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144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