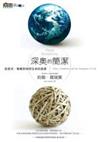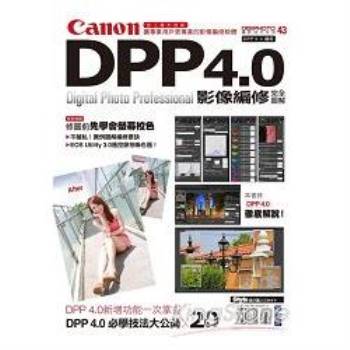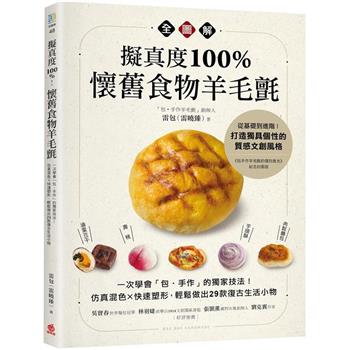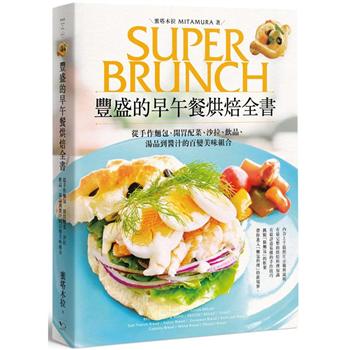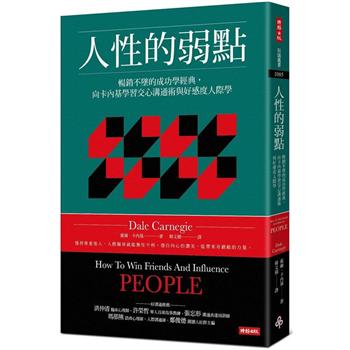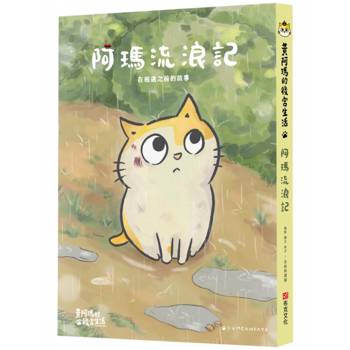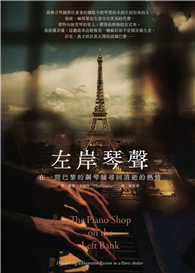序言
複雜的簡潔
我們居住的世界似乎是個複雜的地方,即使存在一些似乎永恆的真理(蘋果總是掉到地下而不是天上,太陽總是由東邊升起而不是西邊)。儘管仗著現代科技的幫助,我們的生活往往仍必須提防突如其來的意外事件。氣象預測既是科學也是藝術;地震與火山爆發隨機發生,難以預料;股市震盪總沒有固定的模式。打從伽利略開始(約從十七世紀起),科學發展的突飛猛進大多忽略了這些複雜的問題,而專注於簡單的部分,試圖解釋為什麼蘋果往下掉與太陽為什麼從東方升起。
科學進步是那麼地迅速,到了二十世紀中葉,所有簡單的問題都有了答案。廣義相對論與量子力學解釋了宇宙在大尺度與小尺度中的運作機制,而對於DNA的結構以及它們在遺傳複製機制中的了解,使得生命與演化可以在分子層次上簡單地被解釋。但在人類尺度的複雜——在生命的層次——依然存在。生命是如何從無生命體中產生的這個最有趣的問題,依然無解。不令人意外,宇宙中最難以用傳統科學探索、最複雜的生物,就是人類。我們可能是宇宙中最複雜的事物,因為在原子這些較小的尺度中,個體以相當簡單的方式彼此互動,而當許多原子以複雜又有趣的方式連接,才會產生像人類這樣複雜又有趣的生物。但這過程不能無限地持續,因為如果愈來愈多的原子結合在一起,它們的整體質量將使得重力壓垮一切的有趣結構。一個原子或是水分子的結構比人類簡單,因為其中只有少許的內在結構;一個星球或是星球內部也比人類簡單,因為重力把所有的結構都壓垮了。這就是為什麼科學能告訴我們很多關於原子行為與星體內部的運作方式,而難以描述人類的行為。
當簡單的問題被解答了,很自然地,科學家會試圖挑戰複雜系統中更困難的問題。雖然早先曾有零零星星針對這些難題所做的勇敢嘗試,但直到強大、快速(以當時的標準而言)的電子電腦在一九六○年代出現後,我們才得以真正了解複雜人類世界的運作。這些新發展在一九八○年代中期之後漸漸引起更多注意,特別是在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的《混沌中的秩序》(▲Order out of Chaos▲)與詹姆士.葛里克(James Gleick)的《混沌》(▲Chaos▲)出版之後。當時我忙著寫作有關舊科學的豐功偉業,雖然也想要了解關於混沌與複雜的概念,但那實在令人頭痛,因此我多半抱持著觀望的態度。
然而,經過了十年,混沌理論沒有消失,也沒有人以容易了解的方式將之訴諸文字,因此我決定自己著手進行,這表示我必須閱讀所有相關書籍,並自行吸收理解。過程中,我發覺它其實一點也不難。相對論與量子力學剛被建立時,大家都以為只有專家才能懂,但兩者都建立於簡單的概念,即使是門外漢,只要不深究那些數學運算也都能理解。而混沌與複雜具有同樣的特性,這點也沒什麼好驚訝的。但當我終於知道它是怎麼一回事時,我還是大吃一驚。我的理解是︰重點只在於某些系統(「系統」可以包含的範圍很廣,像是擺盪的鐘擺、太陽系或水龍頭的滴水)對於初始條件非常敏感,因此初始「那一剎那」的少許差異,會造成截然不同的結果。此外,還有「迴饋」(feedback),迴饋使得系統會影響自身的行為。這一切看來太完美了,簡單得令人難以置信!。因此我請教朋友中最聰明的拉夫洛克(Jim Lovelock),我是否找對了方向:「是否混沌和複雜所探討的一切,只是建立於兩個簡單的概念——系統對初始狀態的敏感以及迴饋?」他回答:「一點也沒錯,全都包在裡面。」
這有點像是說,狹義相對論「全都包在」光速對所有觀測者來說皆一致這樣的概念。這的確是實情,也很簡單易懂。然而,建立於簡單事實上的複雜結構相當驚人,需要一些數學背景才能完全體會。就過去對於不具科學背景的人士解釋相對論本質的經驗,以及明白了在混沌與複雜架構下也是類似的簡單真理,我有信心能以淺顯的方式介紹這個領域。而這個成果正捧在你的手中,《深奧的簡潔》是一本針對一般大眾、以由淺入深的簡單方式嘗試解釋混沌與複雜的著作。本書的重點在於,混沌和複雜遵循簡單法則,基本上就和牛頓三百年前發現的簡單法則一樣。某些論調會讓你以為四個世紀以來的科學努力被顛覆了,然而,這些新發展卻大大不同,它們顯示了對簡單法則長久累積出的科學認知如何能成功地解釋(雖然無法預測)看似無法解釋的天氣系統、股票市場、地震,甚至人類。我也將試圖說服你,混沌與從簡單系統突現的複雜,就快要能夠解釋生命的起源。美國物理學家莫瑞.格爾曼(Murray Gell-Mann)的一句話也呼應了本書前面引用物理學家理查.費曼(Richard Feynman)的猜想:我們在周遭世界所見的複雜行為——甚至在生命世界中——只是「#從深奧的簡潔中所浮現出的複雜表象#」。而支撐著複雜的深奧簡潔,正是這本書的主題。
約翰.葛瑞賓
二○○三年一月
例如,引自羅傑.李文(Roger Lewin)的《複雜》(▲Complexity▲)。
由混沌孕育出的生命
馬自恆
一沙一世界是一種美,它是一種概念的美,神遊於一粒沙的無垠複雜,並不需真的要用顯微鏡把隱藏於平凡的奧妙呈現在眼前。小時候唸過一篇陳之藩的散文,他說「數大就是美」,這也是難以具象形容的美,這種美源自於心靈上的感應或許更勝於視覺上的衝擊。對稱是一種美,「數大」提供了一幅對稱的圖象,像是以單調磁磚鋪滿的大地。但還有一種心靈上的對稱,抽象的對稱,更能感動數學家們。是否存在對稱於一沙一世界這樣的概念?整個世界單純得有如一粒沙?直到電腦發達之後,人們才真正地目睹了這項大自然的神奇。它是一種叫「碎形」的圖案。利用一個非常簡單的式子,可以在平面上呈現出瑰麗的圖形。但比表面上看來更神奇的是,無論將其中任何一塊區域放大,看到的仍是完全相似的不規則圖案。整個花花世界原來只有一條規則!這種動人的美,吸引了無數科學家投入研究。
碎形常被當成混沌的表徵,因為兩者都是非線性方程式的產物。但在意涵上,兩者卻背道而馳。混沌意味了對於機械運作可預測性的否定。而碎形則印證了在無法掌控的複雜之中,仍然存在無比簡潔的秩序。有沒有可能整個宇宙的運作也具有相同的模式?表面上看來異常複雜,但卻埋藏著簡潔的真理?同樣的問題,在歷史上反覆地出現於科學家心中,也是本書作者想解開的謎題。
作者以尋找生命的起源為目標,從銀河系外到動物胚胎,四處探索宇宙間的物理現象。最後終於得到了結論,宇宙間有趣的事物,都是處於混沌邊緣不斷變化、自我調整的系統,包括了最複雜的人類生命。
這本書涵蓋了相當廣泛的議題,包括了「新科學」中的混沌、蓋婭、連結等等。雖然因為內容緊湊,整本書裡能讓讀者會心一笑的小軼事趣聞很少,不是休閑良伴。但對於想了解新科學,或是科學研究之基本理念的讀者,這是一本不容錯過的好書。作者葛瑞賓的知識非常廣闊,是現代科普作家中的佼佼者。除了在書中從宇宙形成到胚胎演化,都做了深入探討,他對科學史也有深入的研究。這些特質,使得他能夠以全面的方式將所有科學進展明白地標誌出來,引領讀者一一探索究竟。如同造訪博物館,任何外行人都可走馬看花地見到一些寶藏,但若有深入介紹,就可看得更加興味盎然。
科普讀物可以在不同層面帶給讀者樂趣。最實用的層面是獲取新知識,尤其是針對明確問題的簡短答案,可以寫在試卷上的那一類。大陸上有一套名為《十萬個為什麼》的讀本,一直是小朋友們探索自然奧祕的入門書,提供各種問題的科學解答。這本書中也有許許多多對大自然奧祕的解答。比方說為什麼小行星帶會形成,為什麼長頸鹿會有大塊的斑點,以及為什麼海洋上可以形成雲層等等。
在另一個層面,讀者也可以透過追隨科學家們的研究過程,分享科學發現的喜悅(與挫折),並進一步品味科學的精神。葛瑞賓的強項在於將科學發展的脈絡連貫起來。透過他既廣又深的知識背景,將新科學中各領域的關係梳理得非常清楚。讀者未必要全盤接受他的結論,也就是所有自然現象的深處,都存在簡單的規則。(其實作者本身也未必有如此的堅持,它是小心求證前必要的大膽假設。)但葛瑞賓在提出相關主張時所引用的邏輯論述,可視為現代科學的主流品味。無論是想了解科學家們的思維方式,或是本身從事科學活動的人,都可從本書中獲益良多。
所謂的「新科學」,或者稱為系統科學,主要探討超越單一事物運作時的(複雜)交互作用。涉及的課題包括混沌、複雜、連結、突現、災難理論等等。它們的突飛猛進和高速電腦的發展有很大關聯。
混沌理論是本書的骨幹。大約於一九八○年代中期,由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與葛里克(James Gleick)出版了兩本關於混沌的著作之後,它更加廣受重視。到目前,有關的理論輪廓已相當清晰。無人否認羅倫玆(Edward Lorenz)發現的混沌是「決定式的」,也就是說在初始條件確知,又有無限計算與儲存能力的狀態下,所有過去與未來都可由計算預測(不考慮量子世界)。當然這些條件不是今日,或可見未來人類所能奢求取得。那麼僅僅將這些完美的條件當成天下掉下來的禮物,在這樣的心智遊戲的條件下,是否能斷言宇宙是決定式的?甚至進一步追問宇宙間是否存在自由意志?這類哲學上衍生出的問題仍然斷斷續續地受到爭辯。但像是交鋒到了「不可預測並不代表不可決定」這樣的深度, 庸俗科學家們加入論戰的興趣並不高。葛瑞賓用了最圓滑也是最聰明的方式面對這問題,他說「預測宇宙最有效的工具就是宇宙本身」。
複雜是另一個主軸。葛瑞賓很大膽地將複雜定位於混沌的邊緣上。複雜和資訊量(或者稱為熵值)息息相關。如果從完全有序的狀態一路變化到完全隨機的狀態,資訊量開始時將一路增加,到達某個極限後,又快速下降。想像你要用電話告訴遠方的朋友自己電腦螢幕上的圖案。如果在完全有序的狀態下,比方說一片純白,很容易用一句話形容清楚,或者說這個圖案的資訊量很少。另一個極端,如果螢幕上是完全隨機的雜訊,雖然世上無所謂一模一樣的雜訊,但並不難確切地將這種景象忠實地描述出來,資訊量也很少。資訊理論是一門新興的科學,由仙儂(Claude Shannon)在三○年代提出。一般研究資訊理論走的是由簡入繁的路子。借用先前的比喻,是由一片純白的螢幕開始,進而研究在上面加入一隻老鼠,接著兩頭牛,再來三隻老虎……。這一路發展的資訊量,不超越我們所能掌控的範圍。典型的應用像是把音樂檔案壓縮,以最少的資訊量達成不失真的目的。但複雜卻是由另一個方向看,從一片隨機雜訊往前追溯,看看在什麼地方才有意義與無意義的分野,並試圖找出它存在的原因。在新興的「小世界」連結理論上也發生類似事件。我個人熟悉的傳統圖論走的也是由簡入繁的路線。光譜的另一個極端,是隨機圖,只有艾迪胥(Paul Erdos) 等少數人留下足跡。直到史特羅蓋茲(Steve Strogatz)與華茲(Duncan Watts)研究了完全隨機圖邊緣之外一些圖的性質,才發現了另一片新天地。自然界的動力系統與抽象的連結模型,在進入不可知的混沌區域前經常表現出了自我類似、冪次律等共同特質。一切只是巧合,或是某種大自然的神祕訊息?這是有待探討的最有趣問題。
這片新科學領域上的討論,常常涉及一些科學哲學的議題。透過對各方說法的探討,可以凸顯一些對科學的反思。在此我們勾出兩個議題。一則因為「新科學」是否代表某種「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是個有趣的爭議性話題。 再則因為「新科學」中眩目術語被濫用的情況最嚴重,使我們覺得有必要做一說明。討論這兩項議題前,有必要簡單說明由波柏(Karl Popper)與孔恩(Thomas Kuhn )開創及衍生出的科學哲學。
波柏常被視為邏輯實證主義的開山始祖之一,但他不承認(孔恩也有同樣的困擾,認為大眾曲解了他們的思想)。波柏以他對科學假設必須建立於「可證偽性」(falsifiability)上的堅持而著名。「可證偽性」的確和實證主義早期主張的「可驗證性」(verifiability)有些不同。早期實證論者主張凡是不可被驗證的陳述沒有意義。因此造物主是否存在是無法被驗證的陳述。但波柏主張任何陳述都可以被接受,前提是提出陳述主張者必須同時指出這項陳述將如何被證偽。這種觀點擴大了科學探索的範圍。比方說大霹靂的宇宙起源論,以狹義可驗證性而言是無意義的,因為無從得知宇宙是否起源於某種形態的大霹靂。但依波柏的要求,提出大霹靂論者除了解釋已知的科學觀察,還需要指出它可被推翻的實驗方法。雖然不是很正式地,但在一九六五年由彭齊亞斯(Arno Penzias)與威爾遜(Robert Wilson)發現的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恰好吻合了哈伯式大霹靂論的計算數據,因此在證偽的考驗上通過了重要一關。 伴隨波柏主張的,是一種科學的民主。針對單一自然現象,任何論述都可以被提出,它們的價值取決於其理論所附帶之可證偽性,隨著科技發展,類似不同的物種彼此競爭,而天擇之手來自社會共識。問題在於,這裡的「社會」可以指的是科學界,但在民主(民粹的兄弟)口號下,又未嘗不可無限擴張。因此波柏以及他的門徒被後現代學派奉為神祖也就不足為奇了。
孔恩主張科學藉由一連串的「典範轉移」產生變化(不必然是一直進步)。他研究科學史,產生頓悟,發現現代人之所以覺得亞里士多德的科學觀幼稚,只因為我們並不是以亞里士多德的角度看世界。若是經由心智上的「格士塔轉換」(gestalt-switches),我們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的觀念完全符合當時的常態科學。用演化論來做比喻,孔恩主張科學演化是「間斷式」而非漸近式的。
葛瑞賓在廣受好評的《科學家》這部詳細記錄人類科學進展一書的最後,特別地附上一段結語,很謙虛地承認他的科學史觀可能被視為「守舊,甚至反動的」。但他明白指出,排斥孔恩的科學史觀是他的選擇。在這本可視為「新科學史」的著作中,他再度試圖以相同的視野說服讀者。
社會科學(當然,所謂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或是硬科學與軟科學之間,並沒有明確界線,在這裡我們姑且用歷史學做為社會科學的代表,以物理代表自然科學),依卡納普(Rudolf Carnap)的說法 ,由於涉及的條件難以掌握而複雜,因此取得共識的過程比較曲折。早有學者指出自然與社會科學分屬兩種文化。孔恩著名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與其套用在不同時間的同一門科學,還不如用來看待不同學門之間的差異更為恰當。想像有一個大房間,其中裝滿了人類文明所有的知識。如果邀來一批社會學者,試圖就一個問題達成共識,或許會得出一個結論。這時再請另一批有同樣學術背景的學者討論同一問題,有可能得出的結論與前一組得出的大不相同。在社會科學形成共識的過程中,主觀判斷所佔的比重遠大於在自然科學中。因此參與討論者的文化背景和個人性格,都可能影響討論過程與達成的結論。但自然科學,尤其到了二十世紀,幾乎看不到「群體的主觀」。以方才滿載所有人類知識的大房間做比喻,前往進入討論的兩批自然科學家,鮮有可能對同一問題做出相左的結論。隨著時代演進,科學家才可能做出巨大差異的判斷,但不是科學家改變了,甚至不是科學家的科學觀改變了,而是房間裡的知識不斷累積變化,自然科學家永遠只是針對這些資料調整步伐,並透過它們(包括科學觀測與理論)間接進行「對話」。如同葛瑞賓在本書中舉的例子,如果每隔一百年為房內的知識寶藏做一次總結,我們確實可以看到一遍又一遍的典範轉移。但如果每年檢視一次,那麼所有的變化都可找到源由,無需驚動「格士塔轉換」。如果將物理換成更「硬」的數學,這種現象更加明白。二十世紀的大數學家哈地(G. H. Hardy)論及兩千年前古希臘的幾何數學家時,宣稱他們感覺上就像「別所大學的同行」。兩千年的典範不轉移!
科學上許多術語出現在日常言談中未必是壞事。有人聽到混沌理論立刻聯想到「蝴蝶效應」,形容左右為難就用「囚徒困境」,生活上增添一些語言色彩也不錯。但若以一知半解的科學術語自抬身價、著述立論、喊盤定調,就令人坐立難安。有一群不太懂科學的人(不妨以「後現代主義者」稱之,「後現代」沒有明確的定義與界限,但不難從特定對象使用「顛覆」、「解構」等眩目名詞的頻率看出來)經常利用這些名詞字面上的意義亂做文章。後現代人有時還引用像是「非線性」這個有特殊數學涵義的名詞。如本書中敘述得很清楚,混沌理論中的「非線性」指的只是某一數學函數之性質,一點不多,一點不少。但在許多喜歡玩語意遊戲的後現代人口中,非線性代表了某種突破傳統單線思路的全方位思考模式。看了這本書,如果可以增添讀者日後捧腹大笑的機會,是譯者最大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