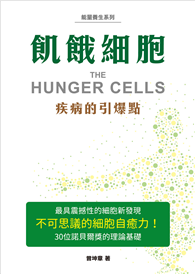內在的酷兒 卡蘿•昆(Carol A. Queen)
最近我開始為自己的性傾向感到擔憂,雖然這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在金賽量表中,我橫跨好幾個位置,甚至在克萊恩量表(Klein Scale)1中也是一樣。任何性學專家都會馬上下診斷說我根本是個雙性戀,但是,我無法確定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我認識許多雙性戀者,他們看起來和一般異性戀沒兩樣,而有些是同性戀者,而有些從外表完全無法分辨。他們是真的雙性戀者嗎?擁有一個性傾向看來似乎很重要,每當有人質疑我的時候,我只能以我所屬的社群、文化與觀點來向他們解釋,是的,我知道傅科(Foucalt)2說,在「性傾向」這個概念被創造出來之前,人們或許根本沒有所謂的性認同,但是,我們現在有了,性認同立基於我們愛戀與慾望的對象,而這是有用的,就像你知道剛認識的新朋友是天蠍座或是民主黨一樣。甚至,我們的性傾向有助於確認我們的性慾,這是我非常想要確認的。
在發現對女人有性慾之前,我不太願意說自己是雙性戀。而現在我憂慮的是,我似乎又不太典型。我使用「女同志認同的雙性戀者」這個詞來稱呼自己(或,當我想要更叛逆一點,我會使用『男同性戀認同的女同志』),但幾乎沒有人懂我在說什麼。
我希望能夠表達我真實的人生,我的性,而不需使用那麼隱晦生澀的字眼。但目前可用的字彙卻限制了我。我對於這些限制,這樣一個摒除異己的世界觀感到不耐。我需要歸屬,需要被命名。
十六歲時,我到德國去做交換學生,為了逃避一段早熟的戀情他是年齡大我兩倍、有妻小的學校男老師。我離開城鎮,不理會門禁,每天都在女子學校裡鬼混。離開德國前,我愛上了一個狂野的,有雙貓般眼眸、看起來似乎從不在家裡過夜的女孩;一個教我法文的寶寶T,她是我男友的姊姊;一個我每天在公車上遇到的女人;以及一個從英國來的,把我當朋友看待的學校老師。
回家之後,同樣的,沒有一位同學可以逃過我的凝視。我已然瞭解情慾中的差異性,但對於同性愛戀這部分的衝擊,我卻沒有做好任何準備。直覺上,我知道我已踏上了這片領土,但我卻沒有把心中的混亂告訴任何人,直到一位新老師來到我們城裡,他是一位男同志。他給了我老式男同志的教育,佐以大量王爾德(Oscar Wilde)的作品,以及古典男性情色文學。這些已足夠讓我混淆了,雖然我初萌的女同志傾向沒因此而退卻,卻也讓我注定終身與男同志種下不解之緣。這些情色作品以其他男人永遠無法企及的方式,撩撥起我的,以及他的狂野。在這個小小的城鎮裡,我們形成了珍貴的共同體關係,讓我幾乎忘卻了他的性別。
進入大學後,我與一位美麗的年輕女子陷入熱戀,我告訴她我愛她。我出櫃了。她很高興得到這樣的關注,只要我繼續和男人上床,不向她提出性邀請就好(這對我一點問題也沒有,因為我根本不知該如何向女人提出性要求)。她說,她知道跟我在一起一定會非常開心,只要,我是個男人。但她賜予的吻卻給了我遠大於王爾德更強烈的衝擊。擁抱她,親吻她帶來的熱情遠超過了我的想像,我渴望與她做愛(她從來不曾答應),直覺告訴我,我已經具備完全的能力可以讓她盡情享受魚水之歡。我知道,我身上流著女同志的血。
所以,為什麼我還繼續跟男人上床?為了有趣,為了幾乎完全不費力的性。比起處理對女人不知該如何表達與掌控、又缺乏出口的熱情,和男人總是簡單的多。
我加入了雙性戀女性團體。其中唯一跟我比較親近的是一位女同志。我修了同志研究的課,對我的雙性戀傾向獲得一點點幫助,而大部分課程卻支持我相信,我正在經歷一個「階段」,而這是終結混亂狀態,向前推進的起始點。我協助創立了一個青少年同志團體,與我的新室友戀愛。她和我的關係在她的異性戀情史中如同螢幕上的小光點,我們的性關係也只佔我們相處極小的一部份。我愈加地疑惑了。也許我根本不是個天生的女同性戀,儘管我感受到自己對女人的熱情。
後來長達兩年以上,我偷偷和一位甜美的年輕男同志上床。當我談到雙性戀,這男孩焦慮地笑笑。比起同志每天上演的劇碼——十幾歲青少年被逐出家門、被他們年長的愛人拋棄、偶爾有自殺念頭又不幸成功——雙性戀似乎難以被認為是個值得探討的議題。這禁忌之吻是我們同志社群裡彼此認同的一種默契表達,即使我們知道得低調一些……至少那和女校裡的同性性幻想一樣不合法。我正在內化一套新的規範,「女人不愛男人」是這個世界裡的法則。
當我終於愛上了一位真正的女同志,疑惑卻愈趨嚴重。連續好幾年,我們的性愛熱烈而狂野,而我們也都各自有其他的情人,我甚至還跟其中一兩個女人過夜。
我仍舊和男人上床。當然,是不定期的,大約每一兩年一次吧,只是為了提醒自己那是什麼感覺。不可思議的是,我越接納自己是個同志,和男人上床就變得越有趣!
我的情人是個自由派。「妳根本不是雙性戀,」她很確定的告訴我,「妳只是個偶爾跟男人上床的女同志。」我想社群裡的其他人,一定更無法理解。我留了迷人的超短小平頭,身穿牛仔褲和無袖上衣,不刮腋毛,我成功地蒙混過關,但這祕密地越軌,讓我在女同志世界不堪其擾,似乎我得設法讓時光倒流,尋回女校時代的同志熱情。我得面對事實了:我只是個行為反常者。我開始從中得到樂趣。
很清楚的是,對傳統女同志來說,如同中世紀傳道士所認為的,所有叛亂的種子都埋藏在女性的嬌媚之中。我買了十三年來的第一個胸罩。我蓄長髮;穿裙子;塗口紅。當我們做女校那檔事時我得把白色蕾絲藏好,以免讓女伴壞了興致。我把那些東西和皮製品混放在一起。女友開始焦慮了。我希望可以變得超級怪異,以致於根本沒人會注意或在意我在做什麼。
當然,首先,我得克服心理障礙:我正在背叛同志社群的規範,冒著可能被我的心靈歸屬驅出家門的危險,只為了特立獨行。我曾經是同志社群的領導者,也是在我居住的小城市中公開露臉的同志之一,我非常擔心會被抓到和某個男同志(或是更糟)上床。面對曝光恐懼,酷兒唯一可做的,就是出櫃。然而,這個培養勇氣、自我壯大的過程是緩慢的,比起當初離開那個充滿危險、遊戲與過時角色扮演的異性戀社會,我感受到的恐懼要大的多。而更糟的是,即便要出櫃,我的位置到底是什麼呢?
我知道我並非孤單一人,這就是為什麼我要說出自己的故事。我們無法被歸類為異性戀或同性戀,我們將金賽量表由異到同的連續體*,具體地呈現出來。雙性戀者從0,異性戀的彼端出走,向6,海洋的另一端之前前進,在尚未抵達美好的同志棲息之地前,我們將不會再回歸那毫無曖昧模糊的乾枯之地。當然,我們之中有些人,就直接向那端游去了,對其餘的人來說,或許這個旅程的本身,而非目的地,才是真正重要的。
我痛恨聽到別人說,「妳只是還沒有打定主意而已。」每次性愛我都做出選擇。我選擇榮耀我貪婪的淫慾低吟。我選擇魅惑的顫抖與愉悅的保證。女人的私處、男人的那話兒、眸中的慾火。
我的伴侶現在是個男同志,喔,不,老天,我們當然不只是朋友。男同志與女同志成為情侶,這是同志關係嗎?但是當人們問我是否是雙性戀時,我仍舊不爽,我感覺自己就像男伴把到的那些想要被上的「異」男一樣,非常荒謬。
我思考這些東西長達十五年。沒人能把這件事弄得更容易些。我屬於並認同一個對抗恐同戰火的社群—他們終究可以宣稱「同性戀是美好的」,卻發現雙性戀太過困難,太接近異性戀、太令人混淆以致於難以讓人擁抱。雙性戀者焦慮地夾在中間,就像是小孩聽父母(異性戀和同性戀)吵架一樣。我們自我防衛說,我們基本上跟大家都是一樣的,性真的只是性而已,跟誰並不重要,這有點像是在戰火中的烏托邦論調。
但事實上烏托邦並未到來,戰火持續延燒。我搬到大城市,遇到了許多雙性戀認同的人,但他們卻對同性戀恐懼的瞭解非常有限,因為他們多半是以異性戀生活為核心再向外發展出同性情慾。我無法在他們之中找到歸屬感。在同志世界裡開疆闢土,能夠瞭解恐同症並勇敢面對圈內恐異氛圍的人,似乎才是我的族類。
要討論「恐雙症」,我們得先分析「恐同」與「恐異」症候群。我們必須瞭解,許多同志必須為了避免被塞入一個並不符合的模子裡而奮鬥,而他們許多人仍對此充滿防衛,充滿恐懼與憤怒。
我們也必須瞭解患有恐同症的異性戀者,酷兒對他們來說是古怪的。他們也沒錯。與男人的性關係並未減低我的破壞性,甚至稀釋我的女同志血液。我大概無須高唱新世紀已然到來,大家本質皆同的論調,我運用雙性戀的智慧穿越邊界,破解密碼,帶回了這個社會用來監禁我們的大量祕密訊息。缺少了這樣的知識,我們將永無機會跨越男╱女,同性戀╱異性戀,階級、膚色,這些我們生來既有的藩籬。
正是我內在的酷兒性質給予我力量,讓我看到這些限制,並跨越它們;讓我質疑那些別人告訴我們的謊言,關於何謂女人,何謂男人,我們應該如何適當地互動……好女孩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我們每個人內在的酷兒性質為了愉悅與改變而大聲疾呼,永不被馴服規化,在創造新事實的過程裡渴求發言權。
在女校裡對班上同學的凝視,慾望與客體混雜成認同,只不過是觀看這個世界最初的方式,那是一個我的文化教育從未教導我,讓我準備好去面對的世界。異性才可以是愛慾對象的假設,就這麼被擲出了窗外。在與女人的關係中,角色的流動性又提出了另一個問題:為什麼不拿這樣的知識,這樣的存在方式,發展與男人的關係?誰制訂了我們應該如何的規則?為什麼我們這些有豐富經驗可汲取的人,必須被這些角色規範所玩弄?
女同志女性主義者對於女人是什麼以及如何行動,對我來說是有意義的,但我不認為我從事異性戀關係,即便我和男人在一起。相反的,我從不買異性戀神話的帳,說什麼「男人與女人大不相同以致於無法全然親密」,因為這暗示了「男╱女相反」的二元對立。我們每個人所有的差異與相同是非常廣泛而豐富的,它們的交互作用是所有關連交織成的網絡。從這樣的複雜性中根本難以創造出合宜的角色;當我們瞭解彼此之後,自然就會即興創作。
我想要榮耀並分享我的祕密。如果可以形成一個雙性戀社群,而無須藉由與相對的「他者」來定義自己,也許在那裡我會找到出櫃的棲息地。但直到現在,家不是處所,而是一個過程。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另一個衣櫃:雙性戀者的生命故事與認同的圖書 |
 |
另一個衣櫃雙性戀者的生命故事與認同(96/6) 作者:Loraine Hutchins,Lani Kaahumanu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07-06-08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64頁 / 14.8*21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38 |
社會人文 |
二手書 |
$ 320 |
二手中文書 |
$ 379 |
LGBT平權書展 |
$ 379 |
社會學 |
$ 379 |
社會哲思 |
$ 422 |
中文書 |
$ 422 |
兩性關係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另一個衣櫃:雙性戀者的生命故事與認同
我愛男人,也愛女人,為什麼我只能選一邊?超過七十位雙性戀者訴說他們的故事!
雙性戀者,從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如此生活著、愛戀著,然而,我們卻從未被正確的命名。現在,是讓雙性戀者發聲的時候了,用我們自己的聲音,而不再透過專家的詮釋。
章節試閱
內在的酷兒 卡蘿•昆(Carol A. Queen) 最近我開始為自己的性傾向感到擔憂,雖然這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在金賽量表中,我橫跨好幾個位置,甚至在克萊恩量表(Klein Scale)1中也是一樣。任何性學專家都會馬上下診斷說我根本是個雙性戀,但是,我無法確定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我認識許多雙性戀者,他們看起來和一般異性戀沒兩樣,而有些是同性戀者,而有些從外表完全無法分辨。他們是真的雙性戀者嗎?擁有一個性傾向看來似乎很重要,每當有人質疑我的時候,我只能以我所屬的社群、文化與觀點來向他們解釋,是的,我知道傅科(Foucalt)2...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Loraine Hutchins、Lani Kaahumanu
- 出版社: 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07-06-05 ISBN/ISSN:9789861248790
-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464頁
- 類別: 中文書> 心理勵志> 兩性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