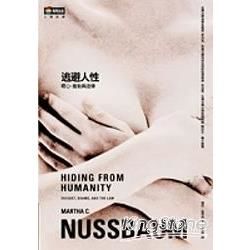〈推薦序〉
客觀理性的背後——從人性的剖析到律法的觀照∕林志潔
二○○七年初,我在國立交通大學開設了一門通識課「Love, Sex and Law」,中文課名叫「愛情的法律學分」,我將這門課分為財產篇、婚姻篇、分手篇、性愛篇等主題,就不同議題所涉及的法律進行探討,我的聽眾是一群理工科為主、男生居多、樸實敦厚但沒有任何法學背景的大四學生,我希望這門課能讓他們在踏出校園前,對愛情、性,以及相關的法律具備基礎的認識。
當我們的主題即將進行至「性交易與法律」的議題時,我預備邀請日日春公娼協進會的工作人員來播放廢公娼及抗爭經過的紀錄片,若有時間,我也打算舉辦一個小型的座談。然而,就在我向學生宣布此計畫的隔週,一張未署名的便條紙從教務長室轉到通識中心主任,又從通識中心主任轉到我手中,紙上寫著:「教務長您好,本校有門通識課『愛情的法律學分』,老師要請日日春的妓女來演講,讓人感到不適,請教務長轉告老師。」
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位認真教學、想帶給學生不同觀點的老師,看到這樣的訊息都不免會心情低落。同事們有的勸我打消此意,因為擔心寫紙條的人會繼續申訴,屆時我將落到得至教評會為自己辯護的局面;至於通識中心和教務長室,則表達支持老師教學及學術自由的理念,不認為我需要做任何處理。我考慮了一天一夜,決定按照原訂計畫請日日春協進會的公娼阿姨來放影片,但我也決定直接在課堂上處理這個「便條紙事件」。我在上課時宣布自己接獲這樣的一種反映,由於紙條未署名,無法確定究竟是否為我的學生,我發給每位同學一張紙,請他們寫出對這樣的課程安排的意見,當作一次不記名的實證調查,希望了解同學們的想法。大家都交了,多數的人認為這樣的安排很好,少數貼心的學生還另外寫上對我的鼓勵與安慰。沒有任何人——至少在收回來的不記名的紙條上——覺得這樣的安排會「不適」。課程照常進行,座談也相當的成功,同學從紀錄片與公娼阿姨的故事中,用過去不曾想過的角度重新反省所謂的法律和正義。
在得知商周出版即將出版瑪莎?納思邦(Martha Nussbaum)教授的《逃避人性:噁心、羞恥與法律》一書並邀請我寫序時,我立刻聯想到這張無名的便條紙。不論這張紙究竟是何人所寫,紙條所呈現的想法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教材,完全呼應了納思邦教授書中的觀點:羞恥與噁心,不該、但卻往往成為法律規訓及懲罰的源頭。
當台灣的「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條做出「罰娼不罰嫖」的選擇時,背後的理由難道僅僅是為了善良風俗的維護?若認為嫖妓行為該被遏阻,為何處罰的不是在經濟上較為強勢的買方(嫖客),反而是弱勢的賣方(性工作者)?立法者或許不願承認,真正的理由可能是沒有說出口的情緒:和嫖客相較,妓女的存在讓人覺得「不適」——娼妓的身體盛滿不同男人的精液,是種不潔污穢之物,娼妓是一種低等、污名的壞女人,是可恥的行業——所以成為處罰的對象。這種噁心嫌惡的羞恥感,亦即我所接到的便條紙上所謂的「不適」感,恐怕才是罰娼不罰嫖的核心思想。
問題在於:為何一位性工作者會讓人感到「不適」?而這種「不適」是否足以成為處罰某一種行為或族群的正當化事由?
納思邦教授在這本書中,提出有力而清楚的主張:對特定族群的噁心和嫌惡,不應該成為法律懲罰的理由。她先以「情緒與人性」作為開場,挑戰「法律是客觀公平理性」的神話,認為人性與情感,往往和法律有著深度的糾結。以政治自由主義和基本善為前提,納思邦教授舉刑法的故意(mens rea)、正當防衛的抗辯(self-defense)與量刑(sentence)為例,呈現出在這些法律原則的思考上,情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納思邦教授接著運用大量的精神分析、心裡學、歷史資料、以及社會學的觀點,分別說明「噁心」與「羞恥」的概念,並對兩者在法律上該有的省思進行辯證。納思邦教授認為,噁心和憤怒不同,噁心是一種「對自我污染的排斥」的情感,與憤怒所針對「錯誤」和「傷害」不同,噁心雖然能引導我們遠離某些危險,但在法律上,它只該在某個狹窄的、對身體環境有所危險的法律領域(如公害法),提供某些行為的建構性判準,而不能成為將弱勢團體或個人邊緣化的工具。而「羞恥」也有類似的問題,固然羞恥有時可能在道德上屬於有價值的情感,而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扮演某些建設性的角色,但羞恥也容易被多數群體誤用成為對少數壓迫及污名的手段,如對同性戀、娼妓、身心障礙人士予以差別次化的對待,因此我們必須強烈地堅持個體自由的權利,並堅定保障所有公民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
簡言之,納思邦教授主張禁止以噁心作為處罰特定群體的理由,並要求國家要創造援助的環境以保護公民免於羞恥,防弊的方式包括通過禁止人民歧視某特定族群的「反歧視法」(anti-discrimination law),或是制訂「仇恨犯罪法」(hate crime law),將那些出於憎恨的主觀要素而傷害其他族群的行為,加以刑事處罰。誠然,在定義何謂「憎恨的主觀」上並不容易,但納思邦教授認為,區別的重點在於該行為是否因被害人具備某特種特質所致,因此,若一個扒手竊取了某個回教徒的錢包,並不因此強化或鼓勵對回教徒的攻擊,那麼被害人雖具有回教徒的特質,但該行為並不屬於仇恨犯罪;反之,若一個犯罪行為直接衝著回教徒(或同性戀、或原住民、或其他移民族群、或性別、或職業)而來,並散布一種攻擊特定族群的訊息,則應被歸為仇恨犯罪而加以禁止,以保護公民應享有的平等尊嚴。
如同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觀察,法律的有效性並非在其強制性,而是在人民對法律的尊敬與服從,這種尊從的源頭是「權利」,由於權利賦予了法律道德性,使法律產生權威,使人民願意尊重法律、服從法律;而在所有權利中,最重要的便是平等權,由於多數作為社會的強勢者,往往成為邊緣化、差異化、歧視化少數的推手,因此國家更須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民,使個人享有不受歧視的尊嚴與保障。納思邦教授的論述雖是為了美國的法律而寫,但在台灣的環境來看,卻也產生極大的意義。每個國家面臨的困境不同,台灣有台灣必須解決的課題。
台灣受到長期的殖民,而殖民政府往往先以差異化對待殖民地人民,再以同化主義將母國文化強加在殖民地上,灌輸人民單一的、以母國文化為主流的價值觀。久而久之,本應充滿海洋多元文化的台灣及台灣人民,逐漸習慣了單一型態的思考以及文化脈絡,處處可見強勢族群主流文化的霸權:戒嚴時期對台灣文化的打壓在政黨輪替後轉變為對外省族群攻擊;對外交流開通卻對外籍配偶或勞工不斷貶抑;異性戀者對同性戀的打壓、身心健康者對殘障或疾病者生存需求的漠視;女性的經濟、勞動條件、社會地位、甚至人身安全,長期無法與男性平等,而男性的沙文主義文化,則不時表現在言語文化或是意象中……。當社會的發展已經無法回到一元,但人民的心態仍然停留在一元,噁心與羞恥便很容易成為標籤化與污名化的工具,如果國家在此時非但未能避免這種將少數人次化的危險,反而利用噁心與羞恥製造對立、污名、階級與所謂的異常者,這種行為與殖民政府又有何異?
回到便條紙事件。如果寫紙條的人,能夠理解台灣色情行業的發展歷史,了解社會不同階級生活的樣貌,看到所謂的「公娼」是一個真實存活、站在眼前的女性,就像鄰家的大嬸或阿姨時,有沒有可能會改變他最初產生的「不適」的想像?我認為有可能。納思邦教授在書中寫道:「如果平等尊重真的想要獲勝,並指引制度與個體行動者的行為,一個自由民主體制必須將這種任務承擔起來。」而我認為,體制是制度性的承擔,教育則是實踐這個承擔的根本。所謂的道德情感不就是從我們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甚至職場教育和社會教育所形成的嗎?納思邦教授在最後也寫道:「教育人民憐憫,憐憫在經過良好教育後,可以為法體系的各個層面提供良好的引導,尤其是涉及闡揚基本權的場合,憐憫可以也通常成為對於因遭受障礙而功能範圍被削弱的受難者的勇氣及能力的欽佩。」換言之,正因為有便條紙上面所呈現的想法,所以這樣的課程安排及教育便顯得更為重要。
你可以不同意納思邦教授對政治自由主義的分析,可以質疑人的感情難以如此清楚的區別為:噁心、憤怒、羞恥、仇恨,也可以挑戰所謂仇恨犯罪與言論自由的界線問題;但是不可否認的,納思邦教授開啟了觀察法律的一種新的角度。從人性與心理的層面,解構「理性客觀的法律」背後所蘊藏的情感與投射,讓我們更清楚地發現人的脆弱與規範的動機。噁心和羞恥雖不可能從人類經驗中完全去除(事實上,納思邦教授也並不做如此的主張),但在法律的界線及國家的政策上,要如何減少噁心和羞恥的入罪化行為,消除滋養歧視、仇視或偏見的環境因素,有效採取反歧視的規範,教育人民與社會建立尊重多元的觀念,都是當前的台灣需要努力的方向。
二○○四年此書剛出版,我正在與我的博士論文奮戰。由於書中充滿大量的精神分析素材,當時的我花了一番功夫才得吸收。三年後,我已經回台灣任教,很高興商周出版找到好的譯者,將全書完整譯出,讓國內的讀者也能閱讀到這本獲二○○四年美國出版協會法學類專書大賞的經典作品。每個人讀書所得各有不同,對我而言,人性有其不完美之處,人所創造出來的律法亦然,對於這種不完整性的坦白,並非是對人性的攻擊,而是一種反省和追尋高貴情操的動力,是創造一個更好、更自由、更多元的社會的起點,這是此書在我寫作博士論文時給我的最大啟示,也是我至今奉行不渝的信念。希望這本譯著的問世,能帶給法學界不同的新觀點,也期待台灣在反歧視的多元化上,能一日比一日加快。
(本文作者為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推薦序〉
情感與法律之間關係的論述∕李茂生
只要上網以簡繁體的網域為限查詢一下Martha Nussbaum,就可以知道這位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在華語圈是多麼地有名,不過這也僅限於倫理學或政治哲學的領域,牽涉到法學時,頂多是少數法理學專家會留意到這位女士的存在。慚愧的是,我也是不知瑪莎.納思邦(Martha Nussbaum)存在的法學研究群的一員。當然我可以藉口說我專研的是大陸法系的刑法學,而輔助性的哲學知識也偏向於歐陸的論述,且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若不是我的學生翻譯了這本書並請我寫推薦文(主要可能是因為我的專攻是刑法學),則我可能一生都不會接觸到這位大名鼎鼎的瑪莎.納思邦女士的論著,不知美國名家的存在一事,是非戰之罪。但是這樣的辯解也只會透露出我偏狹的眼界與不用功之處。在看完譯文後,這種的羞愧感更加深化,不過同時不服輸的彆扭又讓我對於本書有著不得不吐的不滿。以下我將忠實地在推薦文中表達我的羞愧與不滿,讀者就將我的羞愧當成對於瑪莎.納思邦女士這本書的讚美,並將我的不滿當成是碰到趨近完美者時不完美的人的怨憤即可。
瑪莎.納思邦於本書的起頭開宗明義地論及慾望、情感與心情這三種人類心理間的區別,並據此將論述限縮在會直接影響法律運作的人類情感。當然,聰明的瑪莎.納思邦沒有直接了當地立即深入她所欲談論的噁心與原始羞恥的情感,反倒是透過一般人較容易理解與接受的「憤怒」,展開情感與法律間關係的論述。研習過法律的人應該立即會查知,於此所謂的「憤怒」不外就是義憤殺人罪中的「義憤」,並無意中就接受了瑪莎.納思邦所提出的觀點,此即所有的人類情感都會與對於事物的人類評價性認知有關,而這個評價性認知是被建構的(這點牽涉到我對於本書的一點小小不滿)。更巧妙的是,瑪莎.納思邦於討論憤怒時所提出的事例,其實僅是外表與憤怒有關,但實質上卻是與其後她所欲討論的噁心相關的案例。
之後的幾章論述,雖然由法律人的觀點而言,可謂是雜亂無章,有時討論立法,有時討論司法程序,甚至稍稍觸及矯治領域,表面上看似毫無章法可言,但事實上這僅是從法律人自以為是的觀點所為的膚淺觀察而已,瑪莎.納思邦於本書中所舉的刑事法的例子都只是些例證而已,其論述的主軸是在噁心與羞恥,而副軸則是差異、排除與污名化。
排除弱小、污名化奇特人氏,藉此彰顯與肯認「正常人」的存在一事,是很簡單的道理,人人都會說(我在教監獄學時,幾乎一整個學期都在說這件事情),不過能夠更深入從精神醫學以及心理學的觀點闡明這種作為的原始根據,則是博學多聞的人才辦得到,而瑪莎.納思邦正是在本書的論述中充分地展現了她的才華。她說我們這些健全的人因為懼怕人類的動物性與必死性,於是產生噁心情感,並將這種情感投射到污穢、不潔的人(或人種)身上,同時我們也懼怕在一些人身上看到自己原初的脆弱性與不完整性,於是強裝堅強(其實是回歸子宮),並把一些依賴性高的人標示出來,排除於社會之外。在看多了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身體與權力的規訓,以及亞干賓(Giorgio Agamben)的神聖之人、例外狀態等複雜難懂的論述後,這類簡潔的美式論述真的會有令人驚豔的感覺。
或許台灣對於同性戀、人獸交等議題不太熟悉(至少我國沒有將這種行為入罪化,而且就像人獸交的的議題一樣,我們立即以簡單一語「學術自由」即將議題打入冷宮),但是在看到最近我們偉大的公民或公僕們對漢生病患者的粗魯與冷漠後,應該會有些感受吧。而這種的感受正是瑪莎.納思邦所企求的。
在論完人類的本性後,瑪莎.納思邦並沒有簡單地結束論述,其發揮了美國人樂觀的精神,提出了解決的方案。她說噁心的情感也有正面的意義,這種情感可以讓我們遠離危險,而原始的羞恥感也可以昇華到積極的、反省的羞恥感。據此,瑪莎.納思邦主張應該採取一些救濟的方案,諸如失業救濟、社會福利、反差別對待的法制等,她期待這些方案能夠讓我們產生細緻的人際溝通,並且讓被我們人類的本性排除出去的「非健全者」得到機會能夠回到社會中。為展開論述,瑪莎.納思邦在最後一章,除再度確認法律規制的限度是彌爾(J.S.Mill)的傷害原理外,另駁斥彌爾的功利原理以及人本的真理,而改採羅爾斯(John Rawls)的非真理的合理選擇論調(雖然在論及女性主義的議題時,她好像也對Rawls的議論頗有微詞)。
確實,社會契約論中所討論的參與者是自由平等獨立的,其前提已經排除了不自由、被差別對待以及依賴他人而活存的人,這不外是一個差異與排除的論述,殊不可採,但是細膩的人際關係以及單純的救濟真的可以取代救贖嗎?真的可以期待我們將來會容忍不傷害他人的異端(完美的、想像中的人類之外,必然存在的必死的、依賴的人類)存在嗎?
我也曾經在討論死刑問題時,利用了積極的羞恥感,企圖讓人們能夠理解到死刑的荒謬,甚至提出令其他論者嗤之以鼻的極端論調:讓判死刑的司法人員自行去執行死刑。我認為只有在自己手上結束一個生命時,才會感到深層的、積極的羞愧。不僅如此,我甚至設計了一套不講愛而只講贖罪的少年司法。然而,死刑的暫時停止執行僅是為了國際觀瞻的利益,而且曾幾何時,那套少年事件處理法已經失去了光環,淪陷在功利的泥淖中。台灣人與美國人都是人,瑪莎.納思邦真的能夠在處處充滿超人、蝙蝠俠、蜘蛛人等人類的完美性論述,以及崇拜鋼鐵雄師般的意志的美國,實現其羅爾斯式的美景?抑或,這只是再一度的吸食鴉片過程?難道前一個世紀八○年代後,刑事政策領域中社會復歸模式已經蕩然無存的事實,對瑪莎.納思邦而言,是個毫無意義的社會事實?再度地強調社會復歸或再社會化的努力的必要性一事,真的能改變現狀?
誠如瑪莎.納思邦所言,人類的情感是奠基於對於事物的人類評價性認識,而羅爾斯所主張的也不是真理而僅是合理的選擇。難道這些認識與選擇不是一種建構,一種被語言所支配的創造物?或許傅柯所談論的勞動與性的規訓僅是一種表象,更深層的還有人性的問題,不過人性也是一種語言的產物,所以真正讓查拉圖斯特拉感到無奈的應該是語言的結構吧。
數年前我寫過一篇有關後現代犯罪學的文章,文中介紹了日本的戎橋事件。一個大阪的流浪漢因為在另一位流浪漢身上看到自己未來的影子,於是將他擲入運河中凍死。當事實真相公諸於世後,令我無限感慨的是日本法官的良心判決。這位法官在毫無論述的情形下,做出了原諒行為人,也深刻反省日本現況的結論。他將語言的結構、共同主觀的結構epoche起來了,他應該是憑藉著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純粹主觀,做出了這個充滿了道德意涵的判決(語言)。啊!深層的人性不僅是存在於健全人身上,也同時存在於非健全人的體內,而唯一的救贖或許是透過文學或藝術,甚至於無法理解的判決中,所展現出來的、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奇妙共感。這個共感的發揮或許正是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於《法的力量》(#Force de loi#)一書中,最後所談及的可以與法的暴力對抗的純粹的暴力。
奇妙的是,去年我的一位已經畢業多年,而這幾年來幾乎都沒有任何學術上往來的學生也寫了一篇文章,名為〈灰色靈魂,被害?法律?救贖〉。我評審了這篇文章,並且也因為這篇文章的取徑與我上述的文章頗為相似,而內容上卻是比我的文章更加地紮實,所以給了最高的評價。
這篇論文以本文敘述文學,用註釋應證法律論述的書寫方式,利用極短的篇幅說明了對於同一事務,文學與法學的敘述上差異以及互通的可能性;手法雖然不見得會被傳統的法學研究者接受,但是只要細心詳讀幾次,相信有心人士會發覺這種對應方式的意見表達,正是彰顯出文學與法學交互排斥但又相互影響的現實。
該文大量地簡略引用德國、法國以及義大利三國最先端的哲學家的論述,這會造成閱讀以及理解上的困難度,一般的讀者應該是無法理解該文的精義。但這是作為讀者的他人的問題,而不是作者的問題,終究這類的論文在台灣僅是小眾論述,是無法一般化、普遍化的。以一個小眾的觀點而言,該文的作者成功地表達了法律暴力的現實,然後利用系統論的觀點,巧妙地將現象學中有關共同主觀與純粹主觀的論述,轉化為救贖之途,其中的轉折的巧思,令人激賞。
該文認為法律暴力排除所有的其他力量,強將人類的思維與行動納入法律系統的二元區分(該文所舉例子是加害與被害的區分)中,這會妨礙到人類終極的純粹主觀的作用,妨礙到自我透過對於他者的對應而尋覓(文學上的、真正的)自我的可能性;而法律語言的妥協,亦即修復性司法的創設,其實僅是一種表面上的退讓,事實上是無法大量地提供自我他人在純粹主觀層面進行刺激與思維再製的機會的。
以上這類的論述,以目前台灣的法律論壇的程度而言,大概也只有該文作者能夠明確地表述出來吧。連我也僅能在刑事責任判斷(該文中所謂的決斷)與司法良心的層面予以論述,而無法將這類的觀點擴張到所有與法律系統運作有關的人(或角色),或許這是因為我無多少的文學素養所致。
也正因為如此,當我看到該文作者透過文學作品而將海德格的「現世存在、死亡的不安」與自他的相互刺激與思維再製(自我的發覺或確認)連鎖在一起時,會感到非常不舒服。難道只有針對死亡的議題時,自他才有可能「共振」,亦即雙方都可以互相刺激、互相獨立地自我再製,進而形成一種不可言喻、不用言語的溝通(共振)?雖然該文作者在論述的途中,突兀地將死亡的議題模糊化(本文與註釋的本質上切割),而表明只要自我有過(除死亡外的)類似的人生經驗,則自己的人格的自我再製即有可能發生,但是我於最後仍舊認為這是一種永無止境的期待,而且亦僅是期待而已。
雖然我真的不喜歡這篇文章,但是又不得不承認,這篇文章或多或少觸動了少眾的深層悲哀。或許也是因為這種莫名的悲哀,我一直到最近還是寧願一味地將相關論述的可能性寄託在作為權威者、權力者(能將法律的效力予以懸置的人)而存在的「法官」身上,當個縮頭烏龜也無所謂,不然在語言的結構下,「我」要如何愉悅地生存下去?
不過,最近終於在態度上有了稍微的軟化。雖然很早就接觸了亞干賓的「神聖之人」與「奧許維茲的殘餘者」等的論述,但是始終無法理解其中有關人的潛在力的論述,所以感受也不是很深刻。一直到最近讀了亞干賓於二○○二年所書寫的《開展:人類與動物》的日譯本後,觀點才有所轉變。於《開展》一書中亞干賓除了再度強調動物性與人性之間的分隔線並不是那麼地明確,其間存在著被人性排除出去,失去法律保障的赤裸裸的生存(神聖之人或動物人),一種「被開展的人性排除於外,但又於外部包攝了內部的人性,且不屬於閉鎖的動物性」的純粹的存在。動物人或神聖之人無法走向任何一個極端(動物或人),而僅能漂流在人性與動物性間的場域中。在古代,人類透過神話等於外部標示出動物人(不是人也不是動物,而是生存於人類的旁邊,被人類愉悅地食用的想像中生物),並藉此而彰顯出人性的特殊性,但是在近代,人們利用了強而有力的「人性機器」,亦即生物學、哲學、政治學等道具,直接從內部建構起人性的內涵。至此,大量被人性所排除出去的神聖之人或動物人即不斷出現,人性機器愈是精緻(在這種意義下,瑪莎.納思邦的細膩的人際關係、互相尊重,甚至於積極的羞恥情感下所產生的憐憫等都是一種人性機器)則神聖之人或動物人就會愈多,當然人類的悲劇也會不斷地大量發生。亞干賓認為只有利用班雅明式的(或胡賽爾式的)中止判斷,將理性與語言這種人性的標竿用括弧括起來,不然根本不會產生救贖。亦即只有「不為」才有可能「有為」(老子說聖人不為大,所以能成其大),只要放棄或限制人性機器,則人類即可發揮潛在力。
小小的一本書,而且是在論述權力者的作為的「例外狀態」出書前的一年所出版的書,簡潔地讓我理解了我的學生的論述,亦即不僅是對於必死性的恐懼的共感,而是對於所有的人性事務,都能進行所謂的超脫語言桎梏的反省。同時《開展》這本書也讓我理解了我所設計的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盲點,此法的根本應該不在於明示出來的基於積極羞恥感的救濟或基於滿溢而出的情感(滿足感)的愛護,反倒是在於被隱藏起來的基於無為所達成的人性禁制的懸置,而在以往我都是兩者並重,甚或較偏好於前者,根本就忘懷了混沌與複雜秩序間關係的重點應該在於混沌。
瑪莎.納思邦女士的這本書,處處充滿了羅爾斯或哈伯瑪斯(J?rgen Habermas)的樂觀,但是我仍舊應提醒讀者,在讀完這本書,並且充滿幹勁、想要改變這個世界、想要實現積極的政治作為之前,先停下來。尼采在告別華格納、叔本華,結束前期創作,並在產出後期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善惡的彼岸》以及《道德系譜學》前,曾著了一本小書名為《人性,太人性的:一本獻給自由精靈的書》。或許我們在進入美式樂觀論述後,心中仍舊要保留些許抗拒人性時的悲觀情緒吧。
(本文作者為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引言
噢!我的身體。如你之類,男男女女之中的,我不敢遺棄;如你部分的,我亦不敢遺棄。
我深信,如靈魂的,與他們生死與共,(他們就是靈魂)。
我深信,我的詩,與他們唇齒相依,他們就是我的詩。
─惠特曼,〈歌頌帶電的身體〉,9.129-131
人類並非天生的王公貴族或達官顯貴,而是生下來就一絲不掛、一文不名。人類皆要臣服於生命的困苦,必須承受各式各樣的悲傷、疾病、需求與痛楚。最後,還要遭遇死亡……正是這樣的弱點讓我們尋求社會結合,正是共同的困苦讓我們的心朝向人性。如果我們不是必然困苦的人類,我們就不需要人性。任何人間的連繫都顯示著人本身是不足的。如果我們每個人都不需要他人,那麼我們就不會想要與他人團結。因此,從我們的脆弱之處,誕生了我們脆弱的喜樂……我無法想像一個不需要任何事物的人,他能夠喜愛任何事物。我也無法想像,一個不喜愛任何事物的人,他能夠獲得喜樂。
─盧梭,《愛彌兒》,第四卷
「平等的危機在於,既然我們都只是小孩,那問題來了:父親在哪裡?如果我們之中有人是父親,那我們就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了。」
─唐納.溫尼科特的病人B,《抱持與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