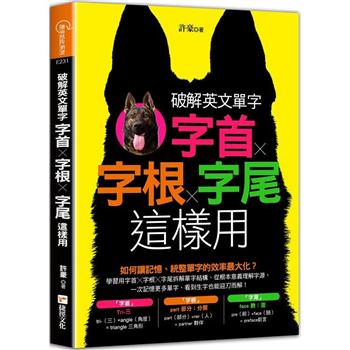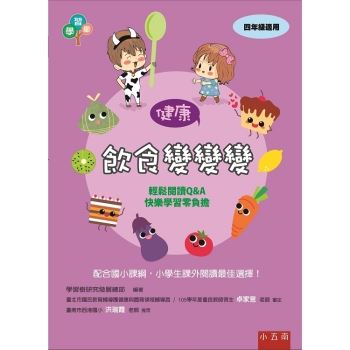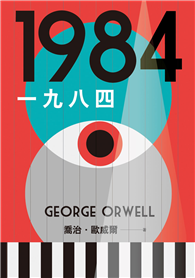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律師不會告訴你的事: 打贏官司的25大心法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59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80 |
社會科學 |
$ 237 |
訴訟法 |
$ 237 |
政治/法律/軍事 |
$ 255 |
社會人文 |
$ 264 |
法律 |
$ 300 |
法律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80%的律師經驗不足,官司勝負掌握在你手上!
面對訴訟,你是否心痛,但不知如何行動!
本書教你如何找好律師、如何與律師溝通、如何應對檢調;
充分的法律認知,正確的訴訟態度,是勝訴的關鍵!
本書以作者張冀明律師的親身經歷為本,傳達出當事人與律師在面對法律訴訟時,應該抱持的態度、應做的基本功課、必須熟悉的遊戲規則,以及可以靈活操作的技巧與空間,乃至於如何與法官、檢察官、對造以及媒體溝通。
作者以自身學習法律的經驗,加上實戰歷程中的轉變與體悟,歸納出二十五條訴訟心法,不論是當事人或執業律師,應用這些心法將是打贏官司的不二法門。全書內容共分三篇:
★第一篇:備戰篇:心法的形成
★第二篇:策略篇:訴訟的二十五大心法
★第三篇:實戰篇:十三個轟動社會的案子,由作者訴說案情與訴訟發展,並說明心法的應用。
本書希望為需要法律協助的人,提供幫助與提醒;為想要瞭解法律的人,做到說明與啟發;為喜愛閱讀故事的人,帶來交流與分享。
作者簡介
張冀明律師(Victor C. M. Chang)
學歷:
台灣大學法學學士、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碩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
現任:
眾達(Jones Day)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出生於台灣嘉義,就讀林森國小、蘭潭國中及嘉義高中,考上台大法律系法學組後,負笈北上。於台大畢業並完成軍旅生活後,即投入法律實務工作,迄今二十年。工作之餘,因著兄姊的協助,陸續於紐約完成碩士及北京取得博士等學位。在「行萬里路」中,活潑了作者的法學思惟及辦案手法。
走過二十年的律師實務歲月,曾處理不動產、國際貿易、智慧財產權、公共工程及白領犯罪等不同領域的案件。以深厚的法學基礎,針對不同的個案,能快速提供精湛的法律策略與解決方法,曾辦理轟動一時的「友訊v.威盛案」、「馬特拉v.北市捷運局案」、「四汴頭案」及「醫生殺妻案」等。
目前任職於眾達(Jones Day)國際法律事務所台北所,為訴訟部門的主要成員,處理各類型跨國交易與訴訟,同時提供跨國企業全球佈局的策略擘劃及法律諮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