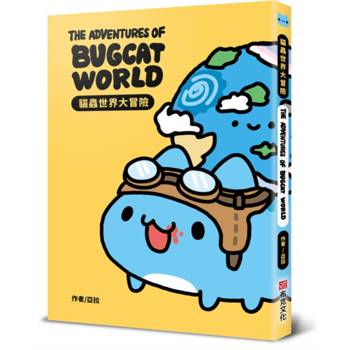詩的世界,藏有許多美麗的祕密
《邊緣光影》是席慕蓉經過十多年、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在一九九九年四月集結出版的作品,當時是爾雅版,目前她重新修訂及為此新版特別繪製約十幅美麗的畫作加入書中,交給圓神出版。
在創作上,無論是繪畫還是詩文都不曾停頓的她,書中結合了各類型的詩篇,題材多變,在這本詩集中,我們可以看到她多元的創作表現,稱得上是一部展現她創作顛峰的作品。
這是一本讓人不禁會用心看、用心想,也用心去感動的珍藏詩集!
作者簡介
席慕蓉
生於四川,童年在香港度過,成長於台灣。於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後,赴歐深造。一九六六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
在國內外舉行個展多次,曾獲比利時皇家金牌獎、布魯塞爾市政府金牌獎、歐洲美協兩項銅牌獎、金鼎獎最佳作詞及中興文藝獎章新詩獎等。擔任台灣新竹師範學院教授多年,現為專業畫家。
著作有詩集、散文集、畫冊等四十餘種,讀者遍及海內外。近十年來,潛心探索蒙古文化,以原鄉為創作主題。二○○二年受聘為內蒙古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