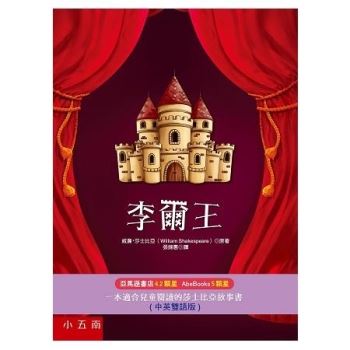•那個產婆仔
我幼年時,除了媽媽、兄姊之外,我並不清楚家裡應該還有一個叫爸爸的人。一直到我要上小學前,因為左鄰右舍的家庭都有一個爸爸,才漸漸清楚好像每一個家都應該有一個爸爸,而且都應該住在家裡。只是那時年紀太小懵懵懂懂的,雖然開始知道我也有一個爸爸,但我也不清楚為什麼我的爸爸幾乎都不在家裡住,也不知道爸爸到底住在哪裡。記憶中爸爸沒有寫信回家過,且那時新莊一般人家也普遍都沒有裝電話,我家自然也是沒有電話,所以爸爸好像與家裡並沒有在聯絡。只是爸爸會偶爾突然回家,那時候我反而會因很少回家的爸爸突然出現,好像家裡來了一個很特別的客人,而感到很興奮。
進了小學後,我才逐漸由大人的談話中了解,原來爸爸在外面跟一個在做「產婆」的潘姓女人住一起,才沒有住在家裡。
那時我不知道爸爸跟那個女人住哪裡,也不知道那個女人是誰,但因為家人那時都很怨恨,每次提到那個女人時,總是用很鄙夷的口氣叫她「那個產婆仔」,我才知道那個女人是一個「產婆」。知道「產婆」是什麼的一種職業,還有知道「那個產婆仔」姓潘,則是更後來的事了。
另外,還有一個很清晰的印象,從小就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中。那個印象依稀是媽媽用綁巾背著幼年的我,而媽媽正與一群大人,男的、女的都有,在互相拉扯,叫罵得很激烈。那個記憶的最後一幕是媽媽哭跪在地上並指天詛咒,另一個也在哭的女人則大力地拉扯著媽媽的頭髮。
那個記憶在我似懂事、又非懂事的年紀時,我也弄不清楚那到底是什麼。只是那個印象,常有事沒事地會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蹺春奶姆
我小時候還有一位奶姆。
原來是媽媽生下我之後不久,就生了一場大病去住療養院,大約住了一年多才出院。媽媽住院期間,我被送去寄養在一位本名喚寶貝,但大家都稱呼作「蹺春仔」的婦人處。「蹺春仔」晚上在替人幫傭做豆腐,後來白天在新莊地藏庵裡賣香、賣金紙,還有賣一些糕餅等拜拜用品。
那時「蹺春仔」剛生了一個女嬰兒,只是那個小嬰兒在人間停留的時間很短暫,所以剛失去小嬰兒的「蹺春仔」有剩奶可以吃,我就被送去寄養在「蹺春仔」那裡吃奶,當年我們就叫「蹺春仔」為奶姆。奶姆是家人的熟識,因為她的二女兒六歲時生了一場病,變成無法言語,以致我們孩子都在背後偷偷叫她「啞口仔奶姆」。
但當時不知為什麼,大人都叫她「蹺春仔」。我曾經想過是不是奶姆的生活重擔使她彎腰駝背──「蹺痀」,大家才那樣稱呼。可是實際上奶姆並沒有很駝背,我心中一直存著疑問,直到幾年前我才請教了奶姆家的大姊,大姊說是因為媽媽的臉與鼻子彎彎的,大家才叫她「蹺春仔」。
奶姆在幫工做豆腐時,她住家與豆腐店都位於現在新莊的全安里,那裡離我們家並不遠。當年那一帶有好幾家豆腐工廠,但現在只剩下一家很有名的百年尤協豐豆腐店了。媽媽住院一年多後才出院。根據媽媽在世時常敘述,她出院後第一次到「蹺春仔」幫工的豆腐店去看我時,豆腐間在夜晚昏黃的燈泡光下,正是熱氣騰騰、煙霧瀰漫,大大小小正忙成一團,在製作豆腐以便一早上市的時候販賣。
在媽媽住院的那一年當中,我曾經得過小兒麻痺症。媽媽說那晚她去豆腐店看我時,我剛好躺在一個放豆渣的大竹米篩中,正在大哭著。看到已經睽違一年多的我,媽媽忍不住地抱起我,緊緊地抱著。接著媽媽摸遍我的全身,要看看我的身體,當媽媽看到我一隻大、一隻小的一對小腳,還有滿頭的癩痢,媽媽非常的不捨,媽媽形容那時我真是一個乾瘦、生長不良的小不點丁。
媽媽回憶說,她緊緊抱住我,滿心的嘸甘。
媽媽說,她看到那樣的情景實在是心疼不已,當晚就把我抱回家了。
由於我們母子已經分隔一年多了,媽媽抱我回家時,其實我是一路哭鬧著,尤其回到家後,我感到環境很不一樣,嚴重認生,更是一直吵著要找奶姆,哭鬧個不停。據媽媽說,我很不安穩,折騰了一夜,最後媽媽掀開衣服,亮出乳房,試著讓我吸吮乳頭。瞇著眼的我在媽媽胸前磨蹭一番後,竟然開始用力吸吮,之後逐漸得到安撫。已經累了的我,才一手抱著媽媽的乳房,安然地睡在媽媽的懷抱裡,過了與媽媽重逢的第一夜。那夜的情形,媽媽生前一再提起,疼惜憐愛溢於言表。
於是從那夜開始,我睡覺時一定要窩在媽媽的腋下,然後一手抱著媽媽的乳房,甚至要吸吮一番才會滿足,才肯安靜地睡覺。媽媽在我小時睡覺的時候,常常會撫摸著我的頭,對窩在媽媽腋下,一手抱著媽媽乳房的我說:「可憐的孩子,一定是幼嬰時沒有吸到媽媽的奶,才會吸老奶脯吸到這款樣。」於是抱著媽媽的乳房睡覺,甚至要吸吮一番,從幼年開始,就成了我的習慣。如果沒有那樣,就會很不安穩不願睡覺……
•掃地出門
在我小學一年級快結束,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初時的一個夜晚,媽媽才剛從台北下班回到家,突然有四個人窮凶惡極的樣子,闖進我們只點著一小盞昏黃油燈火的家,並以毫無轉圜餘地的態度告知媽媽,我們住的公廳已經賣給他們了,要求我們限期搬離。
由於事前沒有任何預警與徵兆,媽媽初聽到這訊息時,好像遭到晴天霹靂,手足無措,完全不知要如何是好。媽媽簡直不敢相信,他們真的會那麼殘忍,真的要把房子賣掉,把我們掃地出門,完全不管我們家一窩小孩要怎麼辦。
「他們」到底是誰,其實到現在我還是不清楚。回想起來,也不知那時爸爸、「卡將」與眾多親友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也不清楚爸爸在那些人來通知後,是否有跟媽媽磋商。總之,我們根本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一家大小就狠狠地遭到掃地出門。
也不清楚媽媽當時到底是怎麼奔走的,幾天後,媽媽是有找到房子並決定立刻搬家離開新莊。
新家是在三重埔的一間小販厝。六月天,要搬到三重埔那天,媽媽租了一輛小貨車,本來是要搬一些家具走的,但我記得那天並沒有看到爸爸,家中卻闖進了一群人來搶東西與看守他們聲稱的公物。他們說大長櫃不能拿走,大桌子不能拿走。這不能拿走,那不能拿走……因為那都是公廳中的公物。
最後,媽媽只能收拾一些衣物、棉被、蚊帳、碗盤與盥洗用具等日用品,分別由全家大小捧著搬上車。我記憶中媽媽小心攜帶的,只有一套早年爸爸去日本,從東京買回來的華麗瓷器,還有一件當年爸爸送給媽媽的黑色呢絨長大衣。媽媽就這樣一人獨自帶著我們五個孩子,離開新莊那個刻滿傷痕與屈辱的地方。
搬家臨走時,很多新莊五十六坎中的鄰居,聚集在我們家第一進中藥鋪的門口兩旁,觀看著我們被掃地出門。小學一年級的我無法理解他們在想什麼,但是他們圍觀看著我們即將離去,彷彿都在議論紛紛,指指點點不知在說什麼。
車子發動時,我們一家孩子都窩著,擠在衣物包裹之間,面無表情地坐在沒有頂篷的小貨車台上。媽媽流著眼淚咬著牙,指著那些來家裡搶東西的人恨恨大罵:「你們這些沒良心的,將來一定會得到報應!」
•乘著歌聲的翅膀
媽媽手上拿的那件黑色呢絨大衣,也是我們童年時代很重要的一件紀念物。在我未上小學前,媽媽帶我到小舅家上班,冬天,只要天氣特別冷,媽媽就會穿著那件大衣。天黑之後,每當我們在站牌等公車時,如果冷颼颼的風襲來,媽媽就會用兩手插在口袋中,並用手將大衣撐開,再把我覆蓋在大衣裡面,如同母雞用翅膀將小雞覆蓋起來保護一樣。
那件大衣,除了曾經是覆蓋保護我們的翅膀外,在我的想像中,那件大衣也彷彿曾經是媽媽乘著歌聲的翅膀。媽媽穿著它要飛往那最美麗的地方,去編織最甜美幸福的夢,去享受最恆久的愛情,與最安靜的人生。
如今媽媽攜帶著的,是一個已然破碎的姻緣夢。在那樣被掃地出門的時刻,媽媽緊緊抱著那一件大衣,想必有難以相信的錐心──之慟。
媽媽過世後,那件大衣一直由三姊收藏著,後來三姊拿去修改繼續穿著。由於大家並不缺衣服,三姊執意繼續穿著那件大衣,我想三姊應該也有類似我常感念,天冷時被媽媽覆蓋著保護,那個永誌難忘的經驗吧。
僅存的那套日式精緻華麗瓷器,後來逐一破損,民國七十年代後,最後一個橢圓船形、我們家都稱為「腰仔盤」的盤子,也告破損。而同一套餐具中,用在餐桌上擺置筷子,僅存的三個白菜形、兩個茄形的瓷「箸置」,則由我留著紀念至今。
在新莊的日子,除了中港厝的阿珠姑仔之外,爸爸那邊的親人,我們大多是非常的疏離。不過新莊還是有一些人,例如水長叔一家,或曾經鼓勵過我們,或曾經幫助過我們,或曾經陪伴過我們,雖然那時我還小,但我一一銘記在心,永遠懷念。
一九五九年,我小學一年級的班導師是陳金棗老師。陳金棗老師在教我之前已教過二姊,對我們家的狀況已有基本的了解,教到我時便對我鼓勵有加。我小學一年級的學校生活過得很順利,主要便是陳金棗老師的鼓勵,尤其她對我寫字與美術方面的表現不斷地稱讚與鼓勵,使得我非常喜愛上學。
記得有一次上圖畫課時,我曾畫過一匹白馬,由於老師很欣賞,一直稱讚那匹馬畫得很好,後來老師拿去刊登在校刊上,因此我受到了莫大的鼓勵。我們搬到三重時,一年級下學期還沒結束,我們都繼續在新莊國小念到那學期結束才轉學。搬家隔天上學時雖與三姊同行,但由於在進入小學之前,坐公路局的巴士,隨媽媽到台北上工已有半年,從新莊中正路到台北,會經過三重埔重新路,那一段路我已相當熟悉,下課後我就自己一個人順利從新莊坐車回三重。第二天到校,陳金棗老師問我知不知道如何坐車,我很大聲地說知道,老師便要全班同學給我鼓掌,說我很勇敢也很棒。
當然,離開新莊,也離開了大多是鄰居的同班同學,像翁文豪、賴碧月、張素霞、張樹木……等等。小學一年級第一學期,翁文豪是第一名,賴碧月是第二名,張素霞是第三名,而我則是第五名,當年的獎品是一個咖啡色的玻璃杯,上面印著品學兼優的白字,不過那杯子使用不久,沖倒燙熱的開水時就裂破了。
我們那些調皮的男生叫賴碧月為「賴(凹)鼻仔月(藝)旦」,而賴碧月與張素霞都是住離我們家不遠的鄰居。我記得張樹木是張素霞的堂兄弟,我們經常一起在新莊慈佑宮裡玩。有一次我們在慈佑宮玩,不知怎樣卻翻臉了,他罵我不要臉,說我愛張素霞,因為我放學時都走在張素霞後面。那次他還用腳把我拐倒在地上,使後腦杓碰到地,害我在慈佑宮裡哭了好久。一九九四年初,我曾在新莊一次選舉的助講場合,向新莊鄉親說,如有人認識張樹木,我那新莊國小一年級時常在一起的玩伴,請告知他我懷念他。
•正義北路一六六巷
我們三重的新家其實是家徒四壁,除了沒有裝潢隔間外,連吃飯的餐桌與睡覺的床都沒有。往外一看、路人在巷中過往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實在是與新莊家中庭院深深,充滿大廳、太師椅、大櫥、大櫃、大床、大灶、大桌,還有棺材等景象完全不同。而比較特別的是新家有自來水,水龍頭一開水就來,令我們很興奮,我們也從此脫離了使用古井取水的那種夢魘。只是後來也發現,新家的自來水常常會停水,有時一停好幾天,停水時要到處張羅水,也挺麻煩的。
我們將新家稍稍整理後,傍晚時分媽媽去買了一些包子充當晚餐,稍早並在我們那條巷子後段尚未完工的工地上,撿來幾張破舊三夾板,洗一洗,擦拭後,晚上鋪在地上當床。由於四周有好幾塊荒廢的水田,蚊子很多,我們點了好幾支蚊香驅蚊,並掛上蚊帳才能睡覺。第二天一大早,媽媽就到處張羅家用品,買鍋子、烘爐、煤球、小型折疊餐桌、椅子……等等家用品。媽媽並在幾個工地上,撿拾廢木材來斬劈生火,總算開始了在新家的正式生活。利用餐桌,我們也有了做功課的地方。
再經過一段時間,媽媽才從小舅那邊搬回來第一張床,之後又陸續張羅到兩張床,家人才能全部有床可睡。而我則仍然與在新莊時一樣,要跟媽媽一起睡,且要窩在媽媽腋下,抱著媽媽的乳房才願意睡覺。
回首在新莊時,雖然第一進的房屋租給別人開中藥鋪後,比阿嬸、阿叔他們在世時要親善得多,但畢竟他們是做生意的,晚上睡得晚,早上並沒有需要很早起來開門。因此每天一大早敲門要他們早起開門讓我們過路,其實偶爾也有不愉快的感覺。那時我們家人要出門工作或上學,如果太早了,或天太冷了,常常要躊躇再三,才能鼓起勇氣向前面敲門。即使是他們店中傭人來開門時,顯露出的一點臉色,對我們一家脆弱的心靈來說,都是難以承受的壓力。
媽媽自小是養女,從長大戀愛被拆散,到跟爸爸成家,其實都沒有過獨立自主的生活。我們初搬到三重時,雖然家徒四壁,媽媽也怨恨被掃地出門的不堪,不過新家一開門就是巷道,出入家門再也不必看人臉色,低頭過人屋簷下了,那是媽媽一生中首度能當自己生活的主人,那意義是何等的重大。回首媽媽的一生,那應是最刻骨銘心的一件大事吧。
一九四九年十月四日媽媽帶著孩子從三芝搬到新莊,一九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媽媽辦妥遷入三重手續,開始了人生另一個完全不同的階段。
那年媽媽四十三歲,爸爸六十一歲。
三重埔在民國五十一年才從鎮升格為縣轄市,所以新家門牌號碼是「台北縣三重鎮正義北路一百六十六巷七號」。原先我們並不清楚媽媽是如何找到那間新房子的。
後來才知,原來坤山舅那時剛好賣了一批二丁掛的瓷磚給三重埔一位叫陳寶樹的販厝自建商。聽到我們即將被趕出新莊的家,媽媽與坤山舅商量,趕緊用瓷磚的貨款,先向陳寶樹先生抵了一間房屋,讓急得團團轉卻不知何去何從的媽媽,有個安頓一家的地方。之後阿舅再幫媽媽的工資從六百元調升為八百元,而搬家後不久,大哥也適好從高農畢業,到縣政府工作,已經可以領固定薪水,才慢慢償還買房子的各種費用與貸款,那樣我們一家才能很快地在新天地安頓下來。
•「田僑仔」之子
巷子右邊的第一家,門牌號是一號,是一間製作布旗的小工廠,除了製作各種旗幟外,也做各式各樣的廣告布條。現在已經是全面電腦化生產的布旗行業,那時製作生產完全是用手工。業者需先將糯米煮開,加入米糠、石灰粉做成隔色糊,那種隔色糊的作用,其實就是類似西畫中的遮色液或留白膠。將隔色糊放在一個三角錐狀的糊筒中,再從糊筒另一端的小洞擠出隔色糊,在布上作畫或填補空白,等隔色糊曬乾了,沒有隔色糊的地方才用刷子刷上需要的顏色,每一種顏色用一個小水桶裝著,一道一道程序的處理,相當地費工。這一家在巷口廢耕田小徑兩旁,綁滿了要晾乾的布旗,有時突然下雨時,老闆一家人就狂奔出去收拾正在晾曬的各種布旗,靠天吃飯相當拚命。
三號是一間小小的塑膠工廠,專門做一些簡單的塑膠射出。機器整天轟隆轟隆地響個不停,以前大家多沒有環保概念,且很多家庭也都是有機器在工作,大家都一樣很吵。所以塑膠工廠的噪音非常嚴重,也沒有人認真的抗議。
但這一家是我們巷子第一家有電話的,當年裝電話非常地昂貴,一般人家是裝不起的。他們就將電話供給左鄰右舍使用,例如我們家也是用他們的電話,但是只能接不能打。親友要跟我們聯絡時,打他們家的電話,他們就會到二樓陽台大叫:「喂──七號電話!」聽到叫聲,我們就跑去他們家二樓接電話。他們以這種方法敦親睦鄰,解決機器有時操作太晚噪音擾人,可能會引起抗議的問題。
民國五十年代的三重,很明顯地正從農耕逐漸轉為工商的城鎮,很多人土地賣人或與建商合作蓋房子,得到不少財富與房產,大家都叫那種人為「田僑仔」。五號的阿男仔,年紀輕輕未滿二十歲,因為他家也有田地拿去與建商合建,分到好幾棟販厝後,他就成為一個頗有資產的「田僑仔」,也去開了一家公司做老闆,但他到底在做什麼,我們其實是不清楚的。
民國五十七年一月五日,我曾在我的日記中寫著:「隔壁阿男,現在實在真可憐,事業經營不良,工廠要完了,債主紛紛到他家去搬東西抵錢,結果他們只好將東西拿去寄人,可悲啊!一個少年年紀輕輕,由於愛花用弄到這個地步,實在真可憐。」他也追過我們家二姊,但二姊似乎很怕跟他相遇到,完全沒有回應。
七號是我們家。一樓前面是一間客廳,中間是一間房間,旁邊是走道,後面則是餐廳、廚房、浴室、廁所,每個空間其實都很小。樓下的房間是媽媽睡的地方,我與三姊則與媽媽睡在一起。
六坪大的二樓,則擠了三個小小的房間與一個小小的客廳。靠後陽台那一間是大哥的房間,媽媽也免費讓大哥兩位從台中上來台北工作的朋友一起住。那兩個朋友,一位姓吳,當年媽媽很喜歡他,極力想要撮合他與大姊,但沒有成功,現在已經移民澳洲多年;另一位則是姓朱,當年隻身北上,每天騎腳踏車,從三重騎到當年尚屬台北縣的內湖鄉公所上班的小公務員,但前幾年已高升到他故鄉的縣府民政局長了。
中間的一間則是大姊與二姊的房間,靠巷子陽台的前邊則是小客廳。大姊、二姊房間與前面小客廳之間還有一間小房間,這間小房間與小客廳,當年都是併在一起,出租給只有夫婦兩人的簡單小家庭以補貼家用。
小小的房子隔了許多隔間,擠了一堆人,雖然很克難,可是當年在那個巷中,一個家庭生有五、六個孩子是很普遍的。擁擠並不是很特殊,多數房子都是那樣,捉襟見肘地在居家住人。
媽媽則還是像以前一樣,每年都要買一些蘿蔔、大黃瓜、小黃瓜等各式蔬果曝曬,並且蒸煮黃豆、黑豆曝曬發酵後,加鹽水裝甕製作醬菜以備家用。所以小小的家裡,仍然擺了許多製作醬菜與豆腐乳的小缸甕。
我也記得很清楚,剛搬家後不久,爸爸有個以前我們從沒有見過的朋友,常會到家裡來坐。有時我也會感覺納悶,爸爸不在家,他常來我們家要做什麼?有一次他在窗外叫門,媽媽叫我不要開門。媽媽說,那個人說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話,以後不要再讓他進門了。那個人好像還有來叫過幾次門,但我們都不開門也不理他,所以那個人後來就沒有再出現了。
九號的主人是在台北市政府公車處上班,民國五十一年台視開播時,他們家是巷中唯一有電視的人家。每天晚飯後,或星期六下午開始,他們家的客廳或窗戶外面,或坐或站,擠滿了一些生活單純的鄰居與工人,包括我們家,都在那裡看電視。我最深刻的記憶,是大家擠著看敘述第二次世界大戰,由雷克•傑遜飾演「漢利排長」,每集最後美軍一定把德軍打得落花流水,大受歡迎的「勇士們」影集。另外還有一部也很受歡迎,由法蘭克.麥克格雷玆主演的「篷車英雄傳」。當年播出時媒體還讚譽為是表現積極、堅毅,充滿自由奮鬥精神的美國西部開拓史。但是該影集其實是充滿了白人的觀點與立場,看的人也是接受了那種觀點與立場。我記得當時美國西部片還相當風行,但美國西部片劇情的最後,也是劇情的高潮,常常是美國騎兵出現,小喇叭響起,騎兵衝鋒後「紅蕃」潰敗。我們那些單純或坐或站的鄰居們,有時還會興奮得鼓掌叫出來。不過,那類種族對立型的西部片後來就消失了,義大利「荒野大鏢客」型的西部片,換成俠客與惡徒決鬥,隨後在電影院風行了好一大陣子。
當然大家也很愛看節目壽命很長的「群星會」。「群星會」在民國五十一年台視開播時,由關華石、慎芝夫婦製作,一推出就相當受歡迎。「群星會」的招牌歌曲──「群星在天空閃亮,百花在地上開放。我們有美麗幻想,為什麼不來齊歡唱。我們也願像星辰一般,把歡樂散播你的身旁,我們也願像花一般,使你的人生更芬芳……」當時好像大家都能琅琅上口,也是很多人的永遠記憶,而當時一些在該節目出現的許多紅歌星,也常常是大家茶餘飯後品頭論足的對象。大家也很愛看民國五十四年十月開播,壽命也超長的節目「五燈獎」。
九號這家雖然每天會擠滿愛看電視的鄰居,但主人卻常常酗酒,因此他們夫婦經常會吵架。他們一吵架,先生會盛怒地坐在後面的飯廳喝悶酒,外省太太則關在中間的房間裡賭氣,電視就不開了。鄰居們都很有經驗,一看就能察覺。一堆吃過晚飯就習慣來報到要看電視的鄰居,如果等個一、二十分鐘,看他家仍然沒有要開電視的跡象,大家就會很失望的離開。其實背負著成群鄰居要看電視的重擔,他們家的壓力也滿大的,有時不開電視,還會惹來希罕什麼的罵名。尤其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紅葉少棒隊意外打敗日本少年棒球明星隊,興起棒球風潮後,民國五十八年八月金龍少棒隊到美國威廉波特比賽,全國風靡半夜起來看電視衛星轉播,他們家半夜也要起來開電視給眾家鄰居看,實在是很辛苦。那次比賽過後,大家深深感覺半夜出門到鄰居家看電視極不方便,才紛紛購買電視機。因此民國五十八年九月我上高一時,發現到鄰居家聚集看電視的情形,幾乎已經完全消失,因為應該是家家戶戶都買電視機了,而且是開始買彩色電視機,連我家也因大嫂進門而有了一台嫁妝電視。
•黑年糕
十一號則是住著苦命的一家人。丈夫在做油漆工,愛酗酒愛賭博,又愛打太太。因為怕丈夫知道,會把工資搶走,十一號的太太就暗中在幫人洗衣服賺零工錢。我媽媽生病開刀回家後,有一段時間,也曾經請過那位瘦小的苦命太太,偷偷來我們家幫忙洗衣服,賺相當於那時學生的補習費,行情約一個月四十五元的洗衣工錢。但她丈夫一喝酒,動不動就痛揍她。有一天她又遭她丈夫莫名其妙白白地毒打了一頓,結果等她丈夫出門,她再痛哭一陣後,就將偷藏了不知有多少時日的一瓶「巴拉松」農藥,從床下拿出整瓶一口灌下,結果當場口吐白沫橫死在小客廳中。小學的我與她家一窩小孩正在她家門口玩耍,我們目睹了那幕極為苦痛的慘劇,驚嚇不已號哭成一團。
十五號則是蓋我們那巷子房屋的「寶樹仔」的家,「寶樹仔」可算我們那巷子中最有錢的人。他小兒子綽號叫「黑年糕」,曾經跟我同班,他個子矮小,結實黝黑,凶悍模樣全校皆知,不但同學怕他,有時我們也都認為一些比較沒有膽量的老師也怕他。小學畢業後,我就沒再看過他了,聽很多鄰居說,他果真變成了一個有頭有臉的「角頭大哥」,不知在何方領導著一個小幫派。
他們家老大叫「阿憨仔」。他其實並不憨,但為什麼大家都叫他「阿憨仔」,我也不知道。他也是小學畢業就無所事事,經常成群結黨聚集在一起打架賭博。有一次「阿憨仔」跟我說,他有得到一本武功秘笈,要收我為徒弟,結果就帶我去一個隱密地方,三、四個人就在那裡,真的比手劃腳起來練功夫,還說我滿可以造就的。不過跟他們在一起鬼鬼祟祟四、五天,就被媽媽發現了,媽媽狠狠地打了我一頓,警告我不可再跟那些流氓在一起。想跟他們混在一起學武功的事,就不了了之了。
•乳癌
那晚,我們幾個孩子都很害怕,偷偷地哭了一場,不過並沒有讓媽媽看到。
經過安排,最後媽媽就到台大醫院去做切片檢查。那時我們都覺得忿忿不平,覺得媽媽如果真的是罹患了惡症,那上天對媽媽實在是非常的不公平。
檢查的結果竟然是惡性的乳癌。當年很多人面對那種惡疾,大多怕病人聽了受不了,因此多會採取對病人隱瞞的態度。大哥、大姊也決定不告訴媽媽真相,甚至也告訴二姊、三姊與我,說媽媽的瘤是良性的,所以我們大家看起來都好像沒事,也告訴媽媽說那是良性的腫瘤,只不過為了安全起見,還是要進行乳房切除手術,並將進行化療。我過了一段時間後,才逐漸知道媽媽真的是罹患了乳癌。
當時大哥也到處打聽,最後就打聽到台大林天佑教授是以一種特殊的腫瘤摘除術稱道於腫瘤手術界。那年的暑假中,媽媽就到林天佑醫師在台北市北門附近的自家醫院進行手術。大姊與二姊也請假在家煮飯送飯,並輪流在醫院照料媽媽。我和三姊也經常在下課後,就提著裝菜飯的小鍋子,由三重的家走路經過台北大橋、延平北路,到林天佑的醫院給媽媽吃。
手術應該算成功,不過也相當嚴重,從媽媽右手臂上端內側開始,到整個右胸部乳房徹底清除。手術後媽媽的右手,整整快有兩年的時間是無法舉起來的。手術後失去右乳房,讓媽媽感覺到整個人失去了平衡,心理也受到很大的衝擊。
而我也一樣受到很大的驚嚇。從我嬰兒時媽媽住療養院出院,到豆腐店去抱我回家之後,我就需要窩在媽媽的腋下,一手抱著媽媽的乳房,才會覺得安穩,才願意安靜睡覺。從我幼年開始,一直是那樣。到了媽媽開刀那時,我已經小學四年級,就要升五年級了,雖然已經沒有像幼小時那般依賴了,但如果狀況允許,睡覺時我都還是要抱著媽媽的乳房才會覺得滿足。
因為我習慣依偎在媽媽的右邊側睡,然後用我的右手抱著媽媽的右乳房。但媽媽胸部的開刀部位很大,右邊乳房不見了,右胸部完全不能隨便碰觸。媽媽開刀回家變成這樣,我受到極大的驚嚇,完全不知要如何是好。在一種很痛苦的情緒下,我竟變成不要再跟媽媽睡了,而跑到樓上哥哥的房間去睡。我不再跟媽媽睡,媽媽其實也是非常的傷心,雖然媽媽最好是獨睡,以免不小心旁人碰觸到媽媽開刀的部位,但那也好像是被人嫌棄。頓時,媽媽整個生活都失去了秩序。
媽媽心情不好時,就會說她一定是得了乳癌惡疾,否則哪需要拿掉乳房?那時媽媽就會怨嘆自己命苦,怨嘆爸爸無情義,讓她如此操勞,才會罹患惡疾。
媽媽也常很傷心自己一定是吃太多醬菜,或吃太多鹽漬的東西,才會弄壞身體。媽媽也擔心還有兩個孩子還小,萬一她走了怎麼辦?
本來滿二十歲就需要去服兵役的大哥,因為家貧一連幾年都申請延後服役,但民國五十五年之時兵役單位已不同意再延了。那幾年大哥與朋友合資,做起本行,在台北下塔悠基隆河邊,租了一小塊地,養了二隻乳牛,生產生乳賣給味全公司與福樂公司。另外也買了一輛馬達三輪車到北投做運送磁磚的生意,那時也正開始將運送貨物的生意,擴大轉為到基隆、瑞芳,購買煤炭送交北投一帶的磁磚工廠燒窯使用。不過最後兵役無法再延,大哥只好放下正起步,供應煤炭給北投磁磚工廠的生意去服役。
那時媽媽開刀後已經休養好一陣子了,原來僵直的右手,也已經改善很多了,媽媽就毅然決定接起了哥哥原本想暫停的生意,獨自把生意撐起來。
媽媽決定作生意後,穿上特別訂做的內衣,不讓人看出她的右乳房已經切除以免橫生困擾,更是開始應酬洽談生意。雖然那時媽媽每天都必須很早起床,工作也非常辛苦,但那時媽媽整個人,實在也是她一生中,難得容光煥發,忙得不亦樂乎的日子。過了兩年大哥退伍,媽媽才改為輔助幫忙性質。經過媽媽與哥哥努力經營,家裡就開始逐漸脫離貧窮的困境。
但接著厄運又悄悄來臨,民國五十九年初,媽媽開刀那邊的胸口出現一個芝麻大的小潰傷,起初不以為意,但後來卻發現小潰傷無法癒合,結果小潰傷越來越大,檢查才知道原來癌症又復發。
那一年夏天,身體一向硬朗從不生病的「豆醬阿嬷」突然生了一場來勢洶洶的大病,檢查還未有結果時,非常意外的,八月二十八日竟撒手人寰而去,享年七十一歲。
我從小就有種感覺,媽媽與「豆醬阿嬤」之間,好像有一種很微妙,卻又從未說出的情感。「豆醬阿嬷」過世時,媽媽非常傷心,常常痛哭不能自已。好似一世的恩義,也好似一生的委屈,無從訴說,最後只有用痛哭來傳達。
•三十九年後
媽媽雖然從沒有被惡劣的環境擊倒,但最後還是不敵病魔。媽媽過世後,我常想:媽媽基本上也是一個與世無爭,善良無辜的人,但命運為何卻會那樣的坎坷?我對媽媽遭遇那樣深深的苦難,不僅心裡上深深覺得不平,也致使我對人生的價值起了極大的懷疑。從媽媽惡疾復發到過世後的好幾年中,我陷入深深的哀傷,常常讓我認為上天不公,致使我的情緒長久無從抒解,很長一段時間我憤世嫉俗,待人處世經常出現一種孤憤式的反應。
那些往事已經幾十年了,但點點滴滴,我無法忘懷。這些年我花了一些時間做訪查、考證,寫下我過去年少時無法抒解的傷感,也寫下我對媽媽至深和永遠的懷念。似乎沒有把那些往事寫出來,幾十年間一直在我的內心中不時吶喊與翻滾的微微情緒,永遠不會平靜下來。
生老病死,悲歡離合,當年的人事已一一隨風而逝。三十九年後的今天,回首,才憬悟原來人間正道是滄桑。悲歡離合原該歸諸緣分,苦痛缺憾只有還諸天地,天地悠悠,一切,原該有個理解了。
只是──不管有何憬悟,或如何地理解,我不會忘記媽媽為了養育兒女所承受的犧牲與苦難,我也不會忘記緊緊依偎在媽媽身邊的滿足,我更不會忘記深深依戀著媽媽的乳房,那種永遠的溫暖。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媽媽的乳房—許足女士的人生歲月及家族記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29 |
歷史人物 |
$ 229 |
中文現代文學 |
$ 255 |
中文書 |
$ 261 |
亞洲當代人物 |
$ 261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媽媽的乳房—許足女士的人生歲月及家族記
•那個產婆仔我幼年時,除了媽媽、兄姊之外,我並不清楚家裡應該還有一個叫爸爸的人。一直到我要上小學前,因為左鄰右舍的家庭都有一個爸爸,才漸漸清楚好像每一個家都應該有一個爸爸,而且都應該住在家裡。只是那時年紀太小懵懵懂懂的,雖然開始知道我也有一個爸爸,但我也不清楚為什麼我的爸爸幾乎都不在家裡住,也不知道爸爸到底住在哪裡。記憶中爸爸沒有寫信回家過,且那時新莊一般人家也普遍都沒有裝電話,我家自然也是沒有電話,所以爸爸好像與家裡並沒有在聯絡。只是爸爸會偶爾突然回家,那時候我反而會因很少回家的爸爸突然出現,...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許陽明
- 出版社: 圓神出版 出版日期:2009-08-25 ISBN/ISSN:9789861332994
-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歷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