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藏起來!」 把後門打開一條縫、窺看外頭的克倫,緊迫地低喝一聲,隨即把門關上。 仰放在台上的軀體,高高隆起的腹部皮膚被切割成十字狀,朝四方掀開,露出鼓脹的子宮。 地板撒了木屑,解剖台底下蜷趴著一條雜種狗。 聖喬治醫院外科醫師丹尼爾.巴頓的手指,正用異於肥短外觀的纖細動作將著色蠟注入遍布子宮表面的血管。動脈已經注完了紅色蠟,現在正在為靜脈注入藍色蠟。 這裡並不是丹尼爾任職的醫院,而是他的私人解剖室。 聽到克倫的通報,正注視著老師手部動作的「胖班」血色紅潤的臉頰剎時變得蒼白。 「老師,請先暫停吧。」愛德低喃說。 「現在沒辦法中止,蠟會凝固。」醫師打了回票。 「沒時間了,他們馬上就要來了。老師,得罪了!」 「皮包骨亞伯」和胖班一左一右抓住了丹尼爾的手。 正以石墨素描屍體狀態的奈吉與愛德對望一眼,彼此點了一下頭,一起動手搬運屍體。 「等一下,不要把屍體弄傷了!」 丹尼爾四十出頭,外貌活脫脫就像顆馬鈴薯。他厭惡拘束的假鬈髮,就連上課的時候也不戴,直接露出那頭蓬亂的紅髮。連上課都如此了,更遑論現在並非正式授課。可是,身居他這種地位卻不戴假髮,就形同穿著內衣褲見客一般。 現在馬鈴薯的雙手被弟子們扭到身後,氣得滿臉通紅,就好像染上了胭脂蟲的紅色一般。 「放心,我們會小心搬運。萬一被他們發現,會被沒收的。」 豈止是沒收,在場所有的人都會被打進大牢。 「老師,不好意思,請您安靜一點,這樣彼此都好辦事。」 奈吉和愛德用攤在地上的白布裹起屍體,再用寬幅布帶從上面捆好,搬到壁爐去。 「小心點!那可是難得弄到的貨色啊!」 「放心,我們知道。」 幸虧現在是七月天,壁爐沒有生火。 奈吉放下壁爐架上的爐門,遮掩住爐口上方三分之一處。爐門是一般常用的家居配件,而且夏天不使用壁爐時通常都會放下來,所以不會啟人疑竇。 愛德打開牆上的密門,進入鑿空厚牆挖出來的狹窄空間。這裡設置了一台堅固的絞盤。 五名弟子為了預防現在這種情形,合力鑿牆挖出這個空間,並裝設了這架裝置。可不能委託別人施工,必須保守秘密。 用鋸子和鑿子切開頭蓋骨、鋸斷骨頭,雖然也是相當費力的活兒,但是敲下牆上的紅磚、挖出空間、設置絞盤、再安裝卡閘避免把手倒轉,然後在與壁爐鄰接的牆上安裝滑輪、在對面牆壁打洞、把前端綁了鉤子的繩索穿進去⋯⋯這些工程實在浩大。 這是他們第一次正式啟用裝置。 克倫走到壁爐前說:「沒問題了嗎?藏好了嗎?」 「藏好了。」 「櫃子。」克倫指示。四名弟子合力拖動櫃子,擋在密門前。密門上貼著與牆壁相同的壁紙,但是仔細察看,還是可以看出門縫。用來擋門的櫃子為了便於移動,裡面已經清空,但依然相當沉重。 門房兼僕役的「歪鼻托比」,前來通知西敏地區治安法官底下的犯罪搜查官—俗稱「弓街探員」—來訪。歪鼻托比把客人領進來前又刻意拖延了一下,為眾人爭取了更多的時間。 丹尼爾頂著一張紅馬鈴薯臉,迎接了兩名弓街探員。他的右手裡,還握著沾滿了鮮血與脂肪的解剖刀。 「醫師,您又偷了對吧?」 「黑爾茲先生,您怎麼一上門就這樣含血噴人呢?」鼻頭布滿雀斑的克倫以伶俐的笑容應道。 丹尼爾的眾弟子與這兩名弓街探員黑爾茲及布雷是老相識了。弓街探員不曉得已經來這裡臨檢過多少次。 「這房間還是老樣子,臭死了,教人作嘔。」兩人皺眉掩鼻說。「今天特別臭。」 「天氣這麼熱嘛。等兩位歸西了,一樣也是這個味兒。」同樣是克倫回嘴。 「盜墓的又是那兩個,迪克和哥布林。他們兩個已經招了。醫師,您這次被海削了一筆呢。迪克那傢伙誇耀說這次的墓地設了防盜墓鐵籠,他們費了好一番工夫才拆掉,所以價錢高於行情是當然的。」 黑爾茲一邊說著,眼光一邊掃遍了整間解剖室。 五名弟子全站在解剖台前,擋住治安隊員的視線。 「話匣子」克倫.史普納,二十二歲。 「胖班」班傑明.貝密斯,二十一歲。 「皮包骨」亞伯.伍德,二十三歲。 俊逸出眾的愛德.特納,二十一歲。 天才細密畫家奈吉.哈特,十九歲。 不,站在解剖台前的只有四人。愛德還在牆壁裡,沒來得及脫身。 「讓開!」布雷粗魯地推開解剖台前的眾弟子。 被固定在台上的是一條狗,被乙醚麻醉了。腿的部分被切開,露出動脈。 「我們正在進行極為困難的解剖,」克倫黏膩地挖苦說。油嘴滑舌是他最擅長的。「兩位卻突然闖進來打擾。我們正要把動脈壁一片片小心地剝開,一直剝到薄得可以看到血液呢。」 「無聊透頂。」布雷嗤之以鼻。 「這很重要的,因為我們要調查動脈壁是否具有再生能力。布雷先生,假設您的動脈受到損傷、大量出血,如果這時候您的動脈壁具有再生能力,不是挺讓人安心的嗎?」 比起克倫輕浮的碎嘴,亞伯不著痕跡遞出去的一枚基尼金幣更加立即見效。老樣子了。布雷抿住了嘴。亞伯雖然外表一副窮酸相,父親卻是個富有的貿易商,所以荷包總是鼓鼓的。一基尼相當於一名外科醫師兩天的薪水,可以買下一整桶琴酒。盜墓者販賣屍體的價格,一般也是一具一基尼。這金額用來堵嘴原本是綽綽有餘,然而黑爾茲從布雷手中捏起刻有喬治三世陛下肖像的金幣後,卻擱在狗屍的腿邊。 原本不收賄賂是弓街探員的最大特色。 在現任治安法官約翰.菲爾丁的異母兄亨利.菲爾丁(註:Henry Fielding,一七○七~一七五四,劇作家及小說家,著有《湯姆.瓊斯》等作品,有「英國小說之父」的美譽。曾編輯報紙,抨擊時政,並擔任治安法官)就任西敏地區治安法官之前,倫敦市內並沒有公家警察組織,治安皆由民間人士負責維持,只要逮捕罪犯,即可獲得報酬。尤其若把死罪難逃的罪大惡極者交給官吏,就能獲得可觀的獎勵金。由於民間警察除此之外收入別無保障,因此無不致力於逮捕罪犯—即便抓的大多是犯了小罪,甚至無辜之人。但是只要能收到大筆賄賂,縱然是窮兇惡極的罪犯,他們照樣放過。更何況治安法官一職只是一種名譽職位,近似於無給的服務。 亨利改革了此一亂象。他將值得信賴的幾名警吏收編為直屬,支付一定的薪餉,嚴禁收賄。 他的異母弟弟約翰協助兄長,在亨利過世後繼任治安法官,更進一步擴充及強化治安組織。他在各地區設立分署,與當地警吏聯手糾發犯罪。除了徒步巡邏的警吏外,也組織騎馬巡邏隊。說到過去的夜間巡邏隊「查理巡夜人」,成員全是些老人。但由於公家人手不足,因此民間依舊盛行密告和私下搜捕,目的當然是獲取獎金。 約翰年輕時便雙眼失明,被稱為「盲眼法官」。雖然失去視力,但是他的聽覺敏銳,罪犯對他那雙能辨別真假的耳朵無不聞風喪膽。 治安隊員被稱為弓街探員,是因為法官官邸位在柯芬園的弓街四號。法官官邸除了是法官住宅,也兼治安法庭,並設有可暫時收容人犯的拘留室。若是微罪犯,可依治安法官的權限直接宣判刑罰,重罪犯則移交俗稱「老貝利」的中央刑事法庭。嫌疑人在接受審判、決定刑罰之前,得先關進監獄。 丹尼爾的解剖教室位在柯芬園的萊斯特廣場及卡斯爾街之間,離法官官邸不遠。 不,稱它為「丹尼爾解剖教室」並不正確。現在正在進行解剖的地方,是丹尼爾的私人解剖室。開設、經營大規模「解剖教室」的人是丹尼爾的哥哥羅伯特.巴頓,因此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羅伯特.巴頓解剖教室」。 弓街探員以清廉聞名,但儘管領有薪餉,也少得可憐:週薪為十三先令六便士,至多十七先令。倫敦市民對於用稅金支薪給警察,賦予部分市民公家權力的觀念不具好感,政府也不願出錢支持。儘管菲爾丁兄弟懷有遠大的理想,但會有黑爾茲和布雷這類鼠輩出現,也是莫可奈何之事。 「醫師,」黑爾茲放柔了聲調說。「事關重大。這次醫師從盜墓人手中買下的屍體,可是準男爵查爾斯.拉夫海德的千金伊蓮小姐呀。」 弟子們對望了一眼。懷孕六個月的千金小姐。 「我們什麼也沒買呀!」克倫急匆匆地嚷著說,其他三人也扯著嗓門亂喊一通。多虧他們的努力,丹尼爾「小姐?不是夫人嗎?」的喃喃自語聲,似乎沒傳進弓街探員的耳裡⋯⋯才對。丹尼爾醫師在解剖和實驗方面是無人能出其右的傑出人物,然而他對世俗應對卻是漫不經心、粗枝大葉,弟子們對此都有共識。 「您知道拉夫海德家嗎?」 「沒聽說過。」丹尼爾冷淡地應道。「不是我的病家。準男爵?是用錢買爵位的暴發戶嗎?」 「居然殘忍地切割黛綠年華的小姐遺體,」沒撈到金幣的布雷,假惺惺地大聲埋怨。「太冷酷無情了。」 「布雷,」丹尼爾冷冷地說。「你想讓一個連胃袋在身體哪個部位都不曉得的醫師治療你嗎?」 「不,那是兩碼子事。」黑爾茲插口,但丹尼爾不予理會。 「布雷,你知道把血液運送到全身的器官是什麼嗎?」 「醫師,我雖然胸無點墨,但這點事還知道好嗎?」布雷用拳頭輕輕敲了敲胸口。 「沒錯,是心臟。但是短短一百數十年前,一般定說都還是血液由肝臟運送,而且就連醫師也不曉得血液會循環全身。利用解剖學證明心臟才是運送血液、使血液循環的器官的偉人,就是我們英國的威廉.哈維博士。這真是太輝煌的成就了!然而,然而⋯⋯」丹尼爾仰頭望天。白色的灰泥天花板一片髒污。「在解剖學方面最落後的國家,卻也是我們英國!這都是因為對解剖人體的偏見導致。一整年來,公家下放給我們的罪人屍體,只有少少的六具而已!而且還被理髮外科工會(註:歐洲早期理髮師可兼任放血、動外科手術的工作。西元一五四○年時,英王亨利八世同意理髮師公會與外科醫師公會合併,此工會在一七四五年分裂。一八○○年英王喬治三世成立皇家外科醫學院,從此理髮師不可再從事醫療手術)給霸占了。這樣怎麼可能進行充分的解剖實習呢!」 弟子們都提心吊膽地看著老師。老師只要一演說起他的主張,不管對象是誰,都會口若懸河、沒完沒了。丹尼爾生長在蘇格蘭鄉村,腔調裡帶著濃濃的蘇格蘭口音,而且笨口拙舌,很符合他那副馬鈴薯般的風貌。但即使說得結結巴巴,他仍然堅持要發表意見。 「在巴黎,有完整的法律保障研究者取得研究所需的屍體,數量充足,然而看看我們英國現在……」 「醫師,那些話去跟上頭的人說吧。」黑爾茲打斷他。「我們的工作是維護倫敦的治安,逮捕違反法令的傢伙。」 「沒錯,快把拉夫海德家的小姐交出來!」布雷愈說愈激動。 「醫師,您就算要偷,好歹也該偷伊蓮小姐的奶媽屍體,那樣就不會鬧出事來了。」黑爾茲倒是很冷靜。 「奶媽也死了嗎?」 「小姐過世,奶媽悲痛過度,追隨小姐去了。」 「聽說是在墓前服毒自殺的。」 「服毒?什麼毒?」出於職業病,丹尼爾首先對這個問題感到好奇。 「誰知道啊?」 「真是疏忽了。奶媽的屍體我也想要。」 「廢話少說,你們把小姐藏哪去了?我們要搜房子囉!」
* * *
轎子為了減輕重量做得很輕薄,於是兩三下就被打壞,跌出一個打扮華貴的少女。 瞬間,納森衝出馬路。 他奔過去扶起少女,把她攙扶到店裡。 幾名手持武器的壯碩男子騎馬趕來。這些人就是愛德他們說的弓街探員嗎?納森這才看到了本尊。 書店裡面跑出兩個驚慌失措的男人。一個是剛才瞧不起納森的店員,另一個體態肥胖、頭髮半禿,肥厚的鼻子上戴著夾鼻眼鏡。 「小姐!」 「出了什麼事?!」 小姐的塔夫綢裙子裂了一條縫。這種情況,通常女性都會佯裝昏厥以強調她們的孱弱,然而這位小姐卻以冷靜的舉止在附近的椅子坐了下來。 「我平常雇的轎夫不巧生病,真不該在路上隨便攔轎的。」 「小姐連僕人也沒帶就出門了嗎?這怎麼行呢?」夾鼻眼鏡男用力揮手說。 「我接到通知,說普烈菲斯神父的《瑪儂.雷斯考》到了,所以急忙趕來了。」 「是的,小姐。前些日子的船運總算從法國送來了一本,所以我立刻派跑腿的小廝到貴府通知。聽說賣得很好,又增刷了。普烈菲斯神父過世已經好幾年了,卻人氣依舊,似乎格外受到婦人們的青睞呢。」 「可以讓我看看嗎?丁道爾先生。」 「當然,當然,書是小姐訂的嘛。不過還沒有縫綴起來,只有折好的書稿而已。」 可是,一個大家閨秀居然讀這種放蕩的愛情故事,真不知道小姐的父母會怎麼想—戴夾鼻眼鏡的丁道爾先生嘴裡嘟噥著,開始在架上找起來。 「奇怪,我明明就放在這裡呀?」 店員撿起散落在地上的紙張,遞給老闆。 「怎麼會掉在地上?是你幹的嗎,費拉?」 「絕對不是。我很清楚這是店裡唯一僅有的貴重書稿。而艾凡斯先生就像您看到的,正沉浸在魯賓遜.克魯索的孤島生活裡,甚至沒有從椅子上站起來。是這傢伙幹的。」 費拉筆直地指著納森說。 「肯定是這小鬼幹的。我發誓,就是這傢伙幹的。」 沒錯,納森不得不承認,就是他幹的好事。為了解救小姐的危機,他丟下手中的書稿趕了過去。 被說是沉浸在魯賓遜孤島生活的艾凡斯先生,頻頻偷瞄小姐和納森。 「你是哪位?」 丁道爾先生調整了一下夾鼻眼鏡的位置。 「我叫納森.卡連。剛才這位先生應該替我傳話了。」 「只是個不曉得哪來的小子罷了。」費拉插嘴說。「我想沒必要驚動忙碌的老闆您。」 「這位先生就像個騎士,把我從那場騷亂中拯救出來。」 納森聞言,竭力將感謝之情表現在臉上,一手擺在胸前向小姐行禮。 「佩勒姆先生—─他是我家鄉教區的牧師——他的信應該已經寄達您的手中了。」 「有嗎?哎,我這兒收到的信可多了。」 「牧師說,丁道爾書店的丁道爾先生,是倫敦第一——也就是世界第一——值得信賴的出版業者。牧師說您對作品的眼光很高。」納森並非奉承,而是滿懷熱忱地陳述事實。 「多謝誇獎。」然而,丁道爾先生嘴上浮現的卻是苦笑。「不是因為你誇我才這麼說,但我想起來了。納森,聽說你發現了十五世紀的神職者所寫的詩篇?」 「是的。」納森激動起來。「很驚人的發現對吧?我把它帶來了,請丁道爾先生務必過目一番。」 丁道爾先生臉上的表情半信半疑——或者說,九成都是嗤之以鼻,但有一成期待那是可能是真貨。 納森把一疊珍貴的羊皮紙放到桌上。 「十五世紀的神職者所寫的詩篇」——這話似乎具有將艾凡斯從孤島上召喚回來的魔力。他發出聲響、拉開椅子,離開看書台走過來,並探頭問道:「哪裡?我看看。」 納森出示最後一張說:「上面署名『一四八五年十一月三日記之。神明忠實的僕人托馬斯.哈瓦德』,所以我想應該是神職者的作品。」 納森接著強硬地說:「然後……呃,我也寫詩,希望請您過目。」 「你想出版你的詩?」 「是的,我認為它值得出版。」 「兩邊都得花時間慢慢研究才行。在那之前,先處理伊蓮小姐專程前來的要事吧。」 費拉在桌上整理好散落的書頁遞給老闆:「我想順序這樣就沒錯了。」然後瞪了納森一眼說:「受不了,都是這臭小子,給人惹麻煩。」接著他向小姐露出諂媚的笑:「幸好地板剛打掃過,書頁沒有污損。」 「這是小店的缺失,請讓我提供一些折扣。」丁道爾先生提議。 「你真是個有良心的老闆,丁道爾先生。」 小姐笑著接受。納森覺得她笑起來真有如一群華艷的蝴蝶翩然起舞。 「難道,」原本在看納森帶來的「十五世紀的神職者的詩篇」的艾凡斯抬起頭來。「您是拉夫海德準男爵家的千金嗎?」 小姐沒有回話,費拉替她答道:「沒錯,這位是伊蓮小姐。」 艾凡斯走近,恭敬地把手放在胸前行禮:「我是令尊的朋友。以前拜訪府上時,曾經見過小姐。我叫蓋伊.艾凡斯。」 伊蓮小姐只是冷淡地頷首回禮。 「小姐想要什麼樣的裝幀呢?」丁道爾先生問。 「用法國摩洛哥皮革,蕾絲花邊樣式。」 「我去拿樣本來,請小姐挑選金箔花樣和皮革染色。費拉,去拿花紋的樣本冊還有皮革樣本,還有花布的色樣。」 花紋與皮革的樣本冊。納森覺得好像在討論自己的詩集裝幀一般。蕾絲花邊樣式是這個世紀開始出現的新設計樣式,蕾絲般纖細的花紋金箔沿著書緣的邊框烙下,中央部分留白,或是飾以花朵圖案或紋章。與前世紀的賈斯康樣式及更古老的凡法爾樣式、修道院樣式等設計相比,顯得優雅許多。 「專門負責小姐書籍裝幀的金箔師傅病倒了,好像是肺出了毛病。哦,請不必擔心,我們還有其他熟練的師傅。」 伊蓮小姐在挑選的時候,納森就站在她身後,隔著她的肩膀觀看各種樣本。艾凡斯先生把魯賓遜丟在孤島上,只顧著翻看「十五世紀詩篇」。 挑選出染成深紅的法國摩洛哥皮革,決定封底的設計時,伊蓮小姐的臉色愈來愈糟了。 「恕我失禮。」小姐用手帕摀住嘴巴,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請問……化妝室……」 納森立下判斷,跑到伊蓮旁邊,脫掉外套,蹲下來接住伊蓮的嘔吐物。他把嘔吐物包起來擱在房間角落,把伊蓮扶到長椅去。 「請坐在這兒稍事歇息。」丁道爾先生慌亂地靠過來說。「費拉,拿水給小姐喝。還有,去拉夫海德家通知小姐身體不適,請他們派人來接。」 「不,不需要。」小姐小聲說。「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好的。那麼請您慢慢休息。」 「我想鬆開衣服⋯⋯」小姐招來納森。「可以請你閉上眼睛,幫我鬆開這邊的繩子嗎?」 納森照著吩咐做。小姐解開衣物前襟,柔嫩的手指把他的手牽引到以鯨骨馬甲勒高胸脯的褻衣繩索處。納森閉起的眼皮底下,小姐的胸脯就像發光的燐火般閃耀著。 小姐放鬆下來,在長椅躺下之後,納森小聲向丁道爾先生請求說:「我想清洗一下衣物。」 「扔掉。」丁道爾先生對房間角落的外套投以嫌惡的視線。 「可是……」那可是納森唯一一件像樣的外套。但愛面子的納森無法說出實情。 「丟去外面的垃圾桶。」 納森照著指示丟掉外套後,回到店裡一看,小姐躺在長椅上閉著眼睛假寐。 「你這樣一個孩子,是怎麼弄到這份古文書的?」丁道爾先生隔著眼鏡盯著納森看。 納森不是孩子,他已經十七歲了。因為個子嬌小,他經常被人誤認為比實際年齡還小。 艾凡斯也盯著納森看。 「佩勒姆牧師寄給您的信裡,應該交代了發現的經過才對。」 「我想親耳聽你證實。」 「是在亡父的遺物中發現的。家父是教會的學校老師,他愛好讀書,也擁有與我們家經濟情況不匹配的大量藏書。家父也蒐集老東西,無論是什麼有年歲的東西,家父都會付出敬意與愛情。教會的建築物曾經改建過,是我出生很久以前的事了。」 「嗯、嗯。」艾凡斯點頭應和著。看到聽眾熱心聆聽,納森愈說愈起勁。 「聽說當時整理了紀錄保管室,丟棄了古老的文件。羊皮紙之類的東西原本就要被下人拿去燒掉,卻被家父要了回來。我繼承了家父的興趣,愛看書勝過任何事。我把家父留在閣樓裡蒙塵的書本都讀遍了。家母和家兄對書都沒有興趣,如果沒有我的保護,那些書早已被一本本扔進爐裡當柴燒了。」 「佩勒姆先生的信裡面也提到,你年紀還小,對古文書卻十分熟悉,而且知識豐富。」 「這部詩篇也是在閣樓裡發現的。是在父親要回來的古文書裡找到的。文書大半都是教會的年間活動或收支紀錄,不怎麼有意思,發現這部詩篇時,我有多麼地感動,我想丁道爾先生應該能夠了解。」 「你讀得懂這篇用古老字彙寫下的艱澀詩篇?」 「我讀得懂。我利用古語辭典等工具做輔助,全部讀完了。因為這樣,我通曉了不少古語。」 「這東西暫時保管在我這裡吧。這陣子假貨很多,必須確實鑑定一番才行。」 「好的,麻煩您了。」納森說著,從成疊的羊皮紙裡面抽出一張,留在身邊。 「為什麼抽走一張?」艾凡斯問。 「為了預防萬一,免得詩篇未經我允許被拿去使用。」 「這小鬼怎麼這麼失禮!」費拉厲聲說。「你不相信丁道爾先生嗎?!」 丁道爾半帶苦笑地制止費拉。 「還有,丁道爾先生也願意讀我的詩作吧?」 「擱在那兒,我晚點再看。」 「拜託您了。」 「您舒服些了嗎?」丁道爾先生對伊蓮小姐說。她已經綁好內衣繩索,理好凌亂的衣服,從長椅坐起上半身。 「嗯。我平常很喜歡皮革的味道的,今天卻突然⋯⋯我沒事了,要告辭了。」 「要幫您攔轎子嗎?還是叫馬車?」 「萬一搖晃,似乎又會不舒服起來,我用走的回去,反正也不遠。」 「我送小姐回去吧?」艾凡斯自告奮勇,但伊蓮沒理會他。 「費拉,你陪小姐回去。」丁道爾先生說。「不必了,我請我的騎士送我。」伊蓮回絕,然後對納森說:「先生,可以請你送我一程嗎?」 「樂意之至。」納森打從心底這麼說。 自古以來,告誡戀愛之愚昧的人不知凡幾。納森也讀過那些文字:「戀愛就是兩個人一起變得愚笨。」眼前納森正是變得愚笨了,但他並沒有自覺。有人說:「人總是墜入愛河,然後就像墜河時那樣,嘗盡苦頭。」還有更辛辣的:「戀愛!那麼你能去愛對方的消化器官、腸子、排泄器官、鼻水、擤鼻涕的鼻子或吃東西的嘴嗎?只要想想這些,熱情也會稍稍減退吧。」但納森連想都不去想。雖然提醒戀愛之可怕的多是法國人,但英國人的莎士比亞也曾在《愛的徒勞》裡寫下這樣的台詞:「那完全就是一種膽汁質疾病,將血肉之軀視若神明,把小母鵝奉若女神。」 納森不到十歲就讀遍莎士比亞作品,卻絲毫不懂得戀愛的本質。 小姐在服裝店前停下腳步。她穿著連帽斗篷,但納森只剩下一件襯衫,被外頭刺骨的寒風凍得嘴唇都失去血色了。 「小姐,歡迎光臨。」店員出來招呼,小姐要求說:「我要找適合這位先生的外套。」 「好的,我來量尺寸。」 「我很急,現在就要。」 「小姐也知道,小店只接受訂製。」 店員一面對小姐搓手哈腰,一面以冰冷的視線觀察納森的破鞋。 「我想到舊衣鋪找會比較快,可是也不能讓拉夫海德準男爵家的伊蓮小姐移駕到舊衣鋪。為了報答小姐平日對小店的關照,讓小的跑一趟,為這位先生找件適合的外套過來如何?」 「麻煩你了。」 「請小姐進店裡休息。正好來了一批美麗的法國蕾絲,我想小姐一定會喜歡的。」 兩人被帶進一個房間,其他店員送來各種布料的樣本,不停地談論法國的最新流行,但伊蓮小姐聽得漫不經心。 外套總算送來了。雖是舊衣,卻也比納森的唯一一套好衣服高級太多了。 「算是糟蹋了你的外套的賠禮。」然後她問店員:「可以找個人送我回家嗎?我和這位年輕先生要在這裡道別了。」 當伊蓮小姐伸出手說「請保重」時,納森不由得像個榮獲授勛的騎士般跪了下來。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剖開您是我的榮幸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4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60 |
二手中文書 |
$ 308 |
推理小說 |
$ 308 |
文學 |
$ 343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剖開您是我的榮幸
「這本推理小說了不起」「最想讀的推理小說」「週刊文春最佳推理小說Best 10」
「第12屆本格推理大獎」得獎作品
被刀剖開的,是肉體、謎團,還是深不可測的人心……?
在18世紀的英國倫敦,解剖屍體被視為違背倫常的異端。外科醫生丹尼爾與五名對醫學懷抱熱情的弟子潛心研究解剖學,終日與非法入手的死屍為伍。每當下刀之前,他們總會低喃著:「剖開您是我的榮幸……」豈料,丹尼爾某天向盜墓人買來的孕婦屍體,竟是一位剛下葬的貴族千金。警察前往解剖教室搜查,卻發現另外一具四肢裁斷、面目全毀的男屍,疑似是從鄉下來到倫敦、懷抱詩人夢想的少年納森。雙目全盲的治安法官約翰,與女扮男裝的外甥女助手循線追兇,嫌疑者卻陸續暴斃。霧都的黑街暗巷內,方興未艾的科學求證精神,善惡難辨的私法制度,難以扭轉的階級差異,架構成一部唯美、血腥、結局百分百出人意料的推理傑作!
作者簡介:
皆川博子
1929年生,現年84歲。東京女子外國語大學肄業。於1952年結婚後成為家庭主婦,空閒之餘廣泛涉獵文學作品,於是立志成為作家。以《海與十字架》出道成為兒童文學作家之後,由於受到中井英夫、赤江瀑等人的影響,轉向為創作懸疑、幻想文學。她從80年代開始涉足推理文學,在新本格推理的領域受到高度評價。
曾獲學研兒童文學獎、小說現代新人獎、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直木獎、柴田鍊三郎獎、吉川英治文學獎、本格推理大獎、日本推理文學大獎。皆川博子為了寫成本書,熟讀狄更斯著作及英國18世紀文史研究書籍,嚴謹的考究精神與精湛的寫作功力,實至名歸的贏得2012年本格推理大獎,同時也是史上最高齡的獲獎人。
章節試閱
「快藏起來!」 把後門打開一條縫、窺看外頭的克倫,緊迫地低喝一聲,隨即把門關上。 仰放在台上的軀體,高高隆起的腹部皮膚被切割成十字狀,朝四方掀開,露出鼓脹的子宮。 地板撒了木屑,解剖台底下蜷趴著一條雜種狗。 聖喬治醫院外科醫師丹尼爾.巴頓的手指,正用異於肥短外觀的纖細動作將著色蠟注入遍布子宮表面的血管。動脈已經注完了紅色蠟,現在正在為靜脈注入藍色蠟。 這裡並不是丹尼爾任職的醫院,而是他的私人解剖室。 聽到克倫的通報,正注視著老師手部動作的「胖班」血色紅潤的臉頰剎時變得蒼白。 「老師,請先暫停吧。」愛德低...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皆川博子 譯者: 王華懋
- 出版社: 圓神出版 出版日期:2013-12-31 ISBN/ISSN:978986133482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32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推理小說
圖書評論 - 評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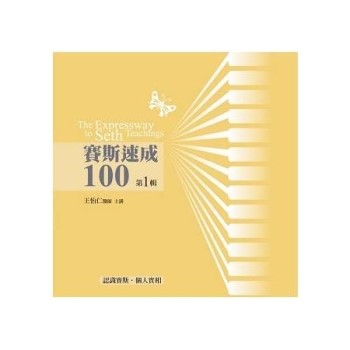









台灣對皆川博子相當陌生,查了維基百科才知道她已經高齡84歲(1929或1930年出生),一共發表了八十多本作品(多數為小說),更讓人感到意外的是皆川博子 發表她的處女作發表在43歲的時後(1972年出版的『海と十字架』),中年才開始從事創作的作家,通常會持續比較久的創作生涯。皆川博子以『恋紅』這本書獲得第95回直木賞(1986年),台灣一直到2014年才引進她的作品,實在有點「過份有耐心」了吧! 既然以前沒有引進繁體中文版,我自然沒有閱讀本書以外的皆川博子的作品,只能就本書來瞭解這位陌生的作者,本書發表於2011年,日文原文書名:『開かせていただき光栄です』,與中文書名完全吻合,書名相當怪異,但絕非標新立異故弄玄虛,書名和內容的吻合度相當高呢! 皆川博子最不簡單的地方在於,如果不讓讀者知道本書的作者是誰,所友讀者絕對會以為這是一本如假包換的英國小說,不論是主配角、跑龍套亦或是所有場景,完完全全是十八世紀初葉的英國倫敦的故事,可見皆川博子對於三百年前的英國的考據所下的功夫。 小說迷人之處在於帶領讀者進入虛虛實實的時空,本書故事背景放在八世紀初葉的英國外科醫生的解剖實習上頭,當年的外科醫生的地位不高,連理髮師都可從事外科手術,可見當時的社會漠視外科手術這個領域,更別提為了訓練外科醫生的解剖實習課程,解剖人體更是社會忌諱被視為敗德且違法的行為,外科醫生為了瞭解人體構造或訓練實習生,往往得踏著法律紅線透過特殊管道如盜墓或貧民窟中尋找可供解剖的屍體。 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天,不小心向盜墓者買到一具貴族的女兒的屍體,而這具女屍竟然懷有身孕,引起倫敦警察司法當局的調查,更荒謬的是,在警方臨檢前醫生們將這具女屍藏了起來,豈料搜查之下,居然還意外地多出了兩具屍體? 故事的軸線當然不僅僅在這群外科醫生與實習生上頭,還有盲眼的法官、女偵探、股市炒家、無賴記者、COSPLAY的解剖學徒、天真的鄉下文青、名醫、貴族女兒....等等攪和成一團宛如迷霧般地兇殺案件內。作者結合了許多推理小說中的經典元素,如消失的屍體、連續殺人、幾百年前的古文珍本書、密室、辦案的盲眼法官。 更讓我感到訝異的是,已經高齡八十的老奶奶作者除了嚴謹的考據以外,角色的安排相當有新意,如男同性戀、女扮男男扮女的cosplay、炒股作手,除了解剖檯的黑色幽默氣氛外,還加入了倫敦當年貧民窟、妓女院、賭場、咖啡廳和茶館等氣氛迴異的各種場景來塑造相當多元的氣氛,套句文學形容詞:耽美。 推理查案的過程和案情的發展,相對於背景的塑造就弱了一些,作者用了計中計、案外案以及埋了許多讓案情一再轉彎的情節與鋪陳,雖然結局頗讓我感到意外,但案情本身的閱讀張力完全比不上十八世紀解剖檯上的光怪陸離。 讀小說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每本小說都會召喚出不同的讀者不同的自我情緒,由於我的背景是財經,所以對於故事中所提到的炒股、貪婪和書中所提到的金融股價泡沫相當感到有趣,雖然作者著墨不深(大概是礙於自身專業限制吧),但可以看到早在三百年的英國就可以看到股票作手與報社老闆的炒作勾當,人們因為貪婪而鋌而走險擴充信用遭不肖人士坑殺的戲碼,幾百年來似乎如出一轍。 比較可惜的是,本書出場人物略嫌多了一些,估計砍掉三分之一都還不影響故事架構與內容佈局,計中計的轉折次數有點偏多,雖然推理小說的書迷完全不在乎被作者欺騙甚至還會樂在其中,製造懸疑,套牢並愚弄讀者本來就是作者的天職,但案情急轉直下的轉折次數過多似乎也造成許多情結交代地不太清楚,小說的中後段正因為如此而讀起來有點冗長並感到吃力。 持平而論,由於描寫的職業(十八世紀的外科醫生的解剖行為)與時空背景相當罕見且引人入勝,推理進程上的小小折損其實仍舊是是瑕不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