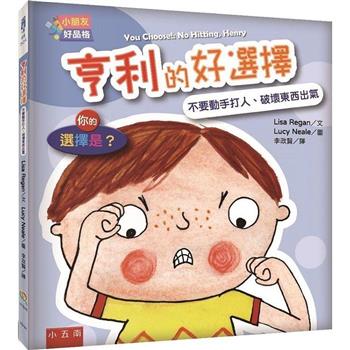推薦序
《史記.司馬相如傳》說:
「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我讀了《李遠哲傳》書稿,太史公這幾句話自然而然地浮現在我的腦際。
《傳》中的主人翁(按:以下簡稱「傳主」)是一位「非常之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隨著這位「非常之人」而來的「非常之事」和「非常之功」也彰彰在人耳目。這部傳記依時序先後,以生動活潑的語言,將傳主其人、其事、其功一一呈現出來;這一成就的本身便是傳記史上一種「非常之功」。
在閱讀全稿的過程中,我一直在追尋一個問題:傳主為什麼會成為一位「非常人」?當然,我最先想到的是傳主的天賦才智,或今天所謂先天基因。這一點在傳稿中有不少跡象可尋:他從小「好奇」,愛「唱反調」,不肯人云亦云地跟著主流走,因此在幼稚園時期已被看作是一個「怪小孩」。不但如此,早在考初中的口試中,他對於「將來想做什麼?」的答案便是「我要當科學家」。在初一班上寫自傳,他更毫不遲疑地表達了「想成為偉大科學家,要以科學救國」的嚮往。
這些早年的突出事蹟都是很值得注意的,但是我並不認為他為什麼成為「非常人」可以從這裡得到滿意的解答。其故有二:首先,這些事蹟所體現的只是傳主的生命潛能,而不是成為「非常人」的可靠保證;其次,根據現代的史學觀點,在傳記中過度重現童年事蹟,往往會淹沒傳主生命成長的實相。當代史學大家彼得.布朗(Peter Brown)在他的名著《奧古斯丁傳》(Augustine of Hippo, 1969)中指出:
「在古代和中古的許多傳記裡,傳主們好像都沒有以往的歷史,他們童年已顯示種種跡象,將來必將攀躋生命的高峰。」
所以他在《奧傳》中,深入而詳盡地追溯了奧古斯丁在生活和思想各方面的發展歷程。
對傳稿記述反覆思考之餘,我發現有一條相關的線索特別值得稍作探索。這是指傳主在童年至少年階段所吸收的某些精神價值而言。這些價值淵源於傳主成長時期的社會和文化,但通過父母訓示、師友交游、書刊閱讀等等渠道而進入他的意識深處。在這篇短序中,我希望能把這一觀察簡要地交代出來。
傳主是很幸運的,從小便得到父母的刻意培育。他們隨時隨地都在扶植著他的德性成長和智力發揮,讓他在日常生活中逐漸養成一種健康的人生觀;但同時又尊重他的自由意志,使他可以充分地實現自我。傳主後來談到怎樣教育孩子時,說過這樣的話:
「孩子對未來有什麼想法,想做什麼,我都尊重。(當年)爸爸媽媽沒有要我們變得很有名或賺大錢,只希望我們做有用的人,對社會有貢獻。」
傳主這番回憶在傳稿中到處都能得到印證,這裡只要舉兩個例子便夠了。
第一,傳主小學五年級時,由於成績超前,導師對他的父親說,他可以跳級考初中。但和一般「望子成龍」的父親不同,他的父親讓他自己做決定。由於他的興趣多端,不願終日為考試而讀書,終於放棄了跳級的機會。回顧往事,傳主多年後說:「父親很開明,讓我自己決定。」
第二,傳主一九九四年回歸臺灣之後,十分忙碌,連探望母親的時間也不多。他的母親只能天天剪下有關傳主一切活動的新聞報導,然後整理收藏起來。
傳稿中有幾句描寫老人家心裡的話,十分動人:
「她就反覆細讀剪報,想到他一如她自小教誨的:『不要追求名利,只要做個有用的人,一個頂天立地堂堂正正的人。』就感到安慰了。」
傳主一生的操守的基本價值最初來自家教,在此正顯露無遺。
傳主的另一難得的幸運是有一位志同道合的終身伴侶,後者曾這樣剖析自我:
「我不喜歡到處玩,也不在乎名利,我可以一個人靜靜地看書,做很多事情,不要人打擾。」這豈不也是「不要追求名利,只要做個有用的人」嗎?沒有這樣的伴侶的長期支援,我們很難想像傳主怎樣能獨自通過那條布著荊棘的「非常人」之路。
讀者也許會說,上面所揭示的基本價值都是很平常的。這話完全正確。這些價值在中國文化中傳衍已久,往往以不同的語言方式表達出來,如曾國藩「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及陸象山「不識一字,也要堂堂做一個人」等語都是顯例。但這些平平常常的價值,一旦與人的精神融為一體,卻能開創出一種完全超越於世俗利害之上的心態,借用禪宗的話,即「平常心」。古往今來,一切在世間立功、立德、立言的「非常人」,其根本動力無不可以溯源到這一超越的「平常心」。
現在讓我們換一個角度,看看傳主從書刊閱讀和師友交遊所得來的關於整體社會的價值取向。
傳主閱讀課外書刊,開始得很早,小學五年級時已看上海出版的《開明少年》。上初中以後,由於特殊的機緣,他竟讀到大批「禁書」和「匪情資料」,其中包括魯迅、郭沫若、巴金等人的作品,甚至還有毛澤東的文字。在他個人的思想進程中,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轉捩點,因為他踏進了「五四」的左翼思潮之中。從傳稿中我們看到:改造社會的抱負貫穿了傳主一生的工作。現在我們可以進一步肯定,這一抱負是從上述的思想躍動中萌生的。課外閱讀怎樣影響到傳主的終極價值取向,我們可以從他另一早年經歷中得到具體的說明。
傳主在初中時候已讀了《居里夫人傳》,對這位偉大科學家的高貴情操,不勝其景仰。但高一那一年,他得了一場病;在休養期間忽然發生了「人生是為什麼?」的根本疑問。就在這苦求解答的當口,居里夫人的光輝典範在他的記憶中浮現出來,終於引導他走出了一次重大的人生困惑。他後來回顧說:
「我迷惑、徬徨的心靈因此獲得解答。她美麗的、充滿理想與熱愛人類的科學生涯,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啟示與追求的目標。至此,我立志救國淑世,想竭盡己力,期望對人類社會有所貢獻。」
這是一場「大澈大悟」,所以他對自己說:
「人生就是要做有意義的事。我不能再像無頭蒼蠅忙著打球、比賽、管樂隊等數不盡的活動,我要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我要成為有用的人,才能對國家社會有貢獻。」
他的社會價值取向,至此已完全確定了。「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
傳主「立志救國淑世」雖直接因閱讀和反思《居里夫人傳》而激起,但其更深一層的動力卻必須追溯到「五四」思潮。「五四」運動正式揭出「科學」和「民主」為救國的兩大法門,缺一不可。這一信念當時正在少年傳主的心中生根,而《居里夫人傳》則恰好為「科學救國」提供了一個具體的例證。不過「民主救國」在他的意識中尚處於「明而未融」的狀態,直到幾十年後,才和他改造社會的抱負合成一體。
通讀全傳,傳主一生的事業顯然可以劃為前後兩大階段,而以一九九四年為分界線。兩期的工作重點各有不同:前期是他全心全意獻身於科學研究的階段;後期他則以科學界領導人的身分同時致力於民主社會秩序的建立。他以一人一身竟先後體現了「五四」的雙重理想──「科學」與「民主」,這真是難得一見的歷史佳話。前期人所共知,此不具論。但後期卻應該稍作解釋。
二○○一年傳主追憶他從美國回臺灣的心理狀態時說:
「一九九四年元月,旅居美國三十多年之後,我終於回到我的故鄉。……
我離開加州大學的時候,很多化學系同事問我:難道臺灣真的那麼美好?為什麼我願意放棄長期建立的穩固基地,捨他們而去?
我告訴他們,如果臺灣已是美好的地方,我會繼續留在加州大學的實驗室,埋首我的研究工作。臺灣雖曾被稱為美麗島,但眼前顯然有許多問題正待大家努力去解決。在全球化、民主化的過程中,臺灣確實充滿了挑戰與希望。科學、教育與文化的提升更是迫在眉睫,這也是我為什麼願意接受挑戰,回到我幼時成長的故鄉,與家鄉父老同甘苦。」
他的意思再清楚不過了,他回臺灣絕不是為了換一個實驗室進行科學研究,甚至也不僅僅是為了「科學、教育與文化的提升」。他是為了接受「全球化、民主化」的挑戰,全方位地將臺灣變成一個「美好的地方」。這只能指向一個民主秩序的建立。
事實上,回到臺灣以後,他的工作遠遠超越出中央研究院的本職之外;舉凡教育改革(一九九四~一九九六)、「九二一」震災重建(一九九九)、首次政黨輪替(二○○○)、出使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PEC,二○○二~二○○四)等等,他不但一一參與,而且還承擔了主要責任。所以二○○○年五月,美國《科學》(Science)雜誌發表評論,一方面讚揚他在短短幾年之內將中央研究院的國際學術地位提升至空前的高度,另一方面則因為他在「九二一」重建和社會改革方面的貢獻而譽之為「臺灣的良心」。
改造社會畢竟與科學研究不同,所牽涉的條件無限,一切不由自主。傳主的努力曾因此而遭到種種挫折,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但他的抱負卻始終沒有動搖過。傳主回歸臺灣,至今已二十二年。在這二十二年中,一個自由、開放的民主秩序終於在臺灣出現,並且日趨於成熟。這當然是整體社會長期奮鬥之所致,不能歸功於任何個人以至團體。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的傳主通過多方面倡導所發揮的影響力終究是不容隱沒的。著眼於此,傳主一九九四年回歸臺灣的歷史意義便朗然展現了。這不禁使我聯想到十九世紀英國神學家兼作家紐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的一句名言: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胡適的譯文說:
現在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便不同了。
我願意借這句話來結束這篇序文。
文/余英時(中研院院士)
二○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推薦序
李遠哲院長一直是國內外學者見賢思齊的楷模典範,他在獲得諾貝爾獎殊榮之後,毅然決然回臺灣貢獻,令人讚賞欽佩。我一直把李院長當作我的導師、兄長、好友,但是我卻在閱讀《李遠哲傳》以後,才了解他從小就立志為臺灣人民,甚至全人類服務奉獻的雄心。
一九九四年李院長回臺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為了延攬國外卓越人才來臺服務,創立了「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每年頒發「傑出人才獎」來補足旅外傑出人才回國服務的薪酬差距。舍弟建德有幸榮獲第一屆「傑出人才獎」,才能舉家返國,擔任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主任。
「傑出人才獎」引領了歸國服務的風潮,使臺灣的科技研發有很大的突破。「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也積極獎勵國內學者做出國際級的研究,我在獲得五次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後,幸運地獲頒了第二屆「傑出人才獎」,這是更上層樓的肯定。「傑出人才獎」的獎勵是有形的,李院長以身作則所展現的號召力卻是無形而澎拜的。諾貝爾獎得主回國報效臺灣所產生的磁吸效應,強大而有力。
李院長很關心周遭的每一個人,更關心國家社會與人類福祉,我常被他的高尚情懷所感動。他有時會在凌晨時刻打電話和我談重要事務,即使當時的我已經睡眼惺忪,也都被他的急公好義所喚醒,我們往往一談就是半個小時。內人總是說:「李院長的身體、精神與心靈都非常的健康安寧。」李院長一直維持充沛的精力、活力和心力,來解決臺灣與世界的問題。
二○○三年臺灣面臨SARS疫情的嚴峻考驗,我在考慮是否接任衛生署長職務時,請教了李院長的意見。他說:「現在國家處境這麼艱難,你應該要挺身而出、勇於承擔!」猶記疫情剛爆發時,人人自危、彼此猜疑;李院長與社區營造學會發起了「全民量體溫運動」,鼓勵大家從管理自己的體溫及健康做起,全民的同心同德發揮了自助互助的正面力量,更從此創造了社會互信的良性循環與安全感。當時中研院領導SARS的防疫研究,篩選出幾個有效藥物,扮演了安定人心的積極角色。
我二○○五年辭卸衛生署長職務回臺大任教,二○○六年李院長來電說:「行政院長蘇貞昌會邀請你出任國科會主委,你一定要答應喔。」我回答說:「謝謝院長的鼓勵,您對科技發展了解透徹,請您答應我,每個月與我見一次面,給我指導和建議。」從每月的請益中,李院長給了我很多臺灣科技發展的寶貴意見,就像我的導師一樣。當時我們都反對國光石化的建設,李院長一再高聲疾呼,節能減碳是人類應盡的世界公民責任,臺灣不應該再發展高耗能、高耗水、高排碳量的產業,而應該朝經濟與環境永續發展轉型。
中研院曾推薦我參加「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的天然災害防治工作小組。李院長卸任院長職務後,翁啟惠院長提名推薦他擔任ICSU會長(president)。當時ICSU的祕書長要我勸進李院長,他說李院長擔任ICSU會長可以大大提升ICSU的聲望和績效。我大膽去跟李院長說:「院長,大家都殷切期盼您到非洲的莫三比克去做提名演講。您去,全世界都會看見臺灣!」
李院長去莫三比克之前,他的講稿已經改了三、四次,到當地又多次修改。ICSU大會剛開始時,臺灣代表團的幾位院士都憂心忡忡,擔心中國會橫加干擾。但是李院長剛講完演講,周昌弘院士就打國際電話跟我說:「What a relief!(鬆了一口氣!)」因為,李院長演講結束,現場就立刻掌聲雷動;周院士知道ICSU的會員們,已準備迎接一位「真正世界級的科技領導者」。隔天,李院長果然高票當選了會長。好幾位院士看到李院長反覆修改講稿,這充分反映李院長做任何事情都是認真仔細、深思熟慮、盡善盡美,就跟他發明了「通用型交叉分子束儀器」的科學探索一樣完美無缺。
李院長在ICSU服務的期間,我聽到很多人的稱讚,以「促進國際科學合作,創造人類福祉」為宗旨的ICSU,更受到全球學術界與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讓我們感到最榮耀的是,李院長的卓越領導,不只是讓臺灣被世界看見,也讓ICSU的國際聲望大幅提升。二○一二年在巴西里約舉辦的Rio+20高峰會的會前活動是ICSU主辦,李院長代表全球科技界在高峰會中演講,呼籲急速減碳,對全球永續發展做出貢獻。去年聯合國「氣候變遷高峰會」(Cop21)通過了巴黎協議,各國承諾要遵循節能減碳的永續發展目標,李院長關懷全球事務的身影處處可見,也終於開花結果。
去年,蔡主席要我做她的競選搭檔,我也請教了李院長的意見,開始他有所保留,擔心我無法適應棄學從政的新環境,在蔡主席的說服下他才釋懷。我一直把李院長當作我人生重要抉擇的迷津指點者,因為他的博學廣識、高瞻遠矚、洞察事理、提攜後進,真是無人能及。
李院長極力支持臺灣的民主發展與政黨輪替,也因此受到許多不公平的汙衊和謾罵。但是他總是寬宏大度、包容忍耐,盼望臺灣的民主幼苗可以茁壯成長,成為亞洲的典範。他相信人性本善,也認為政治人物可以更明理、更有風度。李院長有超越常人的學者風骨,是極富涵養的人格者。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丁肇中院士,更是對李院長讚譽有加。他認為李院長不只是傑出的科學家,更是一位人道主義者,他關心國家社會的發展、全球環境的永續、人類福祉的增進。李院長完全做到了「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
我很榮幸能為《李遠哲傳》一書作序,推薦讀者來認識我的導師、兄長與好友!我何其有幸能得到李院長指導、鼓勵與提攜,他永遠是我高山仰止的典範,也希望能讀者們能見賢思齊,學習成為樂於為全人類服務奉獻的人。
文/陳建仁(中華民國副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