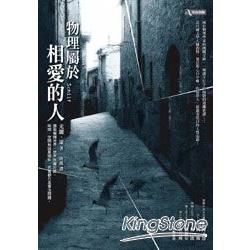第一章 薩巴斯提昂在紙上剪曲線。美可做飯。奧斯卡登門拜訪。物理屬於相愛的人。
如果要薩巴斯提昂描述他的朋友,他會說,奧斯卡看上去就像那種什麼問題都能回答的人:弦理論是否有朝一日能夠成功統一物理基本力量,燕尾服的襯衫是否能與無燕尾的禮服配穿,眼下幾點了,而且是杜拜時間。不論是傾聽的時候,還是自己說話的時候,他那雙花崗石似的眼睛總是一眨不眨地盯著對方。奧斯卡是這麼一個人:他的血管裡流的是水銀,他的腳下永遠有一座統帥土坡,他沒有幼稚可笑的暱稱。有他在場,女人就會坐在自己的手上,以免不小心向他伸出手去。他二十歲的時候,別人以為他三十歲,自從他過了三十歲,別人都說他毫無老相。他身材瘦長,前額光滑,細細的眉毛總是喜歡彎成探詢式的弧形,他的臉頰略微有些凹陷,雖然仔細地刮過臉,臉上還是留有濃重的鬍鬚的痕跡。即便他像今天這樣穿著樸素的毛衣和黑褲子,他的衣著看上去還是經過精心選配的。他身上的衣料只敢在合適的地方起褶,他的姿態往往是外在冷靜與內心緊張的混合表現,這種姿態會令別人直直地盯著他。他們在背地裡議論他,認為他是個演員。在某些圈子裡,奧斯卡還真挺有名,但不是因為他的演技,而是因為他那關於時間性質的理論。
窗外的夏日像藍綠色的帶子飛馳而過。一條聯邦公路緊跟著鐵軌,後面的汽車好像緊緊地粘在火車上,瀝青上有淺淺的水漥亂光閃耀。一個年輕人問能不能坐在他旁邊,奧斯卡剛好取出墨鏡,轉過身,把眼睛藏在深色的鏡片後。年輕人繼續往前走,折疊桌上的咖啡杯站在一汪褐色的水窪中。
奧斯卡常常覺得生活難以忍受,原因在於他對格調極其敏感。很多人不喜歡自己的同胞,但很少有人能像奧斯卡那樣說得清楚理由。他們都是由質子、中子和電子做成的,這他還勉強能原諒,他不能原諒的是,他們不能冷靜地看待這個可悲的事實。當他想起小時候的事情時,就看見十四歲的自己被一群嘻嘻哈哈的少男少女包圍著,他們都伸出手指指著他的腳。那時他沒有得到父母同意就把自行車賣了,用那筆錢買了他的第一雙滾邊皮鞋,出於謹慎,新鞋買大了三號。他至今依然蔑視毫無品味的哄笑,憎惡愚夫的妄自尊大、炫耀自誇和幸災樂禍。依他看來,再沒有比扼殺高尚格調更殘酷的暴行了。如果他什麼時候要殺人的話(完全是計畫外的),那恐怕就是因為他的受害人喋喋不休地評頭論足,太討人嫌了。
當他在十六歲那年身高達到一米九的時候,同學們的嘲笑戛然而止,他們轉而開始爭相吸引他的注意力。只要他在附近,他們的說話嗓門就特別大;女孩在課堂上舉手發言時也會向他這邊張望,好像是想看看他是不是也在聽;甚至數學老師,一個不修邊幅的人,脖子裡的頭髮總是直刺衣領,當他在一列數字後面打上一個能把粉筆折斷的點的時候,也習慣於朝著奧斯卡所在的方向問道:「是這樣吧?」儘管如此,到中學畢業的時候,奧斯卡依然是全班唯一一個沒有積累任何實際博愛經驗的人。他把這看作是勝利,他相信,全世界沒有一個人的在場能讓他忍受十分鐘以上。
當他在大學裡遇見薩巴斯提昂時,這個巨大的認識性錯誤令他頭暈目眩。在新學期開學那天他們就注意到了對方,這要歸功於他們的身高。他們的目光越過其他學生的腦袋彼此相遇,在教室裡他們自然而然地坐在了一起,默默地忍受了系主任那刑訊式的致辭。然後他們在走道上開始了一場輕鬆的談話,十分鐘過去了,薩巴斯提昂還沒有說過任何傻話,也沒有傻笑過一次,奧斯卡不僅忍受了他的在場,還覺得很有興致將談話進行下去。他們走進一家咖啡館,一直聊到黃昏。從這一刻起,奧斯卡就努力接近這個剛認識的人,而薩巴斯提昂也無不樂從。他們的友誼不需要啟動時間,毋須進展,它就像一盞燈,只要有人正確地擰動了開關,它自然就亮起來了。
接下來的幾個月,任何人如果想要描述的話,都難免面臨失之偉大的危險。自從奧斯卡決定在弗萊堡攻讀大學學業後,他就再也不穿著別的衣服在公眾中露面了,而只穿長擺燕尾服和條紋褲子,配以銀色領帶。過沒多久,薩巴斯提昂也穿著同樣的時髦行頭來上課了。每天早晨,在物理學院門前的綠地上,他們倆好像被繩子牽著一樣,經過同學期的所有學生身邊——這些學生只是為了擋他們的道才存在於世界上的——迎著對方走去,然後擊掌致意。每種教材他們都只買一本,因為他們喜歡在打開的書本上把腦袋湊在一起共讀一頁。在教室裡,他們身旁的位置總是空著。別人覺得他們打扮得古怪,但沒人笑話他們。下午,他們手挽手在三人河邊散步,走幾步就會停下來,因為重要的話只能站住後才能說,即便在這時,也沒人笑話他們。他們的老式裝束使他們看上去像泛了黃的明信片,好像他們是被人在現代的時代中雕刻出來的,雖然刻得很仔細,但並非天衣無縫。三人河裡的水聲起勁地摻和他們的談話,風中的樹激動地揮手致意,晚夏的陽光從來不像此刻這麼美麗。他們中的一個手指太陽,說著與太陽中的微子有關的話題。
晚上,他們相會在圖書館。奧斯卡沿著書架徜徉,不時地帶著一本書回到他們共用的桌旁,當奧斯卡把書上某個有趣的地方指給朋友看的時候,他習慣於用胳臂繞著他,自此以後,德語語言文學專業的女大學生們就聚坐在閱覽室玻璃窗後面的長凳上。在舞會上,奧斯卡和薩巴斯提昂各自穿梭在人群中,薩巴斯提昂很可能笨嘴拙舌地去親吻一個女孩,等他抬起頭,他肯定可以與房間另一頭奧斯卡那笑盈盈的目光相遇。晚會結束時,這個女孩被送到出口處,像件衣服似的被交給隨便哪個同學。然後,在夜色中,奧斯卡和薩巴斯提昂相伴回家,一直把對方送到他們的歸途分岔的地方。他們站在那兒,路燈的燈光像一頂帳篷似的包圍著他們,誰也不願意離開這個帳篷。他們面臨著一個艱難的抉擇,不知道在哪個時刻告別比較合適,是此刻呢,還是下一刻?過路的汽車使他們共同的身影繞軸自轉,這時他們默默地發誓,在他們之間什麼也不可以改變,永遠!未來只不過是在他們兩人共同的道路上緩慢鋪展的勻整地毯。在鳥兒初起的嘰喳聲裡,他們轉身消失在自己的那一半曙光中。
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五,奧斯卡允許自己暢想幾秒鐘,城際列車把他帶回到弗萊堡路燈下的某次告別場景,讓他想起三人河邊的激烈爭論,或者至少想起一本兩人共閱的翻開的教科書,然後他品嘗到了自己嘴唇上的微笑,僅僅是為了在下一刻陷入激動的情緒。夜間路燈下的弗萊堡當然已經不存在了。瑞士下方有一條環形的隧道,奧斯卡讓基本粒子在這條隧道中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相互碰撞,另外還有一個弗萊堡,那是他受薩巴斯提昂妻子的邀請去參加家庭聚餐的地方。某個星期五,奧斯卡第一次看見了洋娃娃大小的里昂,在另一個星期五,他獲悉了薩巴斯提昂對大學的呼籲。在星期五,他們看著對方的眼睛,努力不去想起昔日的時光;在星期五,他們吵架。對奧斯卡來說,薩巴斯提昂不僅是唯一一個他能愉快地忍受其存在的人,而且也是個輕輕一動就能惹他發火的傢伙。
* * *
薩巴斯提昂生活中的轉捩點要歸功於一個人,享有這份可疑榮譽的人名叫「小紅帽」。這個綽號源自他那因喝酒而發紅的腦殼,那上面頂著一個破損露線的頭髮花環,他常年穿著一件已經磨平了的燈芯絨上衣,肩上總是覆蓋著一層白色的頭皮屑。與許多同事不同的是,小紅帽很受學生歡迎,他對待他們很認真,用刁鑽複雜的難題挑戰他們的聰明才智。但這種好感不是雙向的,小紅帽尤其不喜歡那些能經得起高標準嚴格要求的學生。
他最不喜歡的就是那兩個每天早晨堵著教室大門的年輕男人。他們的狂妄早成了傳奇,他們的友誼已成了流言蜚語,甚至在教授們的過道裡都能聽到。據說,他們愛物理比愛對方更甚,為了物理,他們以競爭對手的激情爭吵不休。小紅帽不能忍受他們自吹自擂的高談闊論,他們在一群聽眾中間站得過於筆直,朗誦公式就像朗誦歌劇劇本的詩句,用樂團指揮式的雙手整頓宇宙,奧斯卡偶然轉過腦袋抽一口他的埃及菸,他的裝腔作勢足以使他的聽眾陷入一陣不安的騷動。
整個物理系早就知道,奧斯卡把世界看成是因果關係的精密織物,人只有與之保持最遠或最近的距離才能破譯隱藏其中的圖案。他認為,「認知」就是正確選擇距離的問題,所以只有上帝和量子物理學家可以暢通無阻,而普通人只會固執地與物體保持中等距離,所以什麼也看不見。
辯論的時候,薩巴斯提昂總是嗓門大些,反應慢些,他罵他的朋友是可恥的決定論者,他自稱不信因果論,他說因果論就像時間和空間,首先是個認識論的問題。為了氣氣奧斯卡和圍觀的人,他對於以經驗作為認識方法的有效性表示懷疑,一個人站在河岸上看見一千隻白天鵝從眼前游過,不能因此就得出結論說,世界上不存在黑天鵝,所以物理首先得是哲學的僕人。
小紅帽不耐煩地從吵架的人身邊擠過去,他沒有一堂課不聽見他們那討人嫌的竊竊私語聲,有時在他低頭看資料的時候,他覺得他們的低聲會議要把他逼瘋了,等他惱怒地抬起頭來,卻發現奧斯卡和薩巴斯提昂根本沒來上課。
但是有一天他們絕對來上課了。那天小紅帽給學生們一道關於黑暗能量的題目,這道題只有透過引入一個並不恆定的愛因斯坦常數才能解決。下個星期他們沒有堵在教室門口,而是早早地在習慣的位置上坐好,充滿期待地看著小紅帽,而小紅帽還沒走到講臺就用手指指他們。他們一齊起立,奧斯卡走到黑板的右端,薩巴斯提昂略一猶豫後,走到黑板的左端,他們把長襬衣服搭在肩上,用一隻手拉住,而另一隻手越過擋板去搶粉筆,然後他們開始瘋了似的狂寫,奧斯卡從後往前寫,薩巴斯提昂從前往後寫。粉筆伴隨著公式的增長發出刺耳的聲音,除此之外,教室裡什麼聲音也沒有,即便當他們的手在最下面一行的中間碰到一起時,還是很安靜。觀眾中有些面孔在傳播微笑。奧斯卡寫完最後一個「λ」後,用鼓掌的動作拍掉了手上的粉筆灰。其間小紅帽站在他們身後,半張著嘴看著那條公式長廊,好像一個徒步旅行者在驚歎令人目眩的美景。奧斯卡轉身用瘦削的手指輕叩他的肩膀,好像把他當成了三角鐵,想用他奏樂。
「您知不知道剛才我們證明了什麼,教授?」
他的聲音飽滿而響亮,小紅帽出神過甚,無法回答。
「物理屬於相愛的人。」
即便小紅帽對此說了些什麼,他的話也湮沒在哄堂大笑和喧鬧聲中了,薩巴斯提昂手指之間粉筆折斷的聲音同樣也沒人聽見。當奧斯卡在為成功的傑作接受祝賀的時候,薩巴斯提昂還是站在黑板前,滿臉沉思的表情,最後他穿上衣服,離開了教室,而他的朋友並沒有注意到他這個舉動。令他感到震驚的是奧斯卡那理所當然的神情,奧斯卡帶著這樣的神情走向黑板的右端,卻把左端分配給他。
即便知道奧斯卡絕非有意要讓自己相形見絀,薩巴斯提昂的處境也並不因此就輕鬆些,在愚蠢的屈辱感之外,他自己的不公也刺痛了他的心。奧斯卡要的只是轟動效應,他陶醉於他們共同的表演,而薩巴斯提昂更想成為一個優秀的物理學家,這個願望千金不換。對於奧斯卡來說,「有理」不是一個努力的目標,而是他的一個自然狀態。他謙虛地認為,薩巴斯提昂沒有他那樣的能力,不能從後往前推導公式,而糟糕的是,這個估計正與事實相符。薩巴斯提昂覺得迫切需要懲罰奧斯卡,因為他們的手在黑板正中間相碰的那一秒變成了單方面勝利的時刻。友誼的歡慶和共同的光輝,那只是對奧斯卡而言,但對薩巴斯提昂而言,這是身處劣勢的明證。
從那時候起,在與奧斯卡在一起的時候,薩巴斯提昂總是冷若冰霜,他無法向他的朋友作出解釋,為什麼他們的友誼法則突然之間全失效了。薩巴斯提昂的論辯越來越尖刻,他為一起研究騰出的時間越來越少,奧斯卡並不為自己辯護,在半閉的眼皮下,他的目光沉靜而深邃,直望到薩巴斯提昂的睡夢之中。朋友不肯對新的攻擊作出自衛,這只能讓薩巴斯提昂更加強硬,他在奧斯卡的宿舍裡大罵狹隘的四壁和狹隘的宇宙觀,直至有一天晚上,奧斯卡冷冷地輕聲稱他為「沒格調的人」。那一夜,薩巴斯提昂獨自跑遍了大街小巷,在路燈的杆子上砸青了拳頭,他對路燈說,這個世界有些地方不太對勁,肯定還存在別的宇宙,在那兒一切都不一樣,在那兒,一個像他這麼博學多才的人不可能這麼倒楣,在那兒,他和奧斯卡永遠不會失去對方。
到為博士論文答辯的時候,他們已經很久沒有在三人河邊相會了,充其量只是偶爾坐在酒吧的破椅子上一起喝一杯蘇格蘭威士忌。在任何方面他們都再也沒有任何共識了,除了一個問題:作為物理學家他們倆誰更優秀?是奧斯卡。奧斯卡的博士論文獲得的「最高獎勵」為這一個共識蓋上了封印,自此薩巴斯提昂脫下了他的燕尾服,換上了襯衫和牛仔褲,然後結婚了。
在婚禮上,賓客們都用手掩著嘴悄悄談論證婚人,他沿著喜堂的牆壁躡手躡腳地溜達,用他那黑色的身形親自負責產生角落裡的影子,他的神情顯示他現在的消遣比這輩子任何時候都愉快。他告訴那些尷尬的賓客們,薩巴斯提昂不該給他的新娘戴上婚紗,而應該戴上一具綠色標示燈,這對「緊急出口」是最合適的。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物理屬於相愛的人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81 |
小說/文學 |
$ 290 |
中文書 |
$ 290 |
英美文學 |
$ 297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物理屬於相愛的人
第一章 薩巴斯提昂在紙上剪曲線。美可做飯。奧斯卡登門拜訪。物理屬於相愛的人。如果要薩巴斯提昂描述他的朋友,他會說,奧斯卡看上去就像那種什麼問題都能回答的人:弦理論是否有朝一日能夠成功統一物理基本力量,燕尾服的襯衫是否能與無燕尾的禮服配穿,眼下幾點了,而且是杜拜時間。不論是傾聽的時候,還是自己說話的時候,他那雙花崗石似的眼睛總是一眨不眨地盯著對方。奧斯卡是這麼一個人:他的血管裡流的是水銀,他的腳下永遠有一座統帥土坡,他沒有幼稚可笑的暱稱。有他在場,女人就會坐在自己的手上,以免不小心向他伸出手去。他...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尤麗.策 譯者: 唐薇
- 出版社: 究竟出版 出版日期:2009-01-22 ISBN/ISSN:9789861371078
-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