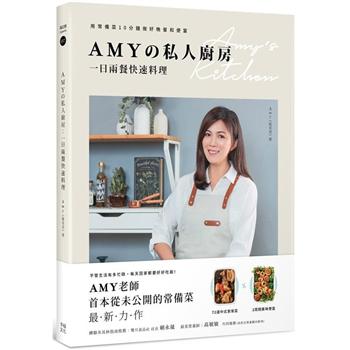推薦文一
周聯華 牧師
《耶路撒冷三千年》是多麼美麗又吸引人的書名;她是全世界人士所景仰的城市,她不是紐約、倫敦、巴黎,當然更非台北所能比擬;她之所以為人所景仰,因為她是全世界三大宗教的搖籃。
我上一次去耶路撒冷時,沿途看到旗幟上印著「慶祝大衛之城」的標誌。這對猶太人是沒有問題的,大衛是猶太人所尊敬的祖先,大衛出生在公元前1010-970;如此算來,耶路撒冷到現在剛好是三千年。但在巴勒斯坦的另一些居民卻不是這麼想的,好比那一次我來到巴勒斯坦時,與當時巴勒斯坦的領袖阿拉法特有過短短的會面,他很清楚地表達另外一種想法,而我不能不把他的想法考慮進去,因為他也代表了當地的另一群人。他告訴我:「這不是大衛之城,這是麥基洗德的城(見本書p50)。」他還向我提出挑戰,要我再去讀聖經,並告訴我:「亞伯拉罕所擁有的土地僅是他花了四百舍客勒所埋葬他妻子的墳地。」當然,以色列人不是這麼想的。當天晚上,我回到我下榻的住所閱讀聖經,果真這段經文記載在創世記第二十三章第七至十六節。
還有一次,我參加一個在耶路撒冷的學術會議,雖然人微言輕,仍主張耶路撒冷不要參加任何政治協商。我的想法是,既然她是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搖籃,那麼就由三個宗教共同負責經濟來維持一切的開支。這三大宗教都非常有錢,只要它們肯合作,財源是最小的問題,可惜沒有成功。
我希望藉著本書能喚起一般讀者對耶路撒冷的興趣。因為本書對歷史的考證有特殊的貢獻,藉著閱讀本書對耶路撒冷有深刻的了解;無論是學者、歷史家,和一般信徒都應該對耶路撒冷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推薦文二
吳獻章博士(中華福音神學院舊約教授)
這本書幫地球上最令人癡迷並迷惑的城市寫傳!
看官您或許會問:傳記,不是敘述人用的文體嗎?給一座城市寫傳?一個缺乏水源、充斥岩石、崎嶇難行、夏烈冬寒、交通遠離地中海沿岸商路?套用白居易的話:「耶路撒冷居,大不易!」何況這城市四周圍是乾癟的骸骨,「藏骸所」不論如何修飾,都掩埋不去歷世這城所經歷的屠殺、災難、破壞、戰爭、恐怖;從聖殿平台往上看橄欖山,墓園滿布,彷彿一座「死人城市」,連看一眼都嫌嘔,還幫她寫傳?
更讓看官迷惑的是,這飽經滄桑的城市,人間許多帝王為此城而動刀,她還是基督教、猶太教與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的故鄉,是文明衝突的戰略要衝,是無神論與信仰齟齬的前線,也是全球鎂光燈聚焦的舞臺,更是當今世界政治上牽一髮動全身的城市──它是九一一戰爭背後的爆炸導火線,中古世紀綿延數百年的十字軍也是為她開打!為這樣的城市寫傳?怎能不讓人如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訝異道:這耶京是「何方神聖」?怎會是讓世人魂牽夢繫的去處,讓亡國後的猶太人朝思夕夢,「明年耶路撒冷見」?
歷史和聖城的石頭會說話。誠摯地邀請您,透過本書細膩嚴謹深遠流長的刻畫,坐上這彷彿魂遊人間歷史的「萬花筒時間船」,凝視三千多年來這原本稱為「和平」的聖城,看舊約人物如大衛、所羅門、希西家、約西亞、尼希米相繼在此登上這座神聖城市,歷代梟雄如尼布甲尼撒王、大利烏王、亞歷山大大帝、龐培、安東尼等,如何用火和劍在此遍體麟傷的城市上耀武揚威,還有馬加比「鐵鎚」家族如何興起,新約人物如希律家族見證君王在宮廷中的腐敗,聖城和馬薩達如何亡於羅馬帝國的刀光火影下,以及兩千年來的基督教、伊斯蘭教、十字軍、鄂圖曼帝國、錫安運動乃至以阿衝突,如何相繼在這上帝聖殿所在的耶路撒冷登場……看官您就會覺得值回書價,且更能瞭解兩千年前,進入這聖城的耶穌,在橄欖山俯瞰這飽經創傷的城市,真情流露出的千年之嘆:
「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裡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新約聖經馬太福音二十三章37-39節)
《耶路撒冷三千年》見證了:
1.人類無可救藥的罪行:離棄上帝的瑪拿西王就在這城活活地燒死自己的孩子(列王紀下二十一章6節),聖殿南邊的欣嫩谷見證人心黑暗如「地獄」;連指責這城為妓女之城的先知以賽亞(賽一21),自己都在這城之聖殿,看見至高者顯現後,不禁冒出人間政治和宗教領袖必須反省的呼籲:「禍哉,我滅亡了!」(賽六5);
2.上帝的公義和聖潔:以色列和猶大相繼被擄亞述帝國和巴比倫帝國,因為不肯垂聽上帝透過先知們的警惕,繼續不斷地與立約的上帝「背約、撕票」。舊約歷史見證了,以色列淪亡原因並非因為「他殺」,而是得罪公義聖潔的上帝──「自殺」導致「他殺」──正如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的名言:Civilizations die from suicide, not by murder. (Study of History;《歷史研究》)。難怪先知耶利米就曾以擬人化口吻來為這聖城哭泣(耶利米哀歌);
3.上帝的救贖和慈愛:不論人間君王臣宰如何叫囂、抵擋,上帝預告在祂的聖山所設立的君王(詩篇二篇),已在「神人相會之城」應驗了。彌賽亞耶穌在這聖城旁的伯利恆降生,在有「以色列之地的靈魂」之稱的聖城,他講道、行神蹟,潔淨聖殿,吩咐死人從墳墓中走出,且為世人的罪,走上這錫安城冰冷的石板路,最後被粗暴地掛在城外的十字架上,死後就在此被埋葬,第三天且從墳墓中復活,也在這大君京城的橄欖山升天……讓最先遇見這城城主麥基洗德的亞伯拉罕(創世記十四章),都歡歡喜喜的仰望、期待(約翰福音八章56節)。因著耶穌,會死、必死的世人從此有路可走,並可親身經歷老子和莊子所期待的「天人合一、以馬內利」。
閱讀這本從耶路撒冷所濃縮出的世界編年史,您可以從這最令人迷茫之城中發現最真實的面貌,看清了上帝最終極心意:「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三章16節)
推薦文三
陳南州(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 鳳信教會牧師)
《耶路撒冷三千年》這本書不只是耶路撒冷這座位於世界歷史中心之城市的歷史。它敘述耶路撒冷猶太人、基督徒、穆斯林的故事;也透露屬世的權勢、武力、財富、虛榮,和屬靈的奧秘、敬虔相互交錯會合的悲慘故事,也就是人民苦難的歷史。它再一次震撼我的心靈,讓我憶起2005年,我在當今世界最大的基督教組織--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假希臘雅典召開的「宣教與傳道世界研討會」(World Conference on Mission and Evangelism)中認識的幾位巴勒斯坦基督徒的叮嚀。他們當中有一位送我一枝用以色列政府建造隔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圍牆時,所剷除的樹木製成的小十字架,他要我紀念被阻隔在耶路撒冷城外之基督徒的苦難。耶路撒冷城的興衰反映出苦難人民令人心疼的歷史。


 2018/08/08
2018/08/08 2014/11/11
2014/11/11 2014/09/01
2014/09/01 2013/07/21
2013/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