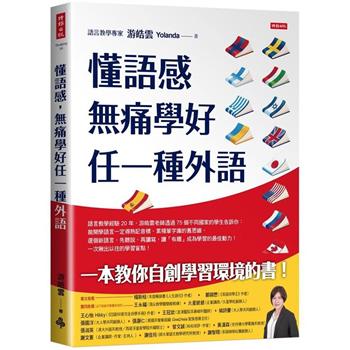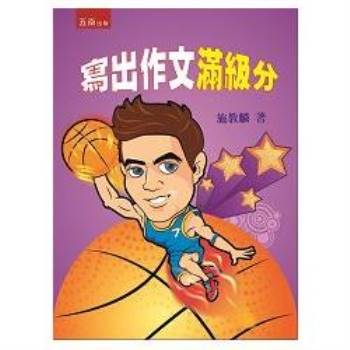「什麼叫命不該絕?難道我連死的權力也沒有嗎?」
奢侈豪華的辦公桌後,一個黑髮女子對著正坐在她面前的自稱是「牛頭」的男子大叫。
西裝革履的男子掏掏耳朵:「閻王叫你三更死,我們是不敢留人到五更的,反過來也一樣。」
「那我現在算怎麼回事?靈魂出竅?」
「鑒於你採用的是跳樓這種自殺方式,軀殼已經損壞,故而再想把你塞回去也是不可能了。」
「我才不要回去。」女子坐下,蹺起二郎腿,恢復一貫自在的神態,「我不要面對那一大堆貪婪勢利毫無人性的人。」
「安心,女,二十八歲,安氏財閥總裁安道宇的私生女。畢業於著名學府東大中文系,擅劍道,好圍棋。後在母逼迫下進入家族企業,確認為正式繼承人之際,戀人林霖被親戚所害,於是親手報仇後於安氏二十八樓頂層跳下。」
男子輕鬆地念完這一段,伸手一點,左牆上出現了一大串人名,宛如一個巨大的電腦螢幕。
他摸著下巴:「呃,讓我看看,有哪個是跟你同時同刻靈魂離體的。」
女子注意到他身前掛著一個鍍金牌子,蠻像現代的工作證,上面寫著「21」,便問道:「你們的穿著打扮怎麼這麼時髦?」
「與時俱進嘛!」牛頭先生盯著螢幕上不斷滾動的資料條,「有了!老七那兒有一個!」邊說邊按下了桌上一排標著數位的鍵。
「你想怎麼樣?」女子皺了皺眉,她一向不願任人擺布。
「讓你借屍還魂。」牛頭哈哈一笑,恰巧門被推開,進來一個人,她看了頓時瞪大眼。
此人一身古代裝束,廣袖寬袍。「廿一,你有完沒完?這個世紀的人這麼難搞嗎?」
牛頭滿臉堆笑:「哪有你那個時代那麼好?人類越進化心思越多了,害得我們的工作也越來越難做。」
「算了算了。」那人擺擺手,過來拉安心。
「你幹嘛?」她反手推開他。
「果然,女子都變得如此潑辣。」他皺皺好看的眉,再次拉住她時她便怎麼也掙不開了。
「你們到底要把我帶到哪兒去?」
「西元七世紀。」
床板好硬。這是她醒來後的第一個感覺。
門外傳來說話聲。
「這丫頭命還真大,扔到林子裡也餓不死,還被人救回來!」
「我說你啊——就這麼容不下她嗎?」男聲顯得無奈、悲哀。
「可以啊,」婦人嗓音尖銳,「你多賺點錢回來啊,我們才養得起這個賠錢貨!」
「要不,要不,讓大弟遲兩年再進書堂——」
「你這老不死的!自己窮了一輩子還不夠,還想拖累我們的兒子不成?你看看人家,凡是會認幾個字的,哪個不是謀了個好差使※整天就知道砍柴砍柴,官府老爺又拿走那麼多,家裡已經沒米下鍋了!」
男人被罵得消了聲。
隔了好一會兒,婦人又道:「這賠錢貨長得像個骷髏,賣了也沒人要。唉,我怎麼那麼命苦喲!」
喉嚨幹得要命,她試圖發出點聲音,卻徒勞無功。
這到底是哪裡?破爛的茅草房,小山似的柴火堆滿了半個屋子,自己躺的根本就不能稱之為「床」,只是一塊大木板,光禿禿的什麼也沒有。她撐手想坐起來,低頭一看,卻嚇了一跳。
這,這,自己的手幾時成了這般恐怖模樣?皮膚下面就只有骨頭,跟非洲難民裡那些瘦弱小的兒童有得一拼。目光慢慢轉向手臂、腿、身體……天!她變成了一個好小好小的女童,而且顯然還是那種過著悲慘生活、瀕臨死亡的女童!
是因為自己以前當安小姐的生活過得太舒服了,所以現在來個徹底大顛覆麼?她呆了半晌,緩緩無聲地笑開來:以這個身體的情況來看,大概不久又可以去牛頭先生那裡坐坐了。
命不該絕?好,那就看看,我到底是怎麼個命不該絕法!
一瞬間,她像看破了生死,想笑的同時,一滴眼淚卻自眼角慢慢流了下來。
從此以後,自己真的就是無親無故,無牽無掛了。
剛剛說話的兩人走了進來。
前面是個中年婦人,粗布裙,腰間圍了條圍裙。看她醒了,走上前來往她胳膊上重重擰了一把:「攤屍呢?還不給我幹活去!」
「孩子他娘,丫頭剛醒,還是先弄點東西給她吃吧。」一個滿臉皺紋、臉色黃黑的大叔從她背後冒了出來。
婦人對著他大叫:「不想活了是不是?還讓老娘給她弄吃的※」
「那,那我去。」大叔歉疚地朝安心笑笑,轉身就走。
「回來!」婦人上下瞟了安心一眼,懶懶道,「我去看看地裡還有沒有野菜,給她弄點粥吧。」又擰了她一把,才轉離去。
安心只覺被她擰得痛不欲生,可身上卻使不出半點力氣來反抗,只能恨恨地看著婦人離去的方向。
大叔待婦人走了,方慢慢蹭到她身邊坐下,只坐了個床角:「丫頭,不是阿爹不疼你,只是孩子他娘那脾氣,賦稅又重……阿爹實在是沒想到她會把你拋到野豬林裡要活活餓死你啊!你,你不怪阿爹吧?」
安心費力地抬手,指指喉嚨,「呵呵」幾聲。
大叔明白了,從窗臺上拿起一個破碗,出去盛了碗水回來,邊慢慢喂她喝,邊嘆氣:「你親娘死得早,要是她在,我也斷不會娶這惡婆娘。」
喉嚨舒服多了,她試著發聲:「阿爹?」
雖然嘶啞難聽,大叔卻高興地笑了:「你認我就好。」
「這附近有哪戶人家,或是官府,要招丫鬟的?」
三個月後。
「小安,今天是你第一次出府,記得按時回來,知道嗎?」淮陽府衙側門外,一個大丫鬟對著一個小小的身影仔細叮囑。
「嗯。」小人兒應聲。大丫鬟摸摸她的頭,想想還是不放心,「小竹那丫頭也是今天放假,還是讓她先送你回去吧。」
小女孩搖頭:「竹姐姐急著回家看她娘親的。我認得路,菊姐姐放心!」
「好吧。」大丫鬟終於放手,「常聽師爺說近來流寇日盛……幸好我們縣還算太平。去吧,去吧。」
安心,不,現在她已改名為安逝了,朝小菊揮揮手,總算脫得身來。
那日自她醒後,非常明白那個所謂的「家」肯定是待不下去的,於是要求「阿爹」帶她四處打探有沒有人家要丫鬟,不要工錢,只管吃住就行。豈知由於長期饑餓的緣故,那些總管掌事什麼的一見她面黃肌瘦骨瘦如柴的模樣便紛紛搖手。灰心喪氣之餘,卻巧遇此縣師爺,可能書生悲天憫人之心生來就盛,又驚見她居然能書會算,當即收了她做小書童,算是有了個安身之地。
想想那日「阿爹」見她突然開口念詩時張大嘴的表情,她不由撲哧一聲笑出來。師爺也曾問她小小年紀怎知這麼多?她笑說自己不久前在野豬林中瀕死之際遇到了仙人,得到仙人點化。也許古人比較迷信,她這麼說他們竟都信了。之後一陣,野豬林裡的香火漸盛。
她走走停停,沿路欣賞著二十一世紀所沒有的淳樸風景。
大片大片的水田,辛勤耕種的農夫,黃牛水牛哞哞叫,白髮垂髫悠然自樂。
縣府規定,新進府的丫鬟家丁每隔三個月可回家一趟。但她並不想回那個「家」,他們不歡迎她,她也不喜歡他們,除了懦弱的「阿爹」外。
「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途士,郁陶傷寸心——」她循聲望去。
不遠處有一座學堂,裡面十來個孩童在追逐嬉戲。堂外,一名青衣人對著田野徐徐念到:「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會,千古傳名諡。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吟罷淚流滿面。
她突然睜大眼,這個人,這個人難道竟是——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盛世唐朝之隋唐逝1:誤入亂世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盛世唐朝之隋唐逝1:誤入亂世
帶你進入擁有最多明星人物的時空,體驗最璀璨的穿越冒險!
他,風流瀟灑;
他,溫柔儒雅;
他,英姿勃發──
三個曠世英雄,到底誰才是她最終的歸宿?
------------------------------------
失去深愛之人的她,
因為再不願面對身邊那群貪婪勢利、毫無人性的人,
在復仇之後便選擇離這人世間……
然而引魂使者卻說她命不該絕,
硬是把她的靈魂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讓她借屍還魂到一個隋朝末年的古人身上,
好賦予她一個全新的人生──
天!她的新身分竟然是一個小女童,
而且似乎還是一個被虐待、過著悲慘生活的女童!?
什麼全新人生,根本就是嫌她還不夠慘嘛!
照眼前情況看來,還來不及遇到什麼英雄美人、談場跨時空戀愛,
她就會一命嗚呼了……
喔喔,左邊來了一個她的偶像歐陽詢,
右邊又來一個英姿勃發的李世民……
不行不行!好不容易來到這個朝代,
她的目標可是要識盡這些英雄人物,
說什麼也要想盡辦法活下去才行──
作者簡介:
青諍
九界網常駐作家。性別非男,24歲,現居深圳,從事外貿工作。學的是文科,進的卻是以理工為主的大學,沒什麼上進心,懶人一個。喜愛文學,喜歡音樂,喜好打RPG遊戲。總是會在無意中讀到某一段文字或看到某一幅畫面時突生感動,然後把它們寫下來,只是零碎居多,成文者少。還是一個字,懶。相信君子之交淡如水。相信雪中送炭永遠好過錦上添花。
章節試閱
「什麼叫命不該絕?難道我連死的權力也沒有嗎?」
奢侈豪華的辦公桌後,一個黑髮女子對著正坐在她面前的自稱是「牛頭」的男子大叫。
西裝革履的男子掏掏耳朵:「閻王叫你三更死,我們是不敢留人到五更的,反過來也一樣。」
「那我現在算怎麼回事?靈魂出竅?」
「鑒於你採用的是跳樓這種自殺方式,軀殼已經損壞,故而再想把你塞回去也是不可能了。」
「我才不要回去。」女子坐下,蹺起二郎腿,恢復一貫自在的神態,「我不要面對那一大堆貪婪勢利毫無人性的人。」
「安心,女,二十八歲,安氏財閥總裁安...
奢侈豪華的辦公桌後,一個黑髮女子對著正坐在她面前的自稱是「牛頭」的男子大叫。
西裝革履的男子掏掏耳朵:「閻王叫你三更死,我們是不敢留人到五更的,反過來也一樣。」
「那我現在算怎麼回事?靈魂出竅?」
「鑒於你採用的是跳樓這種自殺方式,軀殼已經損壞,故而再想把你塞回去也是不可能了。」
「我才不要回去。」女子坐下,蹺起二郎腿,恢復一貫自在的神態,「我不要面對那一大堆貪婪勢利毫無人性的人。」
「安心,女,二十八歲,安氏財閥總裁安...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青諍
- 出版社: 耕林 出版日期:2010-06-09 ISBN/ISSN:986139939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