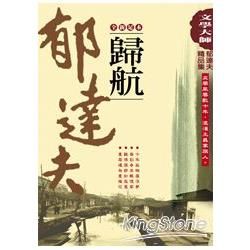※浪漫主義掌旗人!中國近代文學史上一個充滿濃厚浪漫主義色彩又帶有十足前衛風格的悲情文人;更是一個驚世駭俗、才華洋溢的作家。
※典藏重裝,全新編排!郁達夫經典代表作完美重現!
※大膽真實的自我剖析、奔放迷離的寫作手法及四十年早逝的青春,三段糾葛難解的婚姻,使郁達夫在中國近代文學的里程碑中,留下了他的一頁傳奇。
「藝術是天才的創造物,不可以規矩來衡量。」
—郁達夫
《歸航》——
「我這莫名其妙的離情,我這像將死時一樣的哀感,究竟教我如何處置呢?感傷的情懷,一時征服了我的全體,我覺得眼睛裡酸熱起來……」
遊子注定漂泊;才子注定寂寞。
對國家的期待,對自我的抱負,對現實的低頭,對人生的無常;
他選擇逃避還是反擊?
郁達夫文壇代表作。告訴你他的心情,他的想法,和他的苦悶。為了追求理想,他一度遠離家國,放逐日本。然而,不論如何漂泊,他的人生終將歸航。
書中並收錄他懷念徐志摩及魯迅的回憶文,真情流露,讓人動容。
郁達夫——
一個充滿濃厚浪漫主義色彩又帶有十足前衛風格的悲情文人;更是一個驚世駭俗、才華洋溢的作家。四十年早逝的青春,三段糾葛難解的婚姻,讓他留下了許多淒美且不同於一般世俗的作品。而他大膽真實的自我剖析、奔放迷離的寫作手法,亦造成一種孤獨的美感。使他在中國近代文學的里程碑中,擁有不可抹滅的地位。
【文學大師精品集】
進入文學殿堂 典藏大師精品
全新編排譯注 大師作品完美重現!
影響中國文壇的巨擘
魯迅、林語堂、郁達夫、徐志摩、蕭紅不朽傳世經典再次擁有
作者簡介
郁達夫(1896-1945)
原名郁文,字達夫,浙江富陽人。七歲入私塾。九歲便能賦詩。一九一一年起開始創作舊體詩,並向報刊投稿。一九一四年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後開始嘗試小說創作。一九二一年與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等人醞釀成立了新文學團體創造社。七月,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沉淪》問世,震撼當時文壇。一九二二年自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歸國。五月,主編的《創造》季刊創刊號出版。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間先後在北京大學、武昌師大、廣東大學任教。一九二八年加入太陽社,並在魯迅支持下,主編《大眾文藝》。一九三八年至新加坡,主編《星洲日報》等報刊副刊。一九四二年日軍進逼新加坡,逃至蘇門答臘。一九四五年突然失蹤,據傳被日軍憲兵殺害。《沉淪》、《銀灰色的死》、《春風沉醉的晚上》、《遲桂花》等皆為其著名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