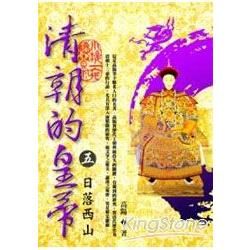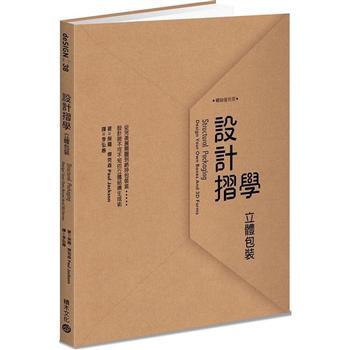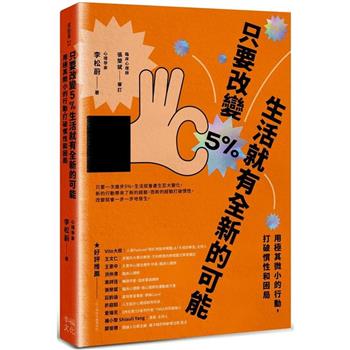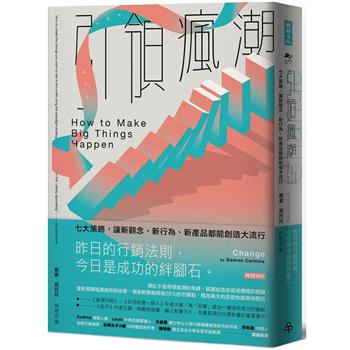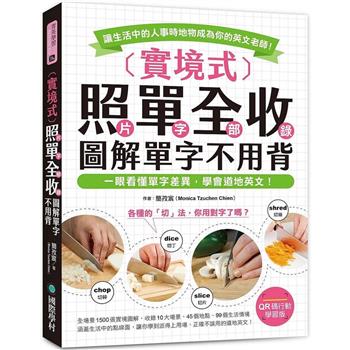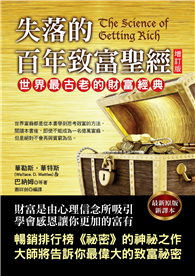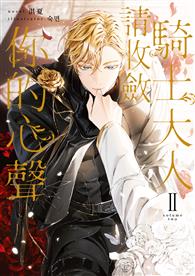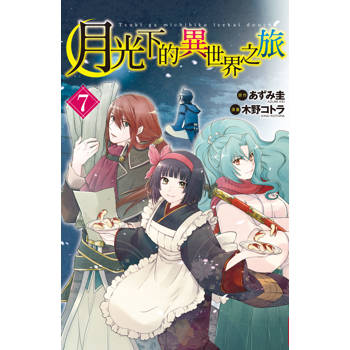※高陽多年研究的心血結晶。歷述大清帝國歷代諸位皇帝之行誼,深入剖析大清由盛轉衰的原因。
※內容鞭辟入裡,見解獨到,亦至情至性,堪稱高陽的代表巨著。
※是文人士子讀史之必備參考書,也是愛好歷史小說者不可不讀之作。
大清自入關至王朝結束,歷經二百多年,共十二位皇帝登基。從開國的努爾哈赤,到康雍乾的盛世,同治光緒的維新振作,再步入晚期的衰弱不振,都揭示了一國之興衰與帝位人選密不可分的關係。《清朝的皇帝》即高陽多年研究的心血結晶,歷述大清帝國歷代諸位皇帝之行誼,深入剖析大清由盛轉衰的原因。內容鞭辟入裡,見解獨到,亦至情至性,堪稱高陽的代表巨著。是文人士子讀史之必備參考書,也是愛好歷史小說者不可不讀之作。
◎清穆宗——同治(1856 ~ 1875)
是咸豐的獨子。其生母即為慈禧太后。在位十三年。六歲即位,因年幼,由兩宮太后「垂簾聽政」,至同治十二年方才親政,次年即病逝。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為當朝重臣。曾辦洋務新政,號稱「同治中興」。但實際權力仍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中,只能抑鬱以終。
◎清德宗——光緒(1871 ~ 1908)
是醇親王的兒子,慈禧的外甥,登基時只有四歲。至光緒十六歲,慈禧「歸政」,但仍實掌大權。期間發生甲午戰爭,戰敗後簽訂馬關條約。康有為曾數次上書要求改革。光緒二十四年下詔變法,但終招至慈禧太后為主的守舊派反對,德宗被幽禁,康梁逃亡日本,史稱「百日維新」。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起事,引發八國聯軍,北京被陷,之後簽下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創下不平等條約之最。最後被軟禁於瀛台,終飲恨病逝。在位三十四年。
作者簡介
高陽(1926-1992)。
本名許晏駢,浙江杭州人。曾任《中華日報》主編。1984年並獲中山文藝獎的文藝論著獎。擅寫歷史小說,也是著名的「紅學」專家。高陽的歷史小說,享譽當代文壇,其作品的最大特色便是「以歷史入小說,以小說述歷史」,從考據中探索歷史的真相,並將求證所獲的資料用於小說之中,使其作品更具深度與意義。因其作品流傳廣大,乃有「有井水處有金庸,有村鎮處有高陽」之說,高陽譽滿海峽兩岸,由此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