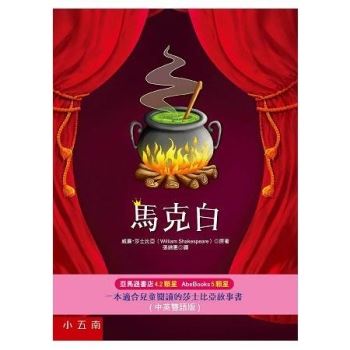※海明威成名代表作之一,美國現代小說史經典之作。
※美國最傑出的作家之一,195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海明威的小說經常出現戰爭、鬥牛、捕魚等題材,字裡行間更寫出他自己的經歷,充分表達了那一代年輕人失落、苦悶的心情。
※本書曾被拍成電影〈妾似朝陽又照君〉!
戰後一群青年浪跡歐洲,整日無所事事,任意放逐自我,因為戰爭的摧殘,讓他們厭惡戰爭,對公理、傳統價值觀產生懷疑,更對人生感到厭倦、迷惘和沮喪,只有藉由追求短暫的快樂刺激以麻痺身心的痛苦。遊戲人間的態度和一味追求享樂、借酒澆愁的生活方式,卻讓他們更加失落。海明威運用獨特的文字鋪陳出這群青年浪漫虛幻的生活情景以及他們精神世界的深刻變化。此書開創了海明威式的獨特文風,也是海明威的成名作與重要代表作之一。
作者簡介:
海明威,1899年7月21日誕生於美國伊利諾州的橡樹園,在六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父親為醫生,母親出身望族。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海明威應徵義大利軍的紅十字會救護車司機,腿部被迫擊砲碎片炸成重傷,住院期間結識一位女護士,兩人墜入愛河。這段戀情雖未能長久,海明威卻始終難以忘懷,日後他的著名小說《戰地春夢》,即以該名護士為女主角。二次大戰,海明威親身參與游擊隊的戰役,並以1936年參與西班牙內戰的經歷,寫成著名的《戰地鐘聲》。在海明威與第二任妻子寶琳居住西礁島時,其身分從美國最著名的作家搖身一變為美國最著名的漁夫。《老人與海》的故事便緣起於此,並於1954年以此書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海明威作品特色為:文字簡單,寓意深遠。不只風靡美國,也風靡全世界。與海明威同為廿世紀美國文學巨擘、也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福克納對他推崇備至,稱譽海明威的作品是「文學界的奇蹟」。晚年由於積勞成疾,數度入院接受電擊治療,於1961年7月2日凌晨,被發現死在自宅樓下的槍架前,一般認為係屬自殺。
章節試閱
「 你們都是失落的一代。」——引自異性知己、文學批評家格特露德‧斯坦茵的一次談話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大地卻永遠長存。太陽昇起,太陽落下,匆匆趕回原處,重新再昇。風吹向南,又轉向北,旋轉不息,循環周行。江河流入大海,大海總不滿溢。江河仍向所在之處,川流不息。」——聖經《傳道書》第一章四至七節
第一部
1
羅柏‧科恩一度是普林斯頓大學的中量級拳擊冠軍。不要以為一個拳擊冠軍的頭銜會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但當時對科恩而言卻是件了不起的事。他對拳擊一點也不愛好,實際上他很討厭拳擊,但他仍然痛苦而一絲不苟地學打拳,以此來抵消在普林斯頓大學被作為猶太人對待時所感到的自卑和羞怯的心情。雖然他很靦腆,是個十分厚道的年輕人,除了在健身房裡打拳,從來不跟人打架鬥毆,但是想到自己能夠把瞧不起他的任何一個人打倒在地,他就暗自得意。他是史班德‧凱利的得意門生。不管這些年輕人的體重是一百零五磅,還是二百零五磅,史班德‧凱利都把他們當作次羽量級拳擊手來教。不過這種方法似乎對科恩很適合。他的動作確實非常敏捷。他學得很好,史班德很快安排他跟強手交鋒,卻給他終生留下了一個扁平的鼻子。這件事增加了科恩對拳擊的反感,但卻給了他某種異樣的滿足,而且確實使他的鼻子反而變得好看些。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最後一年,讀書過多,開始戴眼鏡。我沒見過他班上的同學還有誰記得他的。他們甚至記不得他曾是中量級拳擊冠軍。
我對所有貌似坦率、單純的人向來不甚相信,尤其是當他們講的事沒有漏洞的時候,因此我始終懷疑羅柏‧科恩大概從來也沒當過中量級拳擊冠軍,或許有匹馬曾踩過他的臉,要不,也許他母親懷胎時受過驚嚇或者看見過什麼怪物,要不,也許他小時候曾撞在什麼東西上,不過他這段經歷終於有人從史班德‧凱利那裡為我得到證實。史班德‧凱利不僅記得科恩。他還常常想知道科恩後來怎麼樣了。
從父系來說,羅柏‧科恩出身於紐約一個非常富有的猶太家庭,從母系來說,又是一個古老世家的後裔。為了進普林斯頓大學,他在軍事學校補習過,是該校橄欖球隊裡非常出色的邊鋒,在那裡,沒人使他意識到自己的種族問題。進普林斯頓大學以前,從來沒人使他感到因為自己是一個猶太人,故而和其他人有所不同。他是個厚道的年輕人,是個和善的年輕人,非常靦腆,這使他很不開心。他在拳擊中發洩這種情緒,他帶著痛苦的自我感覺和扁平的鼻子離開普林斯頓大學,碰到第一個待他好的女孩就結了婚。他結婚五年,生了三個孩子,父親留給他的五萬美元幾乎揮霍殆盡,遺產的其餘部分歸了他母親。而由於和有錢的妻子過著不幸的家庭生活,他變得冷漠無情,使人討厭;正當他決心遺棄他妻子的時候,她卻先拋棄了他,跟一位袖珍人像畫家出走了。他已有好幾個月一直考慮著要離開他的妻子,只因為覺得使她失去他未免太過殘酷,所以沒有付諸實施,因此她的出走對他倒是一次非常有利的衝擊。
辦妥了離婚手續,羅柏‧科恩動身去西海岸。在加利福尼亞,他投身於文藝界,由於他那五萬美元還略有剩餘,所以不久就資助一家文藝評論雜誌。這家雜誌創刊於加州的卡默爾,停刊於麻薩諸塞州的普羅文斯敦。科恩起初純粹被看作一個後臺金主,他的名字給登在扉頁上只不過作為顧問之一,後來卻成為唯一的編輯了。雜誌出刊靠他的錢,他發現自己喜歡編輯的職權。當這家雜誌因開支太大,致使他不得不放棄這項事業時,他感到很惋惜。
不過那時候,另外有事要他來操心了。他已經被一位指望跟這家雜誌一起飛黃騰達的女士捏在手心裡了。她非常堅強有力,科恩始終沒法擺脫她的掌握。況且,他也確信自己在愛她。這女士發現雜誌已經一蹶不振時,就有點嫌棄科恩,心想還是趁還有東西可撈的時候撈他一把的好,所以她極力主張他倆到歐洲去,認為科恩在那裡可以從事寫作。他們到了她曾在那裡念過書的歐洲,待了三年。這三年期間的第一年,他們用來在各地旅行,後兩年住在巴黎,羅柏‧科恩結識了兩個朋友:布雷多和我。布雷多是他文藝界的朋友。我則是他打網球的夥伴。
這位掌握科恩的女士名叫法蘭西絲,在第二年末發現自己的姿色日見衰弛,就一反過去漫不經心地掌握並利用科恩的心態,斷然決定他必須娶她。在此期間,羅柏的母親給了他一筆生活費,每個月約三百美元。我相信在兩年半的時間裡,羅柏沒有注意過別的女人。他相當幸福,只不過和許多住在歐洲的美國人一樣,他總覺得還是住在美國好。他發現自己能寫點東西。他寫了一部小說,雖然寫得並不好,但也完全不像後來有些評論家所說的那麼糟。他博覽群書,玩橋牌,打網球,還到本地一個健身房去練拳。
我第一次注意到這位女士對科恩的態度,是在有一天晚上我們三人一塊兒吃完飯之後。我們先在大馬路飯店吃飯,然後到凡爾賽咖啡館喝咖啡。喝完咖啡,我們又喝了幾杯白蘭地,我說我該走了。科恩剛在談我們倆到什麼地方去從事一次週末旅行。他想離開城市,好好地去遠足一番。我建議坐飛機到斯特拉斯堡,從那裡步行到聖奧代爾或者阿爾薩斯地區的什麼別的地方。
「我在斯特拉斯堡有個熟識的女孩,她可以帶我們觀光那座城市,」我說。
有人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腳。我以為是無意中碰著的,所以接著往下說:「她在那裡已經住了兩年,凡是那城裡你想要瞭解的一切她都知道。她是位可愛的女郎。」
在桌子下面我又挨了一腳,我一看,只見法蘭西絲,就是羅柏的情人,正撅著下巴,板著面孔呢。
「去他的,」我說,「為什麼到斯特拉斯堡去呢?我們可以朝北到布魯日或者阿登森林去嘛。」
科恩好像放心了。我再也沒有再挨踢。我向他們說了聲晚安就往外走。科恩說他要陪我到大街拐角去買份報紙。「上帝保佑,」他說,「你提斯特拉斯堡那位女郎幹啥啊?你沒看見法蘭西絲的臉色?」
「沒有,我哪裡知道?我認識一個住在斯特拉斯堡的美國女郎,這究竟關法蘭西絲什麼事?」
「反正一樣。不管是哪個女郎。總而言之,我不能去。」
「別傻了。」
「你不瞭解法蘭西絲。不管是哪個女郎。你沒看見她那副臉色嗎?」
「好啦,」我說,「那我們去森利斯吧。」
「別生氣。」
「我不生氣。森利斯是個好地方,我們可以住在麋鹿大飯店,到樹林裡遠足一次,然後回家。」
「好,那很有意思。」
「好,明天網球場上見,」我說。
「晚安,傑克,」他說著,回頭朝咖啡館走去。
「你忘記買報紙了,」我說。
「真的。」他陪我走到大街拐角的報亭。「你真的不生氣,傑克?」他手裡拿著報紙轉身問。
「不,我幹嘛生氣呢?」
「網球場上見,」他說。我看著他手裡拿著報紙走回咖啡館。我挺喜歡他,法蘭西絲顯然弄得他的日子很不好過。
「 你們都是失落的一代。」——引自異性知己、文學批評家格特露德‧斯坦茵的一次談話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大地卻永遠長存。太陽昇起,太陽落下,匆匆趕回原處,重新再昇。風吹向南,又轉向北,旋轉不息,循環周行。江河流入大海,大海總不滿溢。江河仍向所在之處,川流不息。」——聖經《傳道書》第一章四至七節
第一部
1
羅柏‧科恩一度是普林斯頓大學的中量級拳擊冠軍。不要以為一個拳擊冠軍的頭銜會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但當時對科恩而言卻是件了不起的事。他對拳擊一點也不愛好,實際上他很討厭拳擊,但他仍然痛苦而一絲不苟地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