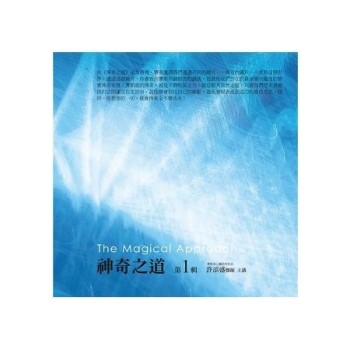一樣的鄉野,不一樣的傳奇!
《狼煙》是我童年期真實存活的世界,這世界,是萬千陷區同胞共同存活、並共同感受的。這部書的題材,在我內心足足孕育了十年之久,從時空背景上看,它發生在抗戰期間的淮河流域,正好是《狂風沙》那一時代的延續……
—司馬中原
國遭大難,整塊天都塌了下來,
陷區裡的老民難免要應劫受苦,
即使投奔到蒿蘆集,得著一時的粗安,
誰又能料得定日後會遭到什麼樣的劫數?
《狼煙》一書,是司馬中原突破性的文學鉅著,深受各方矚目。銳筆縱橫文壇的司馬中原,以抗日剿匪兩大時代為背景,使用色彩濃烈的筆觸,悲天憫人的情懷,鮮活的呈現出一頁英烈悲壯的時代事蹟。
《狼煙》所展現的時代和人物,都曾為作者親身所經歷,經過他的透視和體察,掌握了人性的神髓,更融合了作者的生命情感,鑄成了這部鉅著的時代性、生活性和高度的藝術性,在陰鬱中迸射出灼亮的、人性的火花。
作者簡介
司馬中原
本名吳延玫,江蘇省淮陰市人。他的作品曾多次榮獲臺灣各種文藝獎項,有第一屆青年文藝獎,1967年度教育部文學獎、1971年度十大傑出青年金手獎、第二屆聯合報小說獎的特別貢獻獎等。其作品內容包羅萬象,除以抗日戰爭為主的現代文學;以個人經歷為主的自傳式作品外,更有以鄉野傳奇為主的長篇小說,最為受到讀者歡迎。近年則以靈異的鬼怪故事受到年輕讀者的喜愛,其代表作有:《狂風沙》、《荒原》、《青春行》、《煙雲》等。
◎司馬中原得獎紀錄
1960 第一屆青年文藝獎
1966 教育部文藝獎
1971 十大傑出青年金手獎
1978 十大榮民(首屆)獎
1980 聯合報小說特別貢獻獎
2010 獲世界文化藝術學院頒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