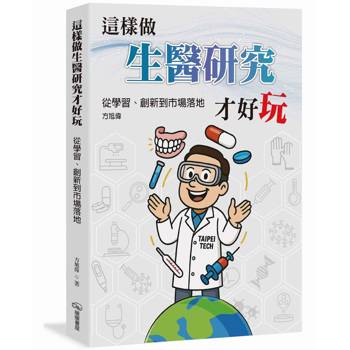第二章 共同基金的開拓者
約翰‧伯格(John Bogle)在共同基金行業的第一位雇主是華特‧摩根(Walter L‧Morgan),他在1920年代建立了威靈頓機構(Wellington organization),並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這個機構是先鋒的前身。1967年,摩根在威靈頓管理公司主席的身份,以及三年後以威靈頓基金(Wellington Fund)主席的身份離職,他是共同基金行業內任職時間最長的主管之一,以及美國公司(U.S.Corporation)任職時間最長的主席之一。直到1998年9月他100歲時去世,他都堅持每週到位於瑪文的先鋒園區,在為紀念他而重新命名為Morgan Building的大樓內工作兩天。同共基金行業的先驅裡面,唯一一個比他活的時間長的是Philip L.Carret,他在1928年創立了先鋒基金(Pioneer Fund);於101歲去世,也是1998年。
第三章 「他比我們更瞭解基金行業」
經營股票基金對發起者和股票持有者都是有利可圖的,得到這項結論後,摩根感謝了伯格,後者不辭辛勞分秒必爭的為惠靈頓股票基金起草了創辦計畫書。(伯格和摩根在為他們的新基金取名時,其想像力並不比他們的競爭者MIT高明多少,後來該基金於1963年更名為溫莎基金(Windsor Fund))。1958年,伯格的建議將公司帶上那時認為的革命性道路時,雖然摩根將這個基金專案交給一個革命性不強的團隊來管理,並指出該基金專案的目的只在於為那些認為自己有充足的固定收益投資的投資者,提供一個受到的管理的普通股票計畫,但他也承認改變是必須的。
對伯格在威靈頓管理公司的職業生涯來說,新型基金的創立是一個轉捩點。他另闢蹊徑並取得成功。為此,摩根對其他人說,伯格在成為公司領導人的道路上正平步青雲。再者做為一位基金管理者,新型基金的誕生使伯格獲得他的第一個頭銜:威靈頓股票基金秘書。這一頭銜隨之而來的是一些繁雜的俗務,例如:忙錄,應酬,照相等等。由此可見,領導一次變革所得的並不只是榮譽和光環。
第四章 如天堂般的婚禮
1958年新增的威靈頓股票基金並沒有將公司的帳本底線提高多少。雖然最初三年新型基金表現不錯,但是在1962年它遇到了災難,市值下跌了四分之一。那時威靈頓股票基金遇到了一些情緒性問題,基金以威靈頓的名義籌集資金,有些股東抱怨這樣做不公平,他們堅持認為只有威靈頓基金才對股票基金的名字擁有所有權。1963年在威靈頓股票基金同意更名為溫莎基金(Windsor Fund)之後,這件事才告一段落。1964年6月,約翰‧奈夫(John B. Neff)接任了證券投資經理一職,他在這個職位上打拼三十二年直到退休,並與彼得‧林區(Peter Lynch),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一同獲得了投資業領袖的殊榮。
雖然在威靈頓管理公司管理之下的資產於1965年超過了20億美元,可是1965年到1966年間它的基金股票銷售額卻一度下滑。為了扭轉這個情形,公司的投資經理換了一個又一個,投資表現依然停滯不前,基金股票的購買量一直下滑,股票償清能力持續高危。伯格認為公司需要引進新東西來擴大資產,他對此早已深思熟慮。當時高收益型基金(go-go從事投機的投資公司)基金已經主導了這個行業,市場佔有率也從1955年的21%增至1964年的40% 和1966年的64%。但是伯格知道在公司內部培植一個成長型基金(performance fund)並不容易,創建溫莎基金的經歷正好證明這個論點。
企業兼併的前景使伯格格外興奮。兼併可以為威靈頓提供急缺的資源——投資管理才能。在使公司突破傳統習慣的同時,兼併還可以增加銷售額,使公司迅速扭轉頹勢;甚至有可能使公司突破共同基金行業,使威靈頓管理公司進軍機構投資顧問業務。至今伯格仍認為這個觀點是日久彌新。「如果你又笨又沒有耐心」他說,聲音裡有幾分無奈,「你會說:『讓我們兼併吧!我們將立刻解決所有問題。它會是一次在天堂上舉辦的婚禮。』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簡單。從本質上來看,兼併總會對一方或另一方造成傷害。」實際上,在接下來的歲月裡,伯格最喜歡的頌詞是:「成長是贏得的,不是買來的。」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共同基金投資新思維:約翰‧伯格與先鋒基金的再造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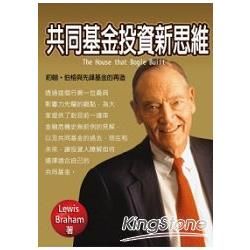 |
共同基金投資新思維:約翰‧伯格與先鋒基金的再造 作者:Lewis Braham / 譯者:邵超武、朱健樺 出版社:大億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5-3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77 |
中文書 |
$ 278 |
基金/債券 |
$ 292 |
債券基金 |
$ 333 |
基金債券/ETF |
$ 333 |
債券/基金 |
$ 333 |
財經企管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共同基金投資新思維:約翰‧伯格與先鋒基金的再造
面對接連不斷的金融危機和醜聞,透過這個行業一位最具影響力先驅的觀點,為大家提供了對當代金融史一項史無前例的見解,讓投資人瞭解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共同基金,以及共同基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共同基金投資新思維》是1975年創立了先鋒集團的約翰‧伯格的故事,以及他對未來投資的看法。它特寫了伯格打破舊習的本性和保持低成本,將投資者利益作為他的首要任務的目標——這和經營共同基金的其他人是完全相反;他們貪婪,想得到更高的利潤和管理費用。伯格很快獲得了行業「良心」的譽,幫助同行從事改革,並因此受到尊敬。
《共同基金投資新思維》揭示了投資世界裡最迷人,最複雜的形象。股東民主的一位頑強支持者,在先鋒集團,他自稱是一位「獨裁者」、一位傑出的數學家,但他對人比對數字更感興趣。嚴酷競爭,為推動同行改革,他費盡心力。儘管如此,相對於其他事物,伯格總是將客戶的利益擺首位——這項做法在他的事業中彌足珍貴。
以從未發表過的研究和對伯格本人的採訪為特色,《共同基金投資新思維》涉及伯格對先鋒,對他的繼任者傑克‧布倫南的看法,以及當前投資領域面臨的危機。伯格堅定的認為擁有美國公司70%股份的法人行動的太少,不能確保這些公司避免在金融方面輕率投資,並仔細分析指數型基金的未來發展。
作者簡介:
財經記者,他的著作在許多商業出版刊物中發表,包括:《商業週刊》,《精明理財》和《彭博市場》。目前居住於賓夕法尼亞的匹茲堡。
章節試閱
第二章 共同基金的開拓者
約翰‧伯格(John Bogle)在共同基金行業的第一位雇主是華特‧摩根(Walter L‧Morgan),他在1920年代建立了威靈頓機構(Wellington organization),並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這個機構是先鋒的前身。1967年,摩根在威靈頓管理公司主席的身份,以及三年後以威靈頓基金(Wellington Fund)主席的身份離職,他是共同基金行業內任職時間最長的主管之一,以及美國公司(U.S.Corporation)任職時間最長的主席之一。直到1998年9月他100歲時去世,他都堅持每週到位於瑪文的先鋒園區,在為紀念他而重新命名為Morgan Build...
約翰‧伯格(John Bogle)在共同基金行業的第一位雇主是華特‧摩根(Walter L‧Morgan),他在1920年代建立了威靈頓機構(Wellington organization),並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這個機構是先鋒的前身。1967年,摩根在威靈頓管理公司主席的身份,以及三年後以威靈頓基金(Wellington Fund)主席的身份離職,他是共同基金行業內任職時間最長的主管之一,以及美國公司(U.S.Corporation)任職時間最長的主席之一。直到1998年9月他100歲時去世,他都堅持每週到位於瑪文的先鋒園區,在為紀念他而重新命名為Morgan Build...
»看全部
作者序
我第一次見到約翰.伯格(Jhon Bogle)是在 2009年11月,賓夕法尼亞州的瑪文市的辦公室。在這之前,我曾在電視節目中看過幾次這位先鋒基金的創始人,並曾在一次會議上聽過他的發言,但從未實際和他面對面的談過話,所以我有些緊張。
一般人在一生中,並不是能經常和傳奇人物見面。作為伯格傳記的作者,我知道在我的工作中難免會談到一些關於他的不愉快的事,關注英雄的隱私是無法避免的事。此外,這位華爾街歷史上「股東利益至上」的最偉大支持者,就因他專制性格和不能容忍異議而揚名。
因為他的性格緣故,所以在自己的著作《The Battl...
一般人在一生中,並不是能經常和傳奇人物見面。作為伯格傳記的作者,我知道在我的工作中難免會談到一些關於他的不愉快的事,關注英雄的隱私是無法避免的事。此外,這位華爾街歷史上「股東利益至上」的最偉大支持者,就因他專制性格和不能容忍異議而揚名。
因為他的性格緣故,所以在自己的著作《The Battl...
»看全部
目錄
序 5
第一章 索普威斯駱駝式戰鬥機 13
第二章 共同基金的開拓者 27
第三章 「他比我們更瞭解基金行業」 33
第四章 如天堂般的婚禮 39
第五章 無法調解的爭執 49
第六章 從先鋒號的甲板出發 61
第七章 解開永遠打不開的結 67
第八章 先鋒手冊 79
第九章 創造忠誠與尊重 87
第十章 大牛市 101
第十一章 「魔鬼的發明」 117
第十二章 傑克兄弟 131
第十三章 「不要叫我牛虻」 151
第十四章 聖•傑克 173
第十五章 投機者的崛起 193
第十六章 相互性的靈魂 209
第...
第一章 索普威斯駱駝式戰鬥機 13
第二章 共同基金的開拓者 27
第三章 「他比我們更瞭解基金行業」 33
第四章 如天堂般的婚禮 39
第五章 無法調解的爭執 49
第六章 從先鋒號的甲板出發 61
第七章 解開永遠打不開的結 67
第八章 先鋒手冊 79
第九章 創造忠誠與尊重 87
第十章 大牛市 101
第十一章 「魔鬼的發明」 117
第十二章 傑克兄弟 131
第十三章 「不要叫我牛虻」 151
第十四章 聖•傑克 173
第十五章 投機者的崛起 193
第十六章 相互性的靈魂 209
第...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Lewis Braham 譯者: 邵超武、朱健樺
- 出版社: 大億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5-30 ISBN/ISSN:978986157866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72頁
- 類別: 中文書> 商業> 投資理財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2012/07/16
2012/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