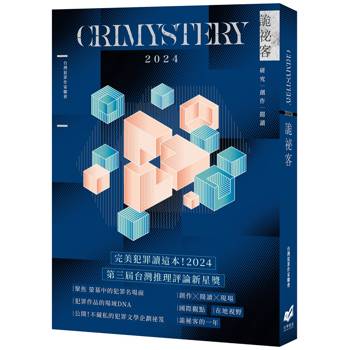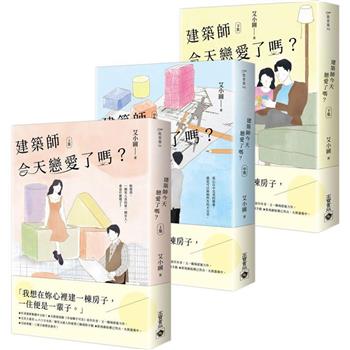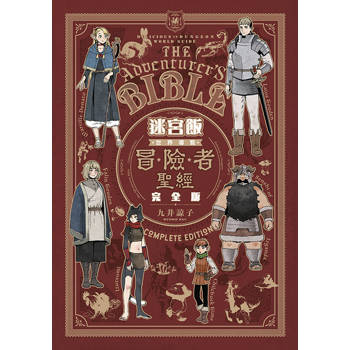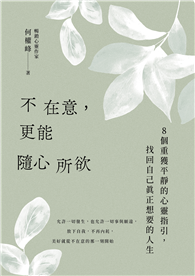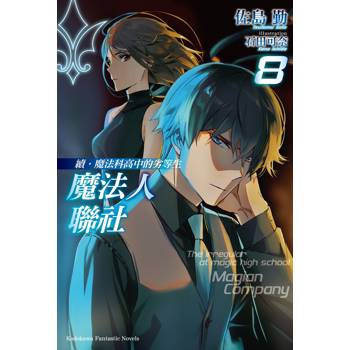燈市街
大明正德元年(一五○六)剛到,北京便迎來了又一個燈節。
燈節起源於東漢。東漢明帝提倡佛事,於上元日在宮廷、寺院「燃燈表佛」,並詔示庶民一律掛燈。不知怎麼著,這種佛教禮儀演變成了民間節日。放燈時間,漢時為一晚,唐玄宗規定為三個晚上,北宋規定為五個晚上,南宋偏安一隅卻規定為六個晚上。
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為招徠天下富商,聚集京師,遂規定從正月初八晚始張燈,至十七日晚落燈,共燃燈十個晚上。自明永樂帝把國都從南京遷至北京後,依然如茲。
明代的元宵節和燈節是混著過的。「正月十五鬧元宵」,其實從正月初八燃燈起,
十三日達到高潮,十五日家家吃元宵時,這個大節慶已趨於尾聲了。
北京集中燃燈的地點在明皇宮的東安門以東,即從東皇城根起,向東二里許,直到崇文門內大街。經過歷代的演變,這時的燈市已比前朝熱火多了。
正月十三這天晚上,天上正飄灑下來一陣小雪,冷颼颼的。但在燈市達到高潮的這個晚上,東安門外人們逛燈的熱乎頭絲毫不減。
明孝宗頭年五月駕崩,舉國服喪了半年,禁伶禁演禁聚餐,京師的人碰到樂事,想抿嘴笑一聲都得四處張望一下。這回上頭開禁了,士民們都像出了籠的鳥兒一樣,緊著到街上撲扇一陣。這時,沿街家家門前的燈柵,上下點燈,不計其數的燈籠,把一條街照得如同白晝。大戶則縛起山棚,擺放宮燈、紗燈、字畫燈、走馬燈,以及五色屏風泡燈等,爭奇鬥妍,故而這一天又被人們稱為賽燈會。
比肩接踵的人流中,太平鼓聲不絕於耳,戴假面具耍大頭和尚的,在人縫中擠來蹭去。更有些尖鑽小偷趁亂做手腳,有時近乎於從攤位上明拿。人們見了,卻只是護住自己的腰包,對這些人不理不睬。在金元之時,為了製造普天同樂的氣氛,在燈市中有三天謂之「放偷」,即小偷在這三天之內,偷也不受懲罰。明代尚存此金元遺風。
逛燈市街,或是一家一戶,或是一夥一群,或是同人結伴,或是男女牽行。總之,
熙熙攘攘,連綿不絕,人山人海,熱鬧非常。
這時,人群中擠出來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和一個半步也不敢離左右的中年男
人。他們一樣在人潮中走動,可不知怎的,不論走到哪兒,前面就空出來一個幾尺寬的空地,使他們能夠暢通無阻地繼續前行,而沒有人能擠著他們,就像暗中有人給他們開道似的。
那少年長得白白淨淨,細皮嫩肉。他的眼睛是冰冷的,眼珠中閃爍著近乎純鋼的光亮,有時瞥視短促而尖銳,但更多的時候是游移的、飄忽的,好像眼前的一切事物都能引起他的好奇一般。實際上,再新鮮的事也不會引起他更大的好奇心。他的穿著極普通,頭戴「武士巾」,用縑為之,巾屋上廣,前後絕隔,垂之於肩,
身上是青布棉襖,白布褲,藍布裙,腳上是白布袢,青布鞋。這副行頭幾乎是全新的。
緊隨其後的那個中年男人頭戴緞面披雲巾,其式扁而頂方,後用披肩半幅,內置棉絮。身著與道袍相似的「直身」。這種寬而大的棉袍一般為士人所穿,是國初明太祖頒詔的標準民庶青布服裝。此人面色蒼白,微胖,無鬚,眼小卻不顯呆滯,在又濃又長的眉毛底下轉來轉去,就像兩隻小耗子,賊溜溜地把尖嘴探出洞外,猜疑地嗅著空氣。
他那發福的形體,圓溜溜的肩,緊隨那個少年行走時屁股的扭動,以及兩手不協調的擺動,都顯現著缺少男人的氣概,倒像個十足的中年女人一般。
在臨街的義豐號老酒店門前,圍了好多人。原先,這家老酒店的門口,有兩樣東西頗吸引人,一個是木頭製做的酒葫蘆,足有一人來高,一、二百斤重,二是店門上方掛著的一塊大木匾,上書「李白回言此處高」,不僅把大詩人李白搬出來招徠顧客,而且這七個字寫得揮灑有力,據說是元人趙孟頫所書。看來,這家的老闆十分精通於行商攬客之道。這次燈會,又訂做了一座龍山,上盤紅綢子紮成的紅龍一條。眼、爪、鱗片上處處是燈,通體透亮,而隨著一個店中小夥計在一個機關處拿扇子呼扇,龍嘴處忽忽地噴著火。讓圍觀的人不住地擊掌稱絕。
那少年聽見人們在大呼小叫,便往那堆人處走去,那中年人緊緊跟上。他們剛走到人堆前,斜刺裏忽地閃出幾條壯漢。他們的衣著不一,都是民間常服,但都穿著一件黃色的對襟罩甲,這種衣服軍民士卒皆不准服用,惟騎馬者可服,而黃色罩甲連騎馬者也不可服,惟軍中騎馬者可服,其衣式較短,為正德年間剛剛啟用。幾條壯漢並不說話,只是彼此間遞個眼色,便橫著肩膀上前,稍一發力,就在人堆中連擠帶別地闖出了一個口子。
那少年上前,踮起腳尖,順著口子向裏看了一眼,見是一座龍山,閃出無動於衷的表情,掉頭便走。他走著,一副對四周事物漠不關心的樣子,唱戲的、踩高蹺的、各種日雜商品從他眼前掠過,他除了扭頭回顧外,毫無表情,只是有漂亮的少女從他眼前經過時,才能惹得他回頭看上幾眼,即使這時,他的嘴也要緊緊地抿著。這種無動於衷,從他的臉上移到了他的身上,滲到了他那優雅懶散的動作上,甚至會在衣服的每條皺褶上表現出來。
一通鑼鼓,壓過了其他嘈雜聲,傳到了他的耳朵裏,他眉心微微一動,見不遠處,
裏三層外三層地圍了一堆人,便又懶懶散散地走了過去。沒走到人堆前,幾個穿對襟黃罩甲的壯漢,便急促地從他身邊繞過,幾個人在人堆邊緣挽起袖子,露出膀子,打頭的悠著勁,一擰身子,擠出了一個空,幾個人往裏一鑽,便不驚動旁人地開出個一尺來寬的小過道,那少年和那婦人般的中年男人,隨即側著身子擠了進去。幾條壯漢原以為那少年照例是看上兩眼便走,誰知道他這回只是一味地呆著,不挪窩了。
場子中有兩個漢子,長相挺相似,像是親哥倆兒。挺冷的天,倆兒都穿著白色的棉搭護,這是元代遺留下來的一種衣式,半截袖,比褂子略長,腰當間束一根半尺寬的大紅帛帶,練把式的人喜服。
倆兒一個拿鑼,一個拿鼓,連敲帶喝。
年長些的那位,圓頭圓眼肉鼻子,臉色烏油油的,有痘瘢;下巴寬大,嘴唇沒一點曲線;脖子短,幾乎和頭一樣粗,個子不算高,背脊闊得異乎尋常。肩頭和手臂一抖一抖的,現著不祥之兆。
他「噹」地敲了聲鑼,隨即厚墩墩的大巴掌往鑼面上一摁,爆出了一嗓子:「俺兩個是哥倆兒!」
另一位擊了聲鼓,亮開了嗓門:「俺哥叫劉寵,在家排行老六,又叫劉六!俺叫劉宸,在家排行老七,又叫劉七。」
他除了個子比劉六略高些外,別的沒啥不同,只是表情顯得聰穎些。
劉六大聲喝道:「俺哥倆兒打霸州而來。霸州在哪兒?距京師不遠,快馬只需一
天的工夫。」
劉七接口道:「來京師做什麼?來京師拉場子。拉場子做什麼?分文不掙!這位要問啦,分文不掙還拉場子,那圖個什麼呢?」
「只圖個以武會友!」劉六又接了過來。說罷,「噹噹噹」敲了陣鑼,末了站定亮相,那架式像個粗墩墩的老樹樁子一般。
圍著的人好奇地看到既拉場又宣稱分文不取的哥倆兒。
靜默中,冷不丁冒出句尖聲細氣的問話:
「霸州來的哥倆兒,你們的話讓我好生納罕。容我再冒問一句,你們這時候來拉場子做什麼?」問話的正是那個微胖、如同女人一般的中年人。他把那少年擋到身後,搶上一步,等著回答。
劉六瞥了他一眼,甕聲甕氣地說:「剛才說了,俺哥兒倆只圖個以武會友。」
「那以武會友又圖個什麼?」中年人似笑非笑地又來了一句。這時,他那對耗子眼泛著賊光。
「以武會友是圖……」劉六被噎住了。
中年人等著回答,眼睛像月牙般彎曲著。他右手輕撫著左邊的面頰,那兒有一個充滿著血筋的肉瘤。
「這位看官,以武會友就是以武會友嘛!」劉七看劉六答不上來了,樂呵呵地接過了話,「這會兒說這話,還不是為了叫列位看官放心,大過節的能不花錢瞧個樂子。」
劉六被提醒了,一揚脖子,「就是這麼回事。」
「列位列位,」劉七怕氣氛冷落下去,忙敲了通鼓,「怎麼個以武會友呢?俺哥倆兒在這兒擺擂摜跤,誰願意上來比試都行。比輸了的,你就下去,回家再練些日子;贏了俺哥倆兒中一個的,俺們掏錢,酒肉請著你,不圖別個,只圖認俺們為友。這就叫『武林走一走,花錢買朋友』!」
既不賣膏藥,又不收場子錢,反倒往外貼錢。京師的士民的確沒見過這等新鮮事。
他們安靜下來,任外面熱鬧非凡,也要瞧瞧此間的動靜。
劉六、劉七在場中四下打拱,好大一陣,沒一個人出來打擂。忽地,響起一聲怪
叫:「我來也!」接著一個戴純陽巾、著裙子的瘦高男子跳入場內。
明代各階層的服制有嚴格規定,往往一看服飾就能知道此人的來路。所謂純陽巾多為生員冬季所戴,其制頂有棉,襞積如竹簡,垂之於後。而男子在外衣之內的束裙係由朝鮮傳入,尤以馬尾裙盛行,其下摺蓬張大。為士人居家時所喜服。看該男子的裝束,就大約可以知道是哪位官人的家人或是跟班的。
劉六見那人上了場,並不搭話,雙手抱拳,微微一拱,便走上前去。將要搭手時,
那人突然閃身,賣了個門戶。劉六微微一笑,搶上一步,一隻有力的手,沉重地放到那人的肩膀上,往下一按,再無其他動作,但見那人的兩隻眼睛越睜越大,嘴角不由自主地抽動起來,高瘦而荏弱的身體,也索索地發起抖來,不消片刻,便一屁股墩兒坐到了地上。
在人們的哄笑聲中,只見又一個潑皮般的漢子,不可一世地上了場。
劉七把劉六撥開,迎上前去。在兩人剛搭上手的瞬間,劉七腳底疾掃,沒等在場的人們看清楚怎麼回事,只見那潑皮橫著身子重重地摔倒在地上,跌了個暈頭轉向。
京師的人好勝。
幾個平日裏練過些花拳繡腿的人見此狀,一個個心裏都是老大不服。哥兒幾個一核計,乾脆,輪番上陣。但見煙土騰起處,劉七左撥一下,右拽一下,不大會兒工夫,便把這一夥人全給收拾了。
場邊的人看傻了。齊聲叫好。那個總是冷漠著臉的少年看得情不自禁地咧開了嘴,
雖不叫好,卻也淡淡地拍了幾下巴掌。他身後的中年人則輕輕撚著臉上那個小肉瘤,在思索著什麼。
正在無人敢上之際,場邊有人發了聲喊:「霸州兄弟還想稱霸京師不成?」話音剛落,一青年男子跳入圈中。
這人生得牛高馬大,濃眉大眼。他頭戴金累絲製成的束髮冠,上有金葉打製的四爪蟒龍盤繞,嵌以睛綠珠石,冠額子上插以雉羽、朱纓。這種冠須,只有朝中重臣或重臣之後方可佩帶,其時要配以窄袖戎衣,束小玉帶。這人戴此冠卻配以綠緞襖子,襖外又罩了件低等的戎衣,即所謂的「褲褶」,其衣式短袖,上截有橫摺,下截為豎摺,為下級軍校所服。這身打扮既表明他是重臣之後,又是軍中的一個半大不小的官。
劉六見此人鐵塔一般,知道來者不善,拱手道:「軍漢貴姓?」
那軍漢亦拱手,「姓李,名丹之。」
場邊的中年人忙俯在少年耳畔輕聲說:
「這是李東陽的兒子李丹之,也是個目無朝綱、到處撒野的東西。」
那少年看得入神,只是不輕不重地「嗯」了一聲。
這時,劉六已和李丹之走開了場子。兩個人圍著一個看不見的圓心,側著身子,臉對臉地轉著,又都是走八卦步,走這種八卦步的目的是力圖搶在對方的身後。由於雙方的步子都到點,所以誰也沒能搶到對方的身後,走了幾圈,一直沒有搭上手。
圈子越走越小,終於搭上了手,你來我往了幾下,誰也撂不倒誰,又忽地各退兩
步,重新繞上了圈子。
劉六是個粗中有細之人,走了一圈場子,故意亂了一步,閃出個破綻,李丹之正專心捕捉對方的失誤處,見此哪肯放過,忽地搶上一步便要抄腿。劉六早有防備,身子一閃,就勢借力往對方的背後一拍,李丹之收不住腳,情急之下,一折脖子,一縮頭,就地一滾,方站將起來。
自唐宋以來的相撲角力,除雙腳之外,身子任何一個部位著地便以輸論。這一回合李丹之輸了,卻又不服,高叫一聲:「再來!」言畢便撲了過去。
劉六見他直朝自己心口撲來,略躲個過,就勢裏從脅下鑽入來,右手帶住了李丹之的肩胛,借力向上猛拽了一把,左手摔住了他的褲襠部,一發力,幾至把這二百多斤的人高高舉起,叫了聲:「去吧!」只見李丹之整個人四肢大開被摜到了地上。
劉七趕忙上前,將他扶起。這李丹之倒也是條好漢,被攙起來後,扶正了束髮冠,
齜牙咧嘴地揉了陣痛處,吸溜著冷氣說:「服抑或不服,後會有期。」
說著,一瘸一拐地走下場子去。
這尊鐵塔一撤下去,再也無人敢上了。
一時冷了場,只剩劉氏兄弟搓著手在場內乾等著。
那少年看冷了場,淡漠的表情頭一次消失了,眉頭微蹙,呈出焦躁之狀。這時,身後的中年人勾頭到他耳畔,輕聲問道:「還想看嗎?」少年中肯地點了點頭。
中年人緩緩地直起身子,從鼻腔裏長長地出了股氣,緊抿著嘴唇,向左右遞了個眼色,短促有力地甩了下頭。
彷彿是一道急令,一個穿黃罩甲的壯漢飛步跳入了場內,騎馬蹲襠,拉足了架式。
劉七見有人上場,雙手抱拳向前,「請問好漢尊姓。」
那壯漢不答話,一頭撲將過來。劉七一驚,閃開,回手就與他摔將起來。那壯漢不是對手,交手了幾下便被摜倒。劉七也不搭理他,又向場邊喊道:「哪位再來?」話剛說完,那壯漢一骨碌躍起,從背後抱住了他的腰。他正掙脫間,又一個穿罩甲的壯漢跳入場內直朝他撲來。
看到劉七一個人跟兩個人摔,劉六眨了眨眼,自語道:「這算哪家的摜法?」言畢上前揪住一個壯漢的衣領,向後一甩,怒喝道:「角力嘛,一個對一個,你們在這裏混鬧個什麼」
像是對他的回答,四、五條穿黃罩甲的壯漢,忽喇喇地衝入了場內,圍住了劉六、
劉七。
劉七看看陣勢,感到不對勁,用胳膊肘捅捅劉六,「哥,這幫人可不大像是來摔跤的。」劉六正在興上,低聲咆哮道:「管他娘的呢!上!」
接著,哥倆兒像兩隻下山虎般撲了上去。
場上是六、七個對兩個,而且沒了章法,被撂了個滾的黃罩甲,爬將起來不退場,
接茬上去又摟又抱。塵土暴起處只聽呼哧呼哧的沉重喘息和皂靴登地的騰騰響聲。漸漸地,劉氏兄弟也顧不得跤場上的規矩了,在黃罩甲們向他們的要害部位使暗勁、下陰招時,他們也只好朝對方卸膀子拿襠了。他們擰成一團,難分難解,這實在是一場不用刀子、不掄拳頭的格鬥。
場邊的人大氣兒不出,驚恐地看著。那少年的臉上卻破題兒頭一遭綻出了笑意。
終於,那六個黃罩甲被制伏得服帖了。他們躺在地上,或是大張著嘴急促地大倒
氣,或是捂這護那,再不就是「哎喲哎喲」地叫喚。
與此同時,劉六、劉七也沒人樣兒了。他們滿身是土,滿身是汗,汗與土混成一
片,黏乎乎地貼在身上。衣服被揪扯成一片一片的,耷拉下來。哥倆兒唇邊泛著白沫,晃晃悠悠地靠在一起。劉六向四下抱拳道:
「列……看官,……今天先練到這兒吧,俺……哥倆兒練不動了。列位……到別
的地方瞧熱鬧去吧。……俺哥倆兒……得回客店洗洗刷刷……緩緩勁兒了。」
他累得連話都說不俐索了。
這時,那中年人「嘿嘿」一樂,尖著嗓門喊道:「以武會友嘛,怎麼這就要走了
呢?還有人要跟你們接著練呢!」
說話間,又是十來個黃罩甲從四面竄入場內,一言不發地把劉六、劉七團團圍定。
那少年見此,扭頭便走,那中年人緊緊跟定。
燈節的高潮是放煙火。這時,煙火升起來了。京師的煙火是有名的。有「響炮」、
「起火」、「三級浪」、「花筒」、「花盆」等幾百種名稱不同的「花兒」,甚至有
「集百巧為一架者」。待施放起來,但見一道道寒光鑽向鬥牛邊,猶如銀燈衝散碧天星。一個個煙炮在空中迸開,嗶嗶啵啵地轟雷繚徹間,火樹銀花開滿天際。待到各種彩煙兒氤氳籠罩時,又一片火織的錦幔在空中鋪開了。
煙火一放,地上的各種活動都暫停了,千萬張臉齊刷刷地向天空看去。
只有那少年兀自走路,全然不管天上有什麼瓊盞玉台、水晶簾泊、八仙捧壽、七聖降妖。在他身後傳來一聲呼喊:
「錦衣衛抓人啦……」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大內錦衣衛:東廠八虎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30 |
小說/文學 |
$ 238 |
歷史小說 |
$ 238 |
歷史小說 |
$ 243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大內錦衣衛:東廠八虎
【本書特色】
明正德元年燈節時,少年皇帝朱厚照的微服私訪;憨直厚道,身手不凡的霸州劉氏二兄弟的無故被捕,後來又奉皇帝之命去追捕一個年輕、貌美、武藝高強的村姑楊娥;閹人劉瑾與其同夥「八虎」的一個個陰謀詭計;耆宿朝臣的死於非命,如此等等,小說如同抽絲剝繭般向人們展示出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故事。小說寫出了皇帝朱厚照在閹人的引誘下,荒廢朝政;置人民於水火而不顧,同樂伎鬼混,在豹房狎妓取樂的荒淫無道,寫出了宦官政治及其特務機構東西廠的黑暗、殘忍與腐敗,同時也錯綜複雜地表現了閣臣與宦官的勾心鬥角……就在這紛紜複雜、險象環生的重重矛盾中,小說以不同尋常的筆觸,表現了霸州鄉民劉七與被他追捕的姑娘楊娥非同尋常的愛情。
章節試閱
燈市街
大明正德元年(一五○六)剛到,北京便迎來了又一個燈節。
燈節起源於東漢。東漢明帝提倡佛事,於上元日在宮廷、寺院「燃燈表佛」,並詔示庶民一律掛燈。不知怎麼著,這種佛教禮儀演變成了民間節日。放燈時間,漢時為一晚,唐玄宗規定為三個晚上,北宋規定為五個晚上,南宋偏安一隅卻規定為六個晚上。
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為招徠天下富商,聚集京師,遂規定從正月初八晚始張燈,至十七日晚落燈,共燃燈十個晚上。自明永樂帝把國都從南京遷至北京後,依然如茲。
明代的元宵節和燈節是混著過的。「正月十五鬧元宵」,其實從正月初...
大明正德元年(一五○六)剛到,北京便迎來了又一個燈節。
燈節起源於東漢。東漢明帝提倡佛事,於上元日在宮廷、寺院「燃燈表佛」,並詔示庶民一律掛燈。不知怎麼著,這種佛教禮儀演變成了民間節日。放燈時間,漢時為一晚,唐玄宗規定為三個晚上,北宋規定為五個晚上,南宋偏安一隅卻規定為六個晚上。
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為招徠天下富商,聚集京師,遂規定從正月初八晚始張燈,至十七日晚落燈,共燃燈十個晚上。自明永樂帝把國都從南京遷至北京後,依然如茲。
明代的元宵節和燈節是混著過的。「正月十五鬧元宵」,其實從正月初...
»看全部
目錄
第一章燈市街
第二章場子
第三章承光殿
第四章內官監
第五章白雲觀
第六章畿內皇莊
第七章廊房頭條
第八章教坊司
第九章窮漢市
第十章六部之首
第十一章崇福寺
第十二章十二團營
第十三章高梁橋
第十四章納后儀
第十五章釣魚臺
第十六章經筵劾
第十七章功德寺
第十八章司禮監
第十九章東廠
第二十章午門廷杖
第二十一章內書堂
第二十二章皮場廟
第二章場子
第三章承光殿
第四章內官監
第五章白雲觀
第六章畿內皇莊
第七章廊房頭條
第八章教坊司
第九章窮漢市
第十章六部之首
第十一章崇福寺
第十二章十二團營
第十三章高梁橋
第十四章納后儀
第十五章釣魚臺
第十六章經筵劾
第十七章功德寺
第十八章司禮監
第十九章東廠
第二十章午門廷杖
第二十一章內書堂
第二十二章皮場廟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馮精志
- 出版社: 益智書坊 出版日期:2012-03-07 ISBN/ISSN:978986167961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36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歷史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