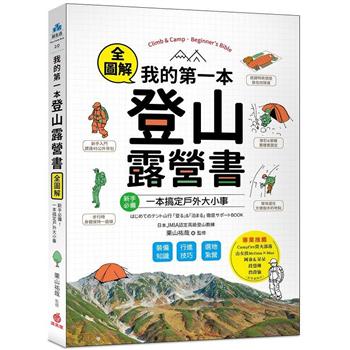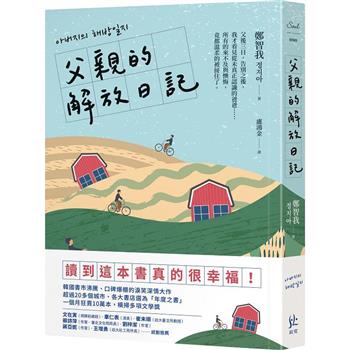這是我從1986年到1998年的寫作旅程,十多年的漫漫長夜和那些晴朗或者陰沉的白晝過去之後,歲月留下了什麼?我感到自己的記憶只能點點滴滴地出現,而且轉瞬即逝。回首往事有時就像是翻閱陳舊的日曆,昔日曾經出現過的歡樂和痛苦的時光成為了同樣的顏色,在泛黃的紙上字跡都是一樣的暗淡,使人難以區分。這似乎就是人生之路,經歷總是比回憶鮮明有力。
回憶在歲月消失後出現,如同一根稻草漂浮到溺水者眼前,自我的拯救僅僅只是象徵。同樣的道理,回憶無法還原過去的生活,它只是偶然提醒我們:過去曾經擁有過什麼?而且這樣的提醒時常以篡改為榮,不過人們也需要偷樑換柱的回憶來滿足內心的虛榮,使過去的人生變得豐富和飽滿。我的經驗是寫作可以不斷地去喚醒記憶,我相信這樣的記憶不僅僅屬於我個人,這可能是一個時代的形象,或者說是一個世界在某一個人心靈深處的烙印,那是無法癒合的疤痕。我的寫作喚醒了我記憶中無數的欲望,這樣的欲望在我過去生活?曾經有過或者根本沒有,曾經實現過或者根本無法實現。
我的寫作使它們聚集到了一起,在虛構的現實?成為合法。十多年之後,我發現自己的寫作已經建立了現實經歷之外的一條人生道路,它和我現實的人生之路同時出發,並肩而行,有時交叉到了一起,有時又天各一方。因此,我現在越來越相信這樣的話──寫作有益於身心健康,因為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來。寫作使我擁有了兩個人生,現實的和虛構的,它們的關係就像是健康和疾病,當一個強大起來時,另一個必然會衰落下去。於是,當我現實的人生越來越平乏之時,我虛構的人生已經異常豐富了。
這些中短篇小說所記錄下來的,就是我的另一條人生之路。與現實的人生之路不同的是,它有著還原的可能,而且準確無誤。雖然歲月的流逝會使它紙張泛黃字跡不清,然而每一次的重新出版都讓它煥然一新,重獲鮮明的形象。這就是我為什麼如此熱愛寫作的理由。
詹姆斯·喬伊絲基金會頒獎詞
余華,我們很榮幸地通知你,你已成為由詹姆斯·喬伊絲基金會榮譽授予,由澳大利亞與愛爾蘭共同舉辦的懸念句子文學獎的首位獲獎中國作家。
你的中篇和短篇小說反映了現代主義的多個側面,它們體現了深刻的人文關懷,並把這種有關人類生存狀態的關懷回歸到最基本最樸實的自然界,正是這種特質把它們與詹姆斯·喬伊絲以及撒母耳等西方先鋒文學作家的作品聯繫起來。在作品《芬妮根守靈》中,喬伊絲把利菲河充分溶入了女性的力量,而在《瓦特》中,撒母耳賦予風以神的力量。你的作品則反映了自然實體的生存狀態,它們既不是聖潔的,也不是聳人聽聞般的,它們只不過是一種類似於天氣般的存在,一種存在於宇宙當中的原始經驗。
現在,有一種全世界都比較普遍的觀點,認為與生俱來的環境的不斷損毀導致了人類的掠奪天性。而你,一位中國作家賦予21世紀的生活以道學的精神,由此帶來一種全新的視野,這也是為什麼喬伊絲把《荷馬史詩》中的奧德修斯稱作領航的大師,他始終與風浪相連,這個人物最終成為他創作《尤利西斯》的原型。
——詹姆斯·喬伊絲基金會
上海文藝出版社
新版說明
將自己的作品集中起來整體出版,我想這是每一位作家的願望。當這樣一套作品系列出現在書架上時,作家就會感到他的寫作和想像開始統一有序了,而且一目了然。感謝上海文藝出版社和郟宗培先生幫助我實現這樣的願望,使這套《余華作品系列》得以出現。現在我的家底都放在上海文藝出版社了,我新掙到的也會陸續放進去。我的意思是說,這是一套開放的作品系列,它包括了我過去的全部作品,也會包括我今後的全部作品。
余華
二三年八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