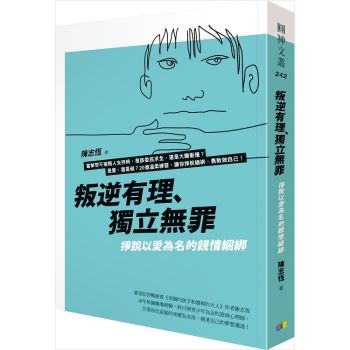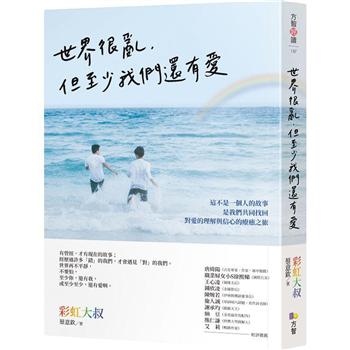第一章
有一艘取名「近江號」的拖曳船和後面拖連著一艘茶色的大型木船,每逢清晨七點許必定穿過流經住家後下方的土佐堀川溯河而上、傍晚六點左右又會按同樣路線折返,這時候,再過一個月就要上小學的松板伸仁,總會探出窗外跟他們揮手招呼。
每次父親問他為什麼只對那艘船家揮手招呼時,伸仁總是這樣回答:
「因為船裡的大叔和大嬸都會跟我招呼啊!」
松板熊吾一邊用剪刀修剪著口髭,一邊看著昨天的晚報。有關史達林死亡的報導幾乎佔去了整個版面。昨天深夜,熊吾喝得酩酊大醉才回到家裡,只從聽到廣播的朋友那裡得知史達林已死的消息,還沒來得及看報紙。
「這傢伙死後八成要下十八層地獄,永世也不得超生哪!」熊吾邊用剪刀尖戳著史達林的相片,邊對著正在做早餐的房江說道。
窗外,不時傳來了數艘拖曳船的轟鳴和電車行經住家旁邊的端建藏橋時的聲響。熊吾一家人從愛媛縣的鄉下搬到大阪市北區中之島七丁目已經將近十個月了。由於房屋仲介商始終找不到那棟被駐軍徵收充做住家兼資料庫三層式樓房的屋主的下落,熊吾他們只好用暫租的方式過日子。
不過,熊吾也擔心原屋主隨時都可能回來,便在樓房西側的空地上蓋了一棟木造房屋,一家三口住在那裡,那棟樓房則出租當倉庫,靠這點房租補貼家用。
堂島川上面有座船津橋。堂島川從熊吾的家前流過,穿過端建藏橋下與土佐堀川匯合之後,就變成安治川了。由於大阪中央批發市場位於面向安治川的北邊,附近多的是買賣昆布和柴魚片等等的海產業者,熊吾就把那棟樓房出租給他們充當倉庫之用。
安治川的下游流入大阪灣,堂島川和土佐堀川的上游則在中之島的東端匯合,蜿蜒流向北邊,連接到主流的淀川。
從住家的後面眺望土佐堀川可以看到正對面的昭和橋上的拱形欄杆。土佐堀川部分的流水從昭和橋下向南流去,變成了木津川,流入大阪港的南側。
因此,可以這麼說,熊吾決定住在大阪的地方,剛好在約莫大阪市西端被河川與橋樑圍繞的一隅,同時也是位於交通的重要地帶。
當初,從南宇和搬到這裡的時候,熊吾還被電車和拖曳船的轟響吵得沒法睡覺,現在不但已經習以為常了,有時候還覺得那也是一種樂趣呢。即使在盛夏時分,因為有河風吹來,家裡倒也舒暢涼爽。
「快起床啦,『近江號』就快來了喔。」
房江一邊在圓矮桌上擺放著碗筷,一邊對著還埋在被窩裡的伸仁,說道:
「阿伸,你都快念小學了,還要賴床啊?我看你要感謝那些拖曳船讓你養成早起的習慣呢。」
這裡的學區是這樣區分的:過了端建藏橋即是西區,一過船津橋那邊則屬於褔島區,因此附近學童們就讀的學校自然不同。住在中之島的孩子們念的是梅田鬧區中心的曾根崎小學,但熊吾他們住在中之島的西郊,所以伸仁得在自家門前的公車站坐公車去上學。
目前,房江最擔心的事情,莫過於今年滿六歲瘦巴巴的有點迷糊的伸仁自己是否真能坐上公車到得了學校?這幾天來,房江跟熊吾談的都離不開這些話題。
「他到野田的市場一下子就迷路了,我才不相信他有辦法一個人坐公車上下學呢。」
房江看著起床以後,脫下睡袍正在換衣服的伸仁,歪著頭這樣說著。
「不僅如此,他還被幼稚園退學過哩。當園長拐彎抹角告訴我,不想收阿伸這名園生的時候,我簡直眼前一片昏暗呢。」
房江說完,熊吾笑著說:
「等他長大以後,還得在他的履歷表註明『幼稚園中輟』才行呢。」
伸仁是個左撇子,畫圖或用剪刀剪色紙或拿筷子都慣用左手。幼稚園的園長為了矯治伸仁的動作,硬逼著他改用右手,但這卻使原本手拙的伸仁,無論剪色紙或吃便當的動作變得更加遲緩了。有一天,他的脖子突然整個偏向右邊不能動彈了。
看診的醫生說,這是硬把左撇子矯正為右撇子的後遺症,由於精神負擔過大,所造成的肌肉神經僵硬。
熊吾為此跑去幼稚園,抓住穿著修道服五十出頭的園長的胸前,怒斥道:
「你這個王八蛋!居然把我的兒子折騰得神經衰弱!有哪條法律規定得要用右手寫字或吃飯啊?」
「我兒子的脖子若一輩子都扭向右邊的話,我也要把你的脖子扭斷!」
園長之所以拐彎抹角跟房江說,希望伸仁轉到其他的幼稚園去,大概是害怕熊吾對他劍拔弩張,可是熊吾卻不准園長把自己怒斥他的事情告訴房江。醫生說得沒錯,自從伸仁恢復使用左手以後,他歪脖子的毛病竟然痊癒了。
伸仁正在洗臉的時候,突然喊了一聲「來了!」,然後就把整個身子探向土佐堀川的方向。
「喔,你光是聽到聲音,就知道那是『近江號』啦?」
熊吾也跟伸仁一起站著看向窗外。
春天的陽光驅散河面上的霧氣。一艘拖曳船後面拉著一艘大木船,從安治川那邊緩緩駛過來了。看那拖曳船的樣子,宛如搬運著比自己身體數倍大食物的螞蟻似的。
「近江號」穿過端建藏橋之後,緩緩地駛到熊吾和阿伸所在的窗下。一個膚色黝黑、約莫四十五六歲的男子,從狹窄的操舵室探出來,微笑地對著伸仁招手,同樣的,站在木船上與那男子年紀相彷、體型健朗的婦女也對著伸仁揮揮手。
「今天,船上載什麼呀?」熊吾出聲問道。
那男子探出半個身子回答說:
「煤炭啦。」
「要載去哪裡啊?」
「毛馬(地名)。」
「就在淀川前面嘛。」
熊吾說完,對著站在木船上正在曬衣服的婦女說:
「看妳每天都很有幹勁哩。」
「窮人沒時間發呆哪。」
這時候,木船那邊走出一個五、六歲的女童和兩隻小狗,來到曬衣服的竹竿底下,看著伸仁。
「她是你們家的女兒啊?看起來很聰明伶俐的嘛。」熊吾說。
「我那個兩歲半的兒子,在船艙裡睡覺呢。」
婦女說著,再次用力揮著手,然後摸著自己的大肚子,笑著說:
「我肚子裡這個,十月要生哩。」
「十月啊?那妳得好好保重才是,被船這麼搖來顛去的,對身體可不好哪。」
「他們兩個都是在船上生的。我已經習慣了。」
「妳真是厲害。」
「你兒子幾歲了?」婦女問道。
「六歲。昨天是我的生日耶。」
伸仁喜孜孜地答道,又問:
「那兩隻小狗叫什麼名字?」
「黑的叫『芝露』,褐色的叫『卡梅』。」
耀眼的晨光把那女童和兩隻小狗的身影照得一片迷濛,整個船家就這樣穿過上游的橋下了。
「他們真是不簡單哪。伸仁,你也想住在船上嗎?你若真的住在船上,每個月恐怕都要感冒發高燒哩。」熊吾一面看著陽光刺眼的上游的方向,一手抓著伸仁的後頸說道。
「我好想住在船上喔。小武的哥哥也住在船上,裡面還有廚房、廁所和浴室耶。」伸仁像猴子般攀抱在熊吾的身上說。
後面拖著載運木材船隻的拖曳船沿著土佐堀川溯河而上,載著砂石的船隻沿著堂島川而下。
熊吾吃完早餐,對房江和伸仁說,今天晚上要為伸仁補辦慶生會。
「晚上七點,你們在梅田新道西側的角落等著,我帶你們去一家好吃的西餐廳。」
過了一會兒,熊吾穿上西裝繫著領帶,走出家門,坐著市公車來到大阪車站,下了車,朝曾根崎警察局走去。在曾根崎警察局擔任交通科科長的杉野信哉就是貴子的哥哥。大約在四十年前,熊吾曾跟貴子私奔到大阪,不幸的是,貴子十七歲那年就死了。半年前杉野還在西成警察局任職,但隨著晉升為科長的同時,他也調到曾根崎警察局了。杉野大概跟熊吾的年紀相仿,但很早以前就以「大哥」相稱。對杉野來說,一來熊吾像是自己的妹夫,二來是報答熊吾對他的恩義。杉野二十三歲來大阪闖天下的時候,就是熊吾請朋友疏通大阪府警局,讓他順利當上警察的。
熊吾走進曾根崎警察局的大門,沿著階梯而上,打開交通科的房門時,隨即看到被三個警察按住肩頸卻仍亂踹桌椅、上身半裸著的男子大聲叫嚷著。
「你們是什麼東西嘛!你們把我當成什麼了呀?有種就拿刀來拚個死活啊!」
昨晚值夜勤已經換上便服身高六尺的杉野站在那個狂亂男子的旁邊。他笑著說:
「聽你的口氣好像很猛的樣子,別以為背上刺個半龍半鳳的就想唬人哪。像你這種只會虛張聲勢的小混混少跟我們大聲嚷嚷!真要拿刀拚個輸贏,被折斷手臂的恐怕是你呀,我們三個人可都是柔道四段的高手喔。」
說完,向熊吾輕輕揮著手。
杉野來到走廊下,對熊吾說道:
「大哥,我肚子餓扁了。今天凌晨四點抓到那個傢伙,他喝得醉醺醺的,搞到現在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都是他害我吃不成沙鍋麵條的。」
「那個小混混犯了什麼案子啊?」熊吾一邊走下樓梯,一邊問道。
「他酒醉開車,撞到小孩之後卻逃之夭夭。肇事逃逸途中因為撞上電線桿,被方向盤打中胸部竟然昏倒了。」
「被撞的小孩傷勢怎樣?」
「整個右膝蓋都被撞斷了。醫生說,粉碎性骨折很難開刀,情況惡劣的話恐怕還得截肢呢。那孩子跟伸仁一樣大,今年要念曾根崎小學。」
「都是警察不對啦,居然把駕照發給那種醉客。以後考駕照的時候,也要審核報考者的面相才行。」
「其實還得考智力測驗呢。」
杉野說,有些烏龍麵店很早就開門了,便朝扇町的方向走去,拐進一條小巷,來到一家烏龍麵店,推開格子門走了進去。
杉野信哉在吃油炸豆腐條清湯麵和雞肉蓋飯的時候,熊吾則看著放在店內的早報。版面上除了史達林死訊的相關報導之外,還有一則留置中國的日本兵將被遣返的消息。
「據說二十三日就會抵達舞鶴(譯註:日本北方四島之一),『興安輪』先到,接著是『高砂輪』。『興安輪』好像要載二千人回來。」杉野說。
「戰爭結束已經八年……。他們居然被拘留了八年。他們肯定被徹底洗腦變成共產主義者才送回來的。」
熊吾這句話惹得杉野發笑,他說了句「中國這個國家真有耐性哪」之後,又說:
「不知道日本要付出多少贖金,才能變成美國那樣的國家哩。」
下個星期日,熊吾就要去考駕照。他為了考取駕照,已經在淀川河邊的空地上,持續練習了兩個月。杉野利用下班時間教他開車。
「倒車入庫我老是學不會,其他就拜託你了。」
熊吾這麼一說,杉野接著說道:
「古川橋的考場裡面多的是我的『部下』。考照那天我也會到場,應該沒什麼問題。儘管如此,大哥你也別太樂觀認為一次就能考上,至少得有考個兩三次的心理準備。」
熊吾預測得很準,汽車業界的銷售成績大幅成長,這兩三年來,都市的汽車愈來愈多,甚至出現了褔特和雪佛萊和克萊斯勒這種美國製的汽車。不過,大阪街頭到處仍看得見拉著貨物馬車的男子不畏路面電車和汽車駕駛怒罵仍悠哉過路的景象。
「你要介紹給我認識的人,是什麼來歷?」熊吾對杉野問道。
「他是台灣人,目前住在淡路島,每個星期大概來大阪三天。」
「他為什麼要住在淡路島?」
杉野露出冷笑,並做了個翹起小指的動作(表示情婦)。
「聽說他曾在昭和十九年,在上海見過周榮文。」
「昭和十九年?他見過周榮文?那個台灣人講話可靠嗎?」
「這我可不敢打包票。平常,我就很少跟住在日本的華僑打交道。那個叫高玉林的台灣人,是個仲介寶石的商人。他好像是出身中國雲南省,昭和二十年逃到台灣,昭和二十五年來到日本的。他的太太和小孩都在台灣,這是真是假就不知道了。早上十點,我跟他約在曾根崎商店街的麻將館碰面。好久沒打麻將了,要不要摸幾圈啊?」
「打麻將……。我已經十幾年沒摸麻將牌了,況且人數也不夠。那個姓高的和你,加上我也才三個人。三個人的牌局我可不會打呀。」
「姓高的女人也會參一腳。現在,學打麻將是最有趣的時候了。總之,那個女人好像是為了打麻將才來大阪的。她剛學會打麻將,但牌技倒是厲害哩。」
「曾根崎警察局就在附近,你這個交通科科長可以在這裡打麻將賭錢嗎?」
熊吾之所以這樣大潑冷水,是擔心今年九月即將退休的杉野很可能因為打麻將而遭到撤職查辦。杉野平常喜歡喝酒,熊吾回到大阪二次,他就曾因為喝醉在酒店打架,把對方打傷了。有柔道三段實力的杉野不但把對方摔得四腳朝天,一個手肘骨折,一個腰骨斷裂。而這兩次麻煩,都是熊吾巧妙掩飾杉野的警察身份,私下找對方和解擺平的。杉野向來不拘小節,個性悠哉,可是幾杯黃湯下肚,就喜歡找附近的醉漢打架。不過,杉野找碴的對象,大都是講話粗暴無禮低級,而且是大學畢業自恃在大公司擔任主管的醉客。
沒什麼學歷的杉野自從當警察以來,總是克盡職守辛勤地付出,解決過許多難纏的案件,是個很有才幹的刑警,但因為酒癖不好常惹來事端,以致於從西成警察局的偵搜一科被轉調到交通科直到現在。
「你的部下說,自從上面把你調到交通科以後,局裡有三件案子成了懸案。還說要不是你出面偵訊,在西成抓到的那名殺妻犯,說什麼也不會招供。」熊吾說。
「我這個老刑警就快退休了。看來對即將退休的刑警來說,安份地待在交通科直到退休還是最保險哩。但話說回來,要是兇案未破就退休的話,良心上總是說不過去。」
杉野一邊笑著,繼續說道:
「我幹了一輩子的刑警,什麼場面沒見過啊,有些東大畢業的年輕刑警卻連命案現場也沒到過哩。他們只要混個十年左右,就當上某分駐所的所長,晉級升官比誰都快,而且還喜歡擺架子。這些連扒手也沒抓過的人,只會坐在辦公室發號施令。」
「對了,你到底是用什麼絕招讓那個難纏的殺妻犯招供的?說出來讓我參考一下嘛。」熊吾說。
杉野陶醉地吸了口菸。
「聽大哥你這樣說話,我也想用我們伊予腔調講話了。」
說完,他壓低聲音說道:
「那時候,拘留期限只剩下一天,我們沒有其他理由可扣留他,也找不到具體物證。雖說他只有情婦可以證明他不在命案現場,但我們實在沒有什麼有力的籌碼。要巧不巧的是,就在我們拘留那名殺妻犯之前,他的情婦卻突然被卡車撞死了。這純粹是一場意外的車禍。這樣一來,我們自然無法追問他的情婦了……。只能看他願不願意自己招供,可是他已經快抓狂了。而且他也從律師那裡知道,再過一天他就會被釋放。」
杉野啜了口茶,沉思了一會兒,用小指挑出杯中的茶梗之後,說道:
「後來,我告訴他上大道的伊佐男的事情。」
「你把伊佐男的事情告訴了那個殺妻犯?」
「大哥,你還記得你回大阪不久,我們在道頓堀喝酒的事情嗎?伊佐男的種種事情,就是你在那時候告訴我的呀。我跟伊佐男從小就經常打架,不過每次想像起他在一木松的墓地自殺的身影時,心情實在有些複雜哪……。我把你告訴我的事情,全部說給那名殺妻犯聽。其實,那時候我已經累了,說這些話並不是要套他。我只是覺得,即使像伊佐男這種無惡不做的流氓,躲在竹林裡嚇得屁滾尿流,仍下定快心求死的悲慘模樣,未免讓人感到心酸……。而且還拜託大哥你把他的遺骨放在他母親的墓裡。總之,我只是在問訊的空檔,跟他閒話家常而已,他卻突然掉下眼淚,低聲地說,他殺了自己的太太。這到底是逼供或者是套供,我也搞不清楚哩。」
熊吾的確把他跟伊佐男的種種始末告訴過杉野,但沒有提過米花懷有伊佐男骨肉的事情。米花答應過熊吾,她若去了大阪,一定會跟他聯絡,可是目前仍沒有米花的任何音訊。
「天底下最難理解的就是人性了。人是基於什麼因緣,如何動心忍性的,其實自己也說不清楚。就像那名殺妻犯一樣,在聽了伊佐男的經歷以後,居然主動招供,當時我也愣住了。我活了這麼大的歲數,只知道人心是最難測啊,除此之外,我實在想不出更好的形容詞。」
杉野用指頭比著自己左眉上的一處小傷,說道:
「這個就是被伊佐男用石頭砸到的傷疤。每次我們在路上碰見,就是一陣廝殺,而他絕不認輸,儘管被我打得很慘,他照樣拚命地衝上來……。」
熊吾和杉野走出麵店,在麻將館附近的咖啡廳喝了杯咖啡,才走進與台灣人高玉林約見的麻將館。
高玉林和他的情婦慢了十五分鐘才來。高玉林約莫四十七八歲、體格矮小,從臉型來看,與其說是中國人,倒不如說像菲律賓人。他的名片上印著:「寶石公司董事長 高玉林」。
高玉林的情婦大約二十四五歲左右,從其化妝的方式和穿著的興趣,以及頻頻吸菸的動作來看,她大概是小酒店的陪酒女郎。
「打麻將之前,我可以先請教周榮文的事情嗎?」熊吾對高玉林問道。
這家麻將館共有六桌麻將台,已經有四組的賭客就座摸牌了。
「我曾跟他在上海工作了兩個月。」高玉林帶著交際性的笑容說道。
「工作?昭和十九年,周榮文在上海做什麼工作啊?周榮文那時候不是在當兵嗎?」
「他在奉天(現今瀋陽)受了傷,後來『這一截』就不見了。」
高玉林用自己的右手指抓住自己的左手腕。據他說,周榮文在奉天受傷失去左手腕,回到上海以後,在某機構負責採買中國軍隊所需的伙食業務。
「他只偷偷地跟我說,他在日本結過婚,有個女兒,等戰爭一結束,就要去找她們母女。」
熊吾聽完,直覺「他」應該就是周榮文。這個姓高的男子的確見過周榮文。
「這麼說,周榮文還活著?他在上海是吧?」熊吾問道。
「可能還活著吧。不過,從那之後我去了廣州,又輾轉到了台灣,往後的情形就不太清楚了。」
「你還知道周榮文的其他事情嗎?」
「他是個老實人,而且頭腦很好。」
「他一個人住在上海嗎?」
「他跟他母親住在一起。不過,我可不曾去過他家喔。」
熊吾從高玉林口中得到周榮文的消息僅此這樣而已。儘管如此,熊吾知道周榮文極有可能還活在世上就很滿足了。
高玉林的情婦先走到麻將台,坐下之後,一邊搓摸著牌支,不時還用催促的眼神看著熊吾。
「難道沒有什麼辦法可以知道周榮文住在哪裡嗎?」
熊吾試著詢問高玉林。高玉林回答說,倒不是完全沒有辦法。
「依目前的情勢來看,要從台灣進入中國境內是非常困難的。不過,透過香港的特殊管道倒是可以進去,只是得花點費用。」
「你的意思是只要花錢,就可以知道周榮文的住所嗎?」
「他待在上海的話,一定找得到。不過,還有其他的方法。」
高玉林的表情宛如在談一筆大生意似的。他說就算知道周榮文的地址捎信給他,以目前中國的政治狀況和中日之間的關係來看,這封信必定會遭到當局的檢查,終究是到不了他的手裡。不過若把此信委託他人,經由香港的特殊管道進入中國境內,在上海找到周榮文,還是可以把信交給他。
「這麼說,對方可以請周榮文當場回信,再把那封信轉寄給我囉?」
「當然是沒問題。只是需要點時間和錢哪。」
「高先生,多少錢你才願意幫忙啊?」
高玉林開出的價碼幾乎是熊吾若考上駕照準備購置一部中型轎車的金額。
「我不能一下子就全部付清。我先付一半給你,剩下的一半,等我收到周榮文的回信,再付給你,怎麼樣?」
有關付款條件,讓我邊打麻將再做考慮吧。高玉林說著,在麻將台前坐了下來,不一會兒,排了「東、西、南、北」四支牌。
下午三點,方城之戰結束了。熊吾約莫輸了一千元,高玉林輸了八百元左右。杉野既沒輸也沒贏,只有高玉林的情婦一人勝出。
「妳的賭運真是強哪。像妳這種超級女賭客誰也贏不了啊。」熊吾一邊付錢給贏錢的女人,一邊說道。
這時候,瞪著三白眼的高玉林告訴熊吾,希望下個月十日,先付一半費用給他。
「下個月的十五號,我的朋友要去香港。」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我要等多久才能收到周榮文的回信呢?」
「至少要四個月吧。」
「再遲要多久呢?」
「可能一輩子也收不到。」
熊吾和杉野答應高玉林下個月十日會在這麻將館跟他碰面,接著從曾根崎商店街朝大阪車站走去了。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血脈之火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76 |
二手中文書 |
$ 300 |
翻譯文學 |
$ 300 |
日本現代文學 |
$ 300 |
日本文學 |
$ 334 |
中文書 |
$ 380 |
日本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血脈之火
宮本輝的人生大作《流轉之海》的第三部曲:血脈之火!
在前二部中,熊吾在戰後百業蕭條的大阪,與妻子房江生下了兒子伸仁,為了這個五十歲才得到的兒子,他決定離開混亂紛擾的大阪,回到他的故鄉九州的一本松村去。然而,多年前結下仇怨的死對頭,也追著他來到島上,想要做一了結。故鄉的新仇舊怨令他看透世情,也決定再次帶全家回到大阪重起爐灶。
伸仁已經七歲上小學,熊吾對商情的透徹,也讓他做起生意得心應手,家中似乎安定下來,但在這個熊吾發跡之地,他該如何面對他的過去和未來?
章節試閱
第一章有一艘取名「近江號」的拖曳船和後面拖連著一艘茶色的大型木船,每逢清晨七點許必定穿過流經住家後下方的土佐堀川溯河而上、傍晚六點左右又會按同樣路線折返,這時候,再過一個月就要上小學的松板伸仁,總會探出窗外跟他們揮手招呼。每次父親問他為什麼只對那艘船家揮手招呼時,伸仁總是這樣回答:「因為船裡的大叔和大嬸都會跟我招呼啊!」松板熊吾一邊用剪刀修剪著口髭,一邊看著昨天的晚報。有關史達林死亡的報導幾乎佔去了整個版面。昨天深夜,熊吾喝得酩酊大醉才回到家裡,只從聽到廣播的朋友那裡得知史達林已死的消息,還沒來...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宮本輝
- 出版社: 麥田 出版日期:2006-08-03 ISBN/ISSN:9861731180
-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440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日本文學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