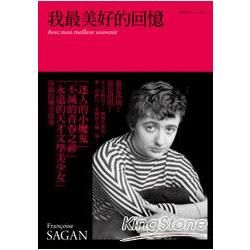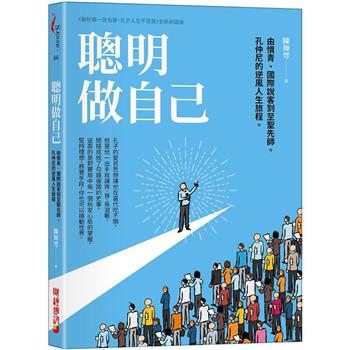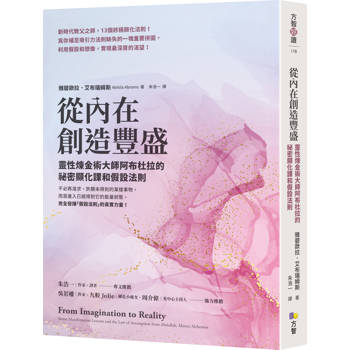難忘的名人、難忘的情事、難忘的際遇、數不盡的風流軼聞,
《我最美好的回憶》是「永遠的天才少女」莎岡
最坦率、最真摰,勇於面對自我的公開情書。
我以為當時莎岡心裡(無論她意識到沒有)已有一種洞徹逐漸揭露:
她將只會、也只能忠實於她的莎岡式幸福。──張惠菁
本書是莎岡最重要、最重視的散文集,
記敘了她寫作《日安憂鬱》成名後所經歷的種種人情世故,
莎岡用奔放的熱情筆調,一種向讀者告白的方式,寫出她生命中最美麗的回憶,
讀書的樂趣、瘋狂飆車、徹夜豪賭,以及與許多名人邂逅爆發的火花,
尤其與法國思想家、作家、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沙特的忘年之交,最為引人注目。
他們的老少戀,到本書所收入莎岡寫給沙特的情書,給文壇留下最美麗的佳話。
本書也藉由莎岡的生活經歷和往事追憶,
重現一九五○至六○年代的歐美文化圈交流盛況,
譬如爵士女伶比莉.哈樂黛、美國著名電影導演奧森.威爾斯、
俄羅斯國際舞蹈家魯道夫.紐瑞耶夫、美國重要劇作家田納西.威廉斯等等,
這些難以忘懷的人與事,深深打動隨意、天性、單純、熱情的莎岡,
將記憶化為文字紀錄,更呈現出莎岡的真性情、慧黠和敏感。
也正是大文豪紀德、卡繆、韓波、普魯斯特的影響,造就永垂不朽的莎岡文學魅力!本書精采度甚至於《流動的饗宴:海明威巴黎回憶錄》,是讀者最美好的文學、文化回憶!
作者簡介
莎岡(Francoise Sagan, 1935.6.21-2004.9.24)
「迷人的小魔鬼」「不滅的青春之神」「永遠的天才少女」
☆「莎岡過世,法國文壇也失去了最閃亮、最敏銳的一顆星。她是文藝圈最頂尖的人物,也是她那時代裡重要的角色。」——法國前總統
席哈克(Jacques Chirac)
☆「莎岡是一抹帶著哀愁、謎樣、疏離與歡樂的微笑。」——法國前總理哈法昂(Jean-Pierre Raffarin)
本名法蘭絲瓦.奎雷茲(Fran?oise Sagan),小名琪琪(Kiki),出生於法國西南洛特省卡日阿城(Cajarc)的富商之家,為家中么女。莎岡自幼嗜愛閱讀,最喜歡讀小說,覺得哲學、歷史、散文無趣。十三歲起陸續讀了紀德的《地糧》、卡繆《反抗的人》、沙特、莎士比亞、詩人阿波里奈、柯蕾特(Colette)、拉封登、蒙田、斯湯達爾、普魯斯特等人的作品,更深受韓波《彩畫集》感動,體悟文字的力量與美,立下投身文學之志願。
莎岡筆下人物多是經濟寬裕的中產階級,他們無憂無慮、享盡奢華,然而內心空虛孤獨,因此成日飲酒作樂,自戀自溺,眼中沒有他人,懶理世間道德。這些人物可說是莎岡自身的投射,其私生活之精采更勝小說情節。
莎岡著作甚豐,出版小說《日安憂鬱》、《熱戀》、《心靈守護者》(麥田陸續出版)、《真愛永不敗北》、《微笑》、《你喜歡布拉姆斯嗎》、《戰時之戀》等三十餘部,並撰有自傳作品《我最美好的回憶》(麥田出版)、芭蕾舞劇《失卻之約》與電視劇本《瑞典的城堡》、《偶爾聽見小提琴》、《昏迷的馬》等多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