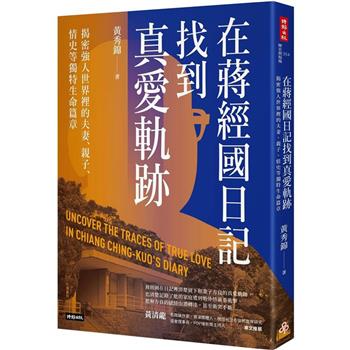無法輕易分辨臉孔的人口
比例高達五十人中就有一個
海瑟是一名文學教授,她常常吻錯男友,甚至錯把男友當壞人報警逮人。海瑟是臉盲症患者──無法從臉辨識人,這是一種罕見的神經病學症狀。根據統計,臉盲症的比例約2%,但我們鮮少聽說周遭有這樣的人,臉盲症患者外表一如常人。
海瑟記不住任何一張臉(包括她自己),連一秒鐘也記不住。她只能從髮型、身材、聲音、穿著、走路的樣子辨識人。路上迎面而來的父母親、同學、朋友,通通像陌生人,對海瑟來說,從背影認人還容易些,但這往往已錯過打招呼的機會,因而造成許多誤解,結果使得她人際關係一團糟,沒有朋友。認不得人讓她害怕自己是不是瘋了。
這本書一半是愛的故事,一半是偵探工作。一個關於家庭、臉盲與寬恕的真實故事。
挖掘自己的真相之旅。
38歲的海瑟帶著準備結婚的男友回家見父母時,她終於開始挖掘關於她的家庭和她自己的真相。她開始相信自己的感受,勇敢地擁抱過去的真實面目,因為唯有這樣才能夠真正放下。在這個挖掘之旅的過程中,她闡明了一個更深刻的真理──就算在缺陷最嚴重的環境下,也能夠看見愛、感受愛,並且將愛銘刻於心。海瑟說:儘管這個家庭有著天大的限制,我們還是深愛著彼此;如果我可以愛我的父母,那我還有誰不能愛!
海瑟有一個狂野的爸爸和一個奇特的媽媽。從小父母離異。
爸爸一身緊身牛仔褲、牛仔靴、燙了一頭捲捲的金色爆炸頭,開車像著了火似的,晝伏夜出。在父親那一身勁裝底下,還穿上女人的胸罩、褲襪、塗指甲油。父親有變裝癖,還不時帶流浪漢回家。
媽媽一身的格紋衫,罩了一件又一件,頭上老是捲著髮捲,連駕照上的照片也捲著髮捲。天還沒亮,媽媽就開著車載海瑟四處追蹤可疑的車子。媽媽沒有死,但卻又像死了;媽媽在不該醒的時候醒來,在該醒的時候又不醒。媽媽患有經神分裂症,每年都幫海瑟轉學。
海瑟必須做所有的家事,哪裡都不能去,只能去學校。海瑟吃紙、吃鉛筆,口中含著石頭,想引起注意。她看著其他小朋友玩耍時,心裡渴望的並不是要和他們一起玩,而是:「哪些小孩會有願意多領養一個小女孩的母親。」
作者簡介
海瑟.賽勒斯
是短篇小說集《水下的喬治雅》與好幾本寫作教學專書的作者。她是《O:歐普拉雜誌》、《太陽報》及其他刊物的撰稿人,在密西根州荷蘭市的希望學院任教。
作者的網站:www.heathersellers.com
譯者簡介
吳妍儀
中正哲研所碩士畢業,現為專職譯者,譯有《雪地拼圖》(馬可孛羅)、《購物台專家為什麼能說服你?心理學家教你突破心防的說服術》(商周)、《白日夢的力量:抓住靈光一閃的創造力》(漫遊者文化)、《我們為什麼要活著?尋找生命意義的11堂哲學必修課》、《紐約好精靈》(麥田)、《我們為什麼要浪費時間睡覺》、《為什麼是碳?》(貓頭鷹出版社)、《天真善感的愛人》、《蓋布瑞爾的眼淚》(木馬出版)、《浮華一世情》(合譯作品,如果出版)、《傲慢與偏見與僵屍》(小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