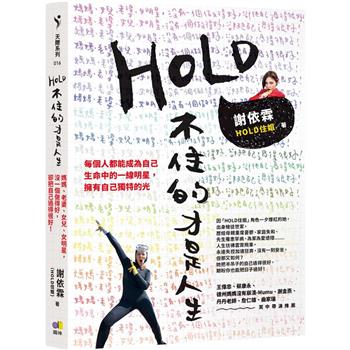那些厚顏無恥的耍賴不走
那些竊取妳切身之物的病態行徑
那些百般把玩也不厭倦的戀物之癖
那些收藏與展示的必須
說的都是──
我怎麼能夠不愛妳!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文學大師帕慕克
最深入愛情之痛的小說創作
獻給所有曾被愛情撕扯得體無完膚的凡夫俗子
「有時我會一動不動地站在一個角落,傾聽內心痛苦的漣漪,努力要讓自己那喊著芙頌、芙頌、芙頌的心臟平靜下來……」
其實,凱末爾曾經擁有芙頌,並且是最純真而完整的芙頌。然而,如同凱末爾的自白:任何人在當下都不會知道自己正在經歷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或許正因如此,本想「永遠把她捧在手心裡」的凱末爾,竟讓芙頌從他手中溜走,甚至是從他手中摔落。
從此以後,為了不斷回到那「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凱末爾在遠遠思念芙頌的痛苦以及放下自尊去靠近芙頌的難堪間撕扯,並陷入了不斷竊取芙頌身邊物品的惡癖。從做愛時掉落的耳墜,到電視機上一個又一個的小狗擺飾,從她的鏡子、她的梳子、她的髮夾,到歷經八年蒐集來的4,213個菸頭。在凱末爾眼中,每一個物品都象徵了與芙頌共處的某一個當下,每一個物品都自有芙頌賦予的靈魂與意義。
日積月累之下,芙頌的物品組成了一座凱末爾的博物館。凱末爾的博物館是她的純真,是他的病態,是一座收藏愛之徒勞的博物館。博物館裡每一個切切訴說著愛情身世的日常小物件,都銘記著那段伊斯坦堡的傾城之戀。
作者簡介
奧罕.帕慕克 Orhan Pamuk
二○○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出生於伊斯坦堡,就讀伊斯坦堡科技大學建築系,伊斯坦堡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曾客居紐約三年。自一九七四年開始創作生涯,至今從未間斷。
帕慕克在文學家庭中成長,他的祖父在凱末爾時代建造國有鐵路累積的財富,讓他父親能夠盡情沉浸在文學的天地間,成為土耳其的法文詩翻譯家。
生長於文化交融之地,令他不對任何問題預設立場,一如他的學習過程。他在七歲與二十一歲時,兩度考慮成為畫家,並試著模仿鄂圖曼伊斯蘭的細密畫。他曾經在紐約生活三年,只為了在如同伊斯坦堡一般文化交會的西方城市漫步街頭。
約翰.厄普戴克將他與普魯斯特相提並論,而他的歷史小說咸認為與湯瑪斯.曼的小說一樣富含音樂性;書評家也常拿他與卡爾維諾、安貝托.艾可、尤瑟娜等傑出名家相評比。帕慕克也說自己非常喜歡尤瑟娜。尤瑟娜在其傑出散文中所呈現的調性與語言,都是帕慕克作品的特質。
帕慕克時時關注政治、文化、社會等議題,一如他筆下的小說人物。近來,他關心政治上的激進主義,例如:二戰中,亞美尼亞人大屠殺事件的真相;庫德族的問題有沒有完美的解答。九一一之後,他積極參與「西方的」與「伊斯蘭的」相關討論;嚴厲反對「黑白問題」的激化。
二○一○年,獲「諾曼.米勒終身成就獎」。
譯者簡介
陳竹冰
一九六六年生於中國西安。一九八五年起,赴土耳其深造,就讀於安卡拉大學史地文學院土耳其語言暨文學系。曾任職於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土耳其語部,並派駐土耳其安卡拉記者站,現任職於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土耳其語部。譯有《杰夫代特先生》、《純真博物館》。


 2016/05/07
2016/05/07 2012/07/10
2012/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