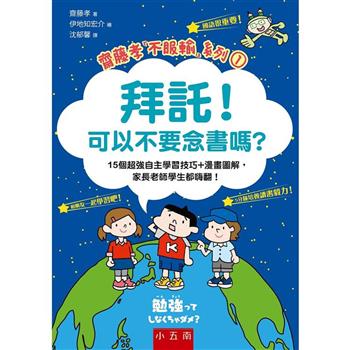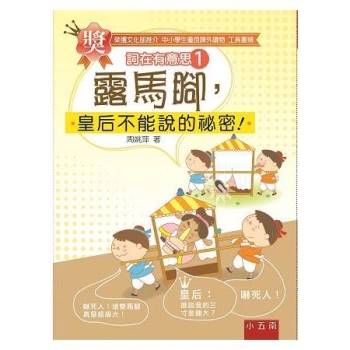「疾病並非隱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盡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然而,要居住在由陰森恐怖的隱喻構成各種風景的疾病王國而不蒙受隱喻的偏見,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寫作此文,是為了揭示這些隱喻,並藉此擺脫這些隱喻。」--蘇珊.桑塔格
1987年,當桑塔格被診斷出罹患乳癌之後,她赫然發現我們早已發展出一套應付疾病的神話學,這套神話的誇張程度,經常扭曲了疾病的真相,讓病患備感孤立。
桑塔格提出,人們對某些疾病,尤其是癌症的迷思,不但給病患加諸更多的痛苦,且往往壓抑了他們去尋求適當治療的方法。她因此為文闡釋,去除了癌症的神祕面紗──癌症不過是一種疾病,而非詛咒或懲罰,當然更不是一件令人難堪的事。
十年後,另一種同樣被神祕化與污名化的疾病──愛滋病出現了,桑塔格再次寫下另一篇論文,針對愛滋病這種流行病,延伸了自己之前的論述。
《疾病的隱喻》一書主要闡釋三種曾被視為絕症的疾病,肺結核、癌、愛滋病,全書包含了〈疾病的隱喻〉與〈愛滋病及其隱喻〉兩篇論文,桑塔格剝除掉疾病千百年來在文化中被誤解的種種迷思,呈現出它們的真正意義。〈愛滋病及其隱喻〉更將她的評論範圍延伸到與愛滋病相關的種種隱喻,揭露真相,讓病患免於罪惡、羞恥和恐懼。本書已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對醫學專業人士,以及成千上萬的患者與照護者,造成了無比深遠的影響。
本書特色
《疾病的隱喻》被譽為我們這個時代最解放人心的經典之作
女性國家書會列為「改變世界的女性著述」
這是一本關於疾病、死亡、美學、文學與社會的書,
當我們的身體為疾病所苦之際,社會的論述如何解釋疫病的恐慌呢?
作者簡介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
1933年1月16日出生於美國紐約市。難以被歸類的傑出寫作者,不僅是一名小說家、哲學家、文學批評家、符號學家,也是電影導演、劇作家與製片。影響遍及各領域,與西蒙.波娃、漢娜.鄂蘭並列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三位女性知識分子,而有「美國最聰明的女人」的封號。
她每發表一本著作都成為了一件文化盛事。代表作品包括:1966年出版的《反詮釋》即成為大學校院經典,令她名噪一時。1977年的《論攝影》獲得國家書評人評論組首獎,至今仍為攝影理論聖經。1978年的《疾病的隱喻》肇於她與乳癌搏鬥的經驗,被女性國家書會列為七十五本「改變世界的女性著述」之一。2000年面世的小說《在美國》為她贏得美國國家書卷獎。
桑塔格一生獲獎無數,1996年獲得哈佛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並當選為美國文學藝術院院士,2001年獲得耶路撒冷獎,表彰其終身的文學成就,2003年再獲頒德國圖書交易會和平獎。雖然她已於2004年12月28日離世,但她提出的問題仍敲打著讀者的心靈,世界也從未停止對她的思考與懷念。
桑塔格部落格:www.susansontag.com/。
譯者簡介
程巍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譯作有《疾病的隱喻》、《反詮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