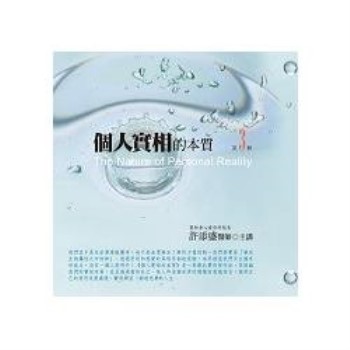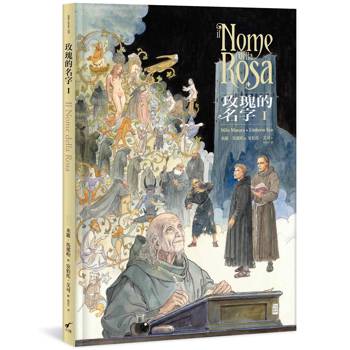◆
是憎恨!這種感情就是所謂的憎恨。
山本彌生望著鏡中的自己,心想。
三十四歲的白皙裸體,在心窩有一塊圓形瘀青,那是丈夫健司昨夜的暴力所造成的。
這一拳讓彌生清楚地產生某種感覺。不,那種感覺從以前就存在了。彌生拚命搖頭,鏡中的裸女也做出相同的動作。從以前就已經存在了,只是說不出那種感覺。
直到剛剛有了「憎恨」這個名詞的瞬間,那種感情像烏雲般迅速擴大,占據了整顆心。此刻,彌生的心裡除了憎恨外,沒有其他感覺。
「我不會原諒你的!」
彌生脫口說出,眼淚也奪眶而出,淚水順著臉頰,滑落在她那小巧而尖挺的胸部。當淚水流到心窩之際,又是一陣令人窒息的痛苦,讓她不由自主地蹲在榻榻米上。連接觸到空氣,也因淚水流過而感到疼痛。大概誰也治不好這種痛楚吧!
感受到這種痛楚,在小棉被下睡覺的孩子們也隨之翻動。彌生慌張地用手擦拭眼淚,急忙地用浴巾包好身體,決定不讓孩子們看到身體上的瘀青。現在不能哭泣。
一旦這麼想,彌生立刻感覺到,這個世界上只有自己必須忍受這種打擊。她被一種強烈的孤獨感侵襲,淚水再度湧出眼眶。她無法忍受被親密的人傷害的事實,也不知道該如何脫離這種痛苦,只能像個無助的嬰兒般號哭。
五歲的大兒子睡得很不安穩,翻來覆去、雙眉緊蹙。三歲的弟弟也受了影響,跟著翻身。現在如果吵醒他們,就沒辦法去工廠了。彌生緩緩爬行,離開臥房。她小心翼翼地拉上紙門,關燈,希望兒子們能好好睡一覺。
接著,彌生躡手躡腳地走向連接小廚房的飯廳,從餐桌上剛洗好的衣堆中找出自己的內衣褲。那是在超市買的廉價胸罩和內褲,毫無任何花邊。她想起婚前都買一些美麗的蕾絲胸罩,因為健司喜歡那種調調。
當時,她根本不知道兩人的未來竟會如此,也想不到夫妻之間居然會隔著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丈夫愚蠢地迷戀著得不到的女人,妻子卻憎恨這個男人。這兩人不可能再度永結同心,因為,彌生不能原諒健司。
今晚,在出門上班前,丈夫大概也不會回來吧!如今,最令彌生擔心的是把孩子留給他照顧,畢竟大兒子的個性多愁善感,很容易受到傷害。而且,丈夫從三個月前就沒有拿薪水回家,母子三人只能靠自己上夜班的微薄收入勉強過活。
究竟是怎麼回事?
狡猾的丈夫趁妻子出門上夜班時,再回家睡覺。等妻子早上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家,夫妻倆必定爭吵不休,用冰冷的眼神互相瞪視對方。這種情形令人感到疲倦不已。彌生深深嘆息,彎腰準備穿上內褲。這時,心窩又是一陣刺痛,她忍不住呻吟。蜷縮在沙發上的貓兒「牛奶」抬起頭,豎直耳朵望著她。昨夜,牠躲在沙發下發出悠悠的叫聲。
一想起當時的情形,彌生的臉色馬上轉為蒼白。憤怒、憎恨以及一種莫名的幽暗感情侵襲著她。截至目前為止,彌生從未厭惡過一個人。出生在外地城市的她,是一對平凡善良的夫妻所疼愛的獨生女。
彌生在山梨縣的短大畢業之後,就來到東京。她在一家中型磁磚公司找到業務助理的工作。年輕漂亮的她是男同事眼中的寶貝,回想當時,可算是這一生的黃金時期。如果她想挑選,合適的對象多得不得了。但是,吸引她的卻是經常在公司出入、任職某建材公司的健司。
健司追求彌生比任何人都積極,彌生在嫁給他之前,交往時總是備受讚美,連彌生自己都夢想著甜蜜的未來。沒想到結了婚,彌生這個備受寵愛的公主,地位立刻跌入谷底。健司總是把她一個人丟在家,自己則沉迷於賭博、喝酒。直到最近,彌生才發覺健司原來是那種喜歡追求得不到之物的男人,東西一旦到手,立即失去興趣。他只是一個追夢的不幸男人。這就是健司。
昨晚,不知道怎麼回事,健司十點以前就回家了。
彌生怕吵醒好不容易睡著的孩子們,躡手躡腳地在廚房裡洗碗。她忽然覺得有動靜,猛然一回頭,看到健司站在後面。他盯著彌生的背,表情彷彿正盯著一種厭惡的東西。彌生嚇了一跳,手上滿是泡沫的海綿掉進流理台。
「啊,嚇我一跳!」
「怎麼,以為是別的男人?」
健司很難得沒醉,只是一臉不高興。不過,彌生對此早就習以為常了。
「對啊,反正平常看到的只是一張睡死如豬的臉孔。」彌生一邊撿起海綿,一邊脫口而出。如果可以的話,她根本不想見到對方。「今天怎麼這麼早?」
「沒錢了。」
「誰知道?你連一毛錢也沒拿回來過啊!」彌生背對著健司說。但是她很清楚健司在笑。
「真的沒有了,連積蓄也花光了。」
「花光了?」彌生顫抖地問。兩人的積蓄應該超過五百萬,馬上就能用來支付新屋的頭期款了……早知如此,自己何必這麼辛苦。
「真的?為什麼?你連薪水都沒拿回來,為什麼連積蓄也花掉?」
「賭博啊,玩『癟十』。」
「你騙人!」彌生愣住了,只能說出這三個字。
「真的。」
「可是,那些錢並不都是你的吧?」
「也不是妳的。」
彌生默默無語。健司隨後又說:「要我離開這個家嗎?嗯,這樣對妳比較好吧?」
發什麼脾氣?有什麼不滿嗎?每次回家,都會興起一場暴風雨。不過,這次事情不是那麼單純,彌生冷靜地反唇相譏:「你走了也不能解決問題吧?」
「那,妳說啊,要怎樣才能解決問題?」
健司一臉狡猾,馬上把問題丟給彌生。這說法早在彌生的預料中。
彌生怒火上升,說:「你最好早點被女人甩掉,那是罪惡的根源。」
突然,彌生感到心窩處一陣劇痛,像是被某種硬物重壓,差點暈厥。她倒在地上,發出哀號,卻搞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接著,像蝦子般蜷縮的背部又被踹了一腳,她忍不住慘叫。
「混蛋!」
彌生瞄到健司一邊咒罵,一邊撫摸著右手走向浴室。她明白自己被丈夫揍了一拳,靜靜地躺著忍受痛楚。浴室傳來嘩啦嘩啦的水聲。
好不容易呼吸變得較為順暢了,彌生滿手泡沫地掀起身上的T恤一看,在心窩處留下一塊清楚的瘀青,彷彿是健司在自己身上烙下的最後印記。她深深地吐了一口氣,拉開紙門,大兒子貴志怯生生地望著這邊。
「媽,怎麼啦?」
「沒事,我摔了一跤,你趕快去睡。」彌生勉強想出這種解釋。
貴志好像若有所悟,默默地拉上紙門。彌生明白他是不想吵醒弟弟,即使這麼小的孩子都有一顆關懷、同情的心,可是,健司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整個人完全變了!難道他原本就是這種人?
彌生用力按住心窩,勉強坐在餐桌前,忍住痛楚,緩緩地調勻呼吸。浴室裡傳來塑膠桶碰撞的聲音。彌生輕笑,連桶子也遭殃了。然後,她雙手掩面,令她可悲的不是挨揍的痛苦,而是不懂自己為什麼會和這種男人生活。
彌生回過神來,發現自己仍穿著內衣褲。她連忙穿上polo衫、牛仔褲。由於最近明顯消瘦,牛仔褲褲頭鬆垮垮的,她只好找條腰帶繫上。
上班的時間快到了,彌生雖然不想去,但又考慮到如果今晚不去,雅子和師傅她們一定會擔心。雅子……任何人的改變都逃不過她的眼睛。雖然有點可怕,但是,自己為什麼會有一股衝動,想把所有事情通通告訴她呢?雅子值得信賴。如果出了什麼事,能夠依靠的人也只有她。彌生覺得自己似乎還有一點希望,稍微加快動作。
玄關有動靜。瞬間,她採取防禦的姿態,擔心是健司回來了,不過聲音似乎未傳進客廳。彌生擔心也許是陌生人闖入,她快步走向玄關。
健司背對著她,坐在門檻上,雙肩無力下垂,茫然地望著地面,襯衫背部髒汙。他似乎未察覺彌生站在背後,低頭不語。彌生一想起昨晚發生的事,內心的憎恨突然膨脹了,這種男人如果永遠不要回來就好了……我不想再看到他……
「妳啊……」健司回頭。「還沒去工廠?」
可能和人打架吧?健司的嘴唇紅腫,滲出血絲。但是,彌生仍舊默默地站著,她不知道如何才能抑制內心湧出的那股憎恨。想不到健司喃喃說道:「什麼嘛!偶爾也該對我溫柔一點。」
這一瞬間,彌生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像是斷線的風箏。她以自己想像不到的速度扯下腰帶,勒住健司的脖子。
「呃!」健司驚訝地想回頭。彌生用力將腰帶往後扯。
◆
對講機鈴聲響起。
「是我。」良江略帶顧忌的聲音傳來。
雅子覺得良江有可能不會來,不過良江卻很守信。雅子開門,良江身穿麻紗質料的短褲,褪色的桃紅T恤,一身打扮和早上一樣。她有點害怕地望著屋內。
「不在這,在車子的行李廂。」
雅子指著停在門外的車子,良江因為靠得太近,慌忙後退一步。
「我還是做不到,可以拒絕嗎?」良江說著,進入玄關,蹲在脫鞋間。
雅子打量著如青蛙般蹲著的良江,那一頭變直的頭髮,不知道多久沒燙了。她早就料到會這樣,所以並不驚訝。
「難道妳去報警了?」雅子說道。
良江臉色蒼白,搖頭說:「不,沒有。」
「可是妳還沒還錢呢!妳寧願讓女兒參加校外教學旅行,也不願接受我一生的拜託?」
「但,那不是正常的要求呀!那可是幫忙殺人。」
「所以我才說是一生的拜託啊!」
「可是,那是殺人!」
「如果是其他事就沒問題嗎?偷竊或搶劫就可以嗎?這又有什麼差別?」雅子問道。
良江愣了一下,輕笑著說:「當然有很大不同了。」
「誰規定的?」
「也不是誰規定,不過在人類的世界裡就是這樣。」
雅子默默地凝視良江。良江不停用雙手拂弄頭髮,低著頭。雅子知道這是困惑時的習慣動作。
「好吧!不過,妳能幫搬嗎?我自己搬不動。」
「我婆婆已經醒了,我得趕快回去。」
「很快就好了。」
雅子穿上良樹的涼鞋,走出門外,雨仍在下,路上的行人稀少。雅子家對面的營建工程已經擱置了很長一段時間,工地裡到處都是被挖起的紅土泥濘,不會有人接近。至於鄰居的住宅雖然屋簷相連接,不過雅子家的玄關位於死角,應該沒有人會看到。
雅子緊握口袋裡的車鑰匙,迅速環視四周,此時正好沒有人經過,應是大好機會。但是,良江還沒走出來。雅子不耐煩了,怒聲叫道:「怎樣,妳到底幫不幫忙?」
「只是幫忙搬……」良江不得已走了出來。
雅子已經拿起玄關前的一塊旅行用的藍色布墊,良江狼狽地愣在車篷架前。雅子繞至車後,打開行李廂鎖。
「啊!」
站在她身後窺看的良江,嚥了一口口水,驚叫一聲。眼前是健司的死狀,雙眼半開、表情呆滯、流至臉頰上的唾液已經乾凅;手腳僵硬、曲膝、雙手伸在半空、手指彎曲,像是想抓住什麼。被拉直的脖頸上留著鮮紅色的勒痕。雅子想起彌生昨晚從屍體的脖子上解下腰帶,又繫在她身上的情景。良江說話了。
「妳說什麼?」雅子回頭問道。
良江雙手合十,聲音略大了,原來正在念「南無阿彌陀佛」。雅子輕拍她的手。
「這麼做太引人注意了,趕快搬進屋裡。」
良江苦著一張臉,雅子不理她,逕自用布墊蓋住健司的屍體,抱起他的手臂和頭部,並用眼神示意良江動作快一點。良江不太情願地抓住屍體的雙腿。兩人小心翼翼地把屍體從行李廂拖出來。屍體僵硬,很容易搬運,不過因為太重又難抓住支撐點,兩人的步履踉蹌。不過,離玄關只有數公尺的距離,總算順利搬入屋內。
雅子喘著氣說:「師傅,這要搬到浴室。」
「我知道。」良江脫掉童鞋般的布鞋。「浴室在哪邊?」
「最裡面。」
在走廊時,兩人屢屢放下屍體稍作休息,總算把屍體搬進洗衣間。雅子拿掉裹住屍體的布墊,鋪在地磚上,以免支解時肉屑卡進隙縫。
「放在這上面。」
良江似乎不再抗拒,點點頭。兩人再度抬起屍體,依雅子事先考慮過的位置,把屍體斜放在對角線上,姿勢與在行李廂裡一樣橫放著。
「真可憐,變成這個樣子,他一定想不到被老婆殺死吧?但願他能夠上西天。」
「那又如何?」
「妳很冷酷啊!」良江的語氣恢復冷靜。
雅子立刻說:「我去拿剪刀,妳把他的衣服全部剪開。」
「妳打算怎麼做?」
「分屍後丟棄。」
良江深深嘆息,但是語氣很鎮定:「口袋裡應該有東西吧?」
「嗯,或許還有皮夾或月票吧?我看看!」
雅子從臥室拿來一把大剪刀,良江已經把健司口袋裡的東西全掏出來擺在浴室門口;有一個磨損的黑色皮夾、一把鑰匙,還有月票、銅板。
雅子打開皮夾一看,裡面有幾張信用卡和將近三萬圓的現鈔,鑰匙好像是家裡的鑰匙。
「必須全部處理掉才行。」
「錢怎麼辦?」
「給妳。」
「可是,那是彌生的吧?」良江說著,又開始自言自語。「不過也很奇怪!不能把錢還給殺夫的妻子。」
「沒錯,就當是妳的酬勞吧!」
良江臉上浮現鬆了一口氣的表情。雅子把鑰匙、空皮夾、信用卡、月票等雜物放入一只小塑膠袋。這附近的田地和空地很多,只要找個地方埋了,就不會有人發現。
良江把現金塞進褲袋裡,一臉愧疚地說:「被勒死了還打著領帶,真是可憐!」
她想替屍體解開領帶。不過,領結繫得很緊,費了一番功夫才解開。雅子顯得不耐煩。
「沒時間做這種事了,剪掉就行了。等一下也不知道誰會回來!」
「妳對死者難道沒有一點尊敬嗎?」良江生氣了。「妳簡直是魔鬼!我不知道妳是這種人。」
「死者?」雅子一邊脫下健司的皮鞋放進袋內,一邊反問。「我覺得這只是物體。」
「物體?明明就是人啊!妳在胡說什麼?」
「
生前是人,現在只是物體,這是我的想法。」
「錯了!」良江很難得發脾氣了,聲音顫抖。「那麼,我照顧的老太婆又算什麼?」
「是活生生的人啊!」
「不對,如果這男人是物體,我家的老太婆也是物體,也就是說,我們這些活人也是物體,所以並沒有差別。」
是那樣嗎?良江的話讓雅子受到衝擊。她想起今天早上在停車場打開行李廂蓋的情景。天亮了,天空飄著細雨,自己的命運有所改變,但是屍體並不會改變,把它視為物體可能是為了掩飾自己心中的恐懼吧。
良江說:「所以妳認為活人是人,死者是物體的觀念並不對,這種心態很傲慢。」
「可能吧!若是那樣,心情就可以放輕鬆了。」
「為什麼?」
「我是因恐懼而強迫自己認為那是物體。不過,如果不認為那是物體,而和我一樣都是人,或許我可以放手去做。」
「做什麼?」
「分屍。」
「為什麼?妳怎麼可以做這種事?」良江大叫。「會遭天譴的,我們都會遭天譴。」
「我不在乎。」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OUT主婦殺人事件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3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0 |
二手中文書 |
$ 300 |
日本推理/犯罪小說 |
$ 323 |
小說/文學 |
$ 334 |
推理小說 |
$ 342 |
文學 |
$ 380 |
推理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OUT主婦殺人事件
1997年週刊文春推理小說Best10第2名
1998年日本推理作家協會大賞
1998年「這本推理小說了不起!」第1名
入選2004年愛倫坡推理小說獎
入圍第19屆吉川英治新人文學獎
入圍第118屆直木賞
改編日劇田中美佐子 飯島直子主演
改編電影西田尚美 倍賞美津子 原田美枝子 室井滋主演
站在日常生活邊緣的她們 平凡人生裡最孤單的一種痛
冷冰冰的家庭成員、照顧久病的婆婆、面對拳頭相向的丈夫、永遠也填不滿的財務缺口……是不可想像的黑暗人生,也是她們的每一天。
她們如何逃出如此無助的絕境?
這不會是罪行,也不是悲劇,只是想要從深淵掙脫的渴望……
香取雅子,冷靜、獨立,企圖掙脫桎梏的家庭主婦,
山本彌生,忍受丈夫嗜賭成性、暴力相向的年輕媽媽,
城之內邦子,好逸惡勞,耽溺於追求物質的未婚女子,
吾妻良江,支撐全家經濟重擔而失去自己人生的寡婦。
四個一同在便當工廠上班的女人,各有各的心思,背負著不足為外人道的陰影。
在彌生不堪丈夫長期精神凌虐與家暴而錯手勒斃丈夫,雅子等人協助分屍、棄屍,卻因邦子愚蠢地將屍塊棄屍於公園引來警方調查,而讓漏洞愈來愈大,不僅將四人推入再也無法回頭的深淵裡,也逐步揭示看似平凡的主婦不為人知的一面……
作者簡介:
桐野夏生
1951年 生於日本石川縣金澤市。
1993年《濡濕面頰的雨》獲得第39屆江戶川亂步獎。本作為日本女性冷硬派小說之濫觴。
1998年《OUT》獲得第51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
1999年《柔嫩的臉頰》獲得第121屆直木獎。
2003年《異常》獲得第31屆泉鏡花文學獎。
2004年《殘虐記》獲得第17屆柴田鍊三郎獎。
《OUT》入圍美國愛倫坡獎最佳小說獎。
2005年《燃燒的靈魂》獲得第5屆婦人公論文藝獎。
2008年《東京島》獲得第44屆谷崎潤一郎獎。
2009年《女神記》獲得第19屆紫式部文學獎。
其他尚有《玉蘭》、《真實世界》、《對不起,媽媽!》、《IN》等作品。
譯者簡介:
林敏生
淡江大學日文系、文化大學日文研究所。專職日文翻譯近二十年,早年涉筆經濟、文學、漫畫等各類性質的譯作,後來偏愛推理小說,所譯的短篇不計其數,中、長篇譯作至今有八十多冊。
章節試閱
◆
是憎恨!這種感情就是所謂的憎恨。
山本彌生望著鏡中的自己,心想。
三十四歲的白皙裸體,在心窩有一塊圓形瘀青,那是丈夫健司昨夜的暴力所造成的。
這一拳讓彌生清楚地產生某種感覺。不,那種感覺從以前就存在了。彌生拚命搖頭,鏡中的裸女也做出相同的動作。從以前就已經存在了,只是說不出那種感覺。
直到剛剛有了「憎恨」這個名詞的瞬間,那種感情像烏雲般迅速擴大,占據了整顆心。此刻,彌生的心裡除了憎恨外,沒有其他感覺。
「我不會原諒你的!」
彌生脫口說出,眼淚也奪眶而出,淚水順著臉頰,滑落在她那小巧而尖挺的胸...
是憎恨!這種感情就是所謂的憎恨。
山本彌生望著鏡中的自己,心想。
三十四歲的白皙裸體,在心窩有一塊圓形瘀青,那是丈夫健司昨夜的暴力所造成的。
這一拳讓彌生清楚地產生某種感覺。不,那種感覺從以前就存在了。彌生拚命搖頭,鏡中的裸女也做出相同的動作。從以前就已經存在了,只是說不出那種感覺。
直到剛剛有了「憎恨」這個名詞的瞬間,那種感情像烏雲般迅速擴大,占據了整顆心。此刻,彌生的心裡除了憎恨外,沒有其他感覺。
「我不會原諒你的!」
彌生脫口說出,眼淚也奪眶而出,淚水順著臉頰,滑落在她那小巧而尖挺的胸...
»看全部
目錄
1上夜班
2浴室
3烏鴉
4黑色幻影
5酬勞
6 四一二號房
7 出口
2浴室
3烏鴉
4黑色幻影
5酬勞
6 四一二號房
7 出口
商品資料
- 作者: 桐野夏生 譯者: 林敏生
- 出版社: 麥田 出版日期:2012-11-04 ISBN/ISSN:978986173819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512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推理小說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2014/05/30
2014/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