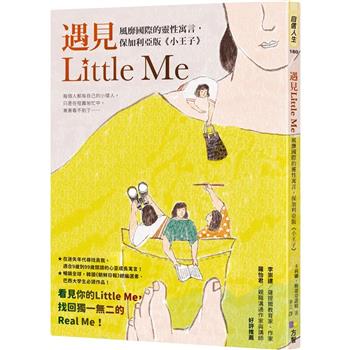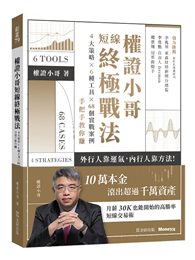前言
一九九○年代頭幾年,我母親曾草草興起寫自傳的想法。由於她在落筆行文之際一向盡可能地避開自己,所以她突然有這個想法讓我挺驚訝的。「就我看來,」她在接受雜誌《波士頓書評》訪問時曾說:「我並不想都寫自己的事情……我也從來不相信自己的品味愛好、幸與不幸會有什麼特殊的示範作用。」
那是我母親在一九七五年接受訪問時說的。當時她在幾年前確診罹患移轉性乳癌第四期,正在進行非常嚴酷的化學治療。醫生雖然希望這套療法可以減輕病況,但至少有一位醫生直接告訴我長期緩解無望,更別說可能治癒(當時仍是病患家屬比病人本身知道更多訊息的時代)。等到她開始恢復寫作之後,就在《紐約書評》發表一系列散文,後來結集出版,即是《論攝影》(On Photography)。在這本書裡頭她不但完全沒談到自己,甚至在後來那本《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中也絕少現身。如果不是她自己也飽嘗那個年代癌症患者遭受的污名,是絕對不會寫出來這本《疾病的隱喻》的。這種因為疾病而造成的污名,現在是比過去輕微一些,但依然存在,通常以自我污名化的形式呈現。
在她的寫作生涯中,我所能想到最接近自傳成分的作品有四部。首先是她在一九七三年出版的短篇小說〈中國旅行計畫〉(Project for a Trip to China),那是她第一次訪問中國之前寫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這篇小說思索的是她自己的童年和她的父親。她父親是個商人,短暫一生的成年時光大都停留在中國,最後也在中國去世,當時我母親才五歲(但她從沒去過當時她父母親所在的天津英國租界區,而是留在美國紐約和紐澤西州,由親戚和保母照顧);第二篇也是短篇小說〈無導之旅〉(Unguided Tour),一九七七年在雜誌《紐約客》發表;第三篇〈朝聖〉(Pilgrimage)於一九八七年同樣發表於《紐約客》,這是她一九四七年在青少年時期於洛杉磯拜訪湯瑪斯.曼的回憶,當時湯瑪斯.曼正流亡美國加州的帕利薩德市。但是〈朝聖〉這篇文章主要是描寫她當時最為推崇敬佩的作家,關於她自己的描述自是遠遠不及,並坦言是「靦腆而熱情的文藝少女和流亡神祇」的會面。最後是我母親第三部小說,一九九二年出版的《火山情人》(The Volcano Lover),結尾出現了一些自傳性質的描述。這種直接談到她身為女人的想法,還有一些童年往事的匆匆一瞥,都是她在已發表作品或採訪時不曾有過的,甚至在她二○○○年出版的最後一部小說《在美國》裡頭也找不到。
「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資本,我想像力的資本。」在那場《波士頓書評》雜誌的訪談中她也這麼說過,並補充說她喜歡「殖民開拓」(colonize)自己的生活經歷。我母親會採取這種說法真是令人感到好奇,也顯得很不尋常,因為她對金錢一向很不感興趣,而且我從不記得她在私底下談話時曾經引用過這種跟金錢有關的譬喻。不過就我看來,這些話倒也非常準確地描述出她做為一位作家的方式。這也是她竟然想要寫自傳,讓我如此驚訝的原因。借用這個資本譬喻的說法,就是她不想再靠這些資本的孳息過活,而是要直接掏老本,探索挖掘那些不合理的極致、那些來路不明的資本,或者說是小說、故事和散文的原始材料。
到最後這個寫自傳的想法也不了了之。我母親後來寫了《火山情人》,並因此覺得自己又回復到一個小說家的身分,對此她深具野心,儘管當時她正寫出她個人最好的散文作品。這部小說的成功讓她找回喪失已久的信心,因為之前的第二部小說,一九六七年出版的《死亡之匣》(Death Kit)毀譽參半,令她非常失望。《火山情人》出版後,我母親長期涉入波士尼亞和處於圍城狀態的塞拉耶佛,為此奉獻全部熱情。後來她又開始寫小說,而就我所知,再也不曾提起回憶錄的事情。
我有時候會誇張地想道,我母親的日記----現在是全三卷中的第二部----不只是她從未涉及的自傳式作品(如果她真的寫自傳的話,我想會是非常文學性且充滿情節、軼事的,就像她極為推崇的約翰.厄普戴克作品《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 那般),而且還是她從來不曾想創作的偉大自傳性小說。沿著傳統軌跡誇張地說,第一本日記《重生》(Reborn)是一本「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一本教育小說,那是她的《布登勃魯克家族》(Buddenbrooks),這本書是湯瑪斯.曼的偉大成就;或者,以較低層次的文學作品而言,可說是她的《馬丁.伊登》(Martin Eden),這本傑克.倫敦的小說是我母親在青少年時期就看過,並終生熱愛不渝的作品。現在這一本----我命名為《正如身體駕御意識》,文句也是從日記內文摘出----則會是一部描述活力充沛而成功的成年生活的小說。至於最後的第三部日記,我暫時還不想討論。
如此形容這些日記的問題在於,我母親曾驕傲而熱切地自承,在她這一生當中都只是個學生。當然,在《重生》這部日記中,非常年輕的蘇珊.桑塔格相當自覺地進行創造,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再創造,從她出生和成長的世界中重新創造自我,做一個她想要成為的人。現在這部日記不再談到她離開童年時的亞利桑那州南部和洛杉磯,前往芝加哥大學、巴黎和紐約的成就感(但絕對不是幸福,這兩個完全不一樣,恐怕也是我母親永遠無法歡快暢飲的泉源),而是在其中記述了我母親做為作家的巨大成功,兼及與許多不同種類的作家、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交遊,從萊諾.崔凌到保羅.柏爾斯,從賈斯培.瓊斯到約瑟夫.布羅茨基,從彼得.布魯克到喬治.孔拉德。在此之間她幾乎是隨心所欲,四處遊走,這也是她童年時期最為渴盼的夢想。這樣的能耐要說對她有何影響的話,也是讓她變得更像個學生,而不是更不像。
對我來說,這部日記最吸引我的,是看到我母親在不同世界間的游移穿梭。其中有些必定跟她內心矛盾有關,有些思想上的背離,我覺得,根本不會減弱,而是變得更為深刻、有趣,說到底,就是抗拒詮釋。但更重要的是,我想,我母親儘管不會高高興興地容忍傻瓜(她對傻瓜的定義,至少可以說,就跟一般人一樣),但當她碰上自己真正欣賞的人時,她就不再是那個她一直想要扮演的導師,而是化身為學生。所以我認為這部《正如身體駕御意識》最突出的部分就在於描述她對很多人的推崇,其中對賈斯培.瓊斯和約瑟夫.布羅茨基兩位的欽佩更是顯得與眾不同。閱讀這些記述之後,應該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我母親的文章,特別是她評介華特.班雅明、羅蘭.巴特和伊利亞斯.卡內提等諸位的文章,那些都是文壇中最早出現的推崇讚譽。
我還覺得這部日記也可以說是政治成長小說。從個人教育的角度來看,正是她邁向成熟的階段。在這本書開頭,記述著我母親曾對美國參與越戰的愚蠢感到極大的憤怒,因此使她成為突出的反越戰人士。她在參觀過美軍轟炸的河內時曾說過一些話,如今來看,我想就算是她,現在對這些發言也會有所保留。不過像這樣的紀事我也毫不猶豫地收錄進來,儘管有許多不同主題的內容會讓我對她感到擔心或者令我自己覺得痛苦。關於越南,我只能說讓她走極端的戰爭恐怖,絕對不是她想像虛構出來的。對於這些反應她或許考慮得不夠周詳,但在當時戰爭對她而言就是難以言喻的怪物。
我母親從未拋棄她反對戰爭的立場。但對共產主義可能解放世界的信念,她的確是後悔了,甚至也公開地揚棄,這點跟她同代的許多人不同(我在此審慎保留,不過目光如炬的讀者應該會知道我所謂跟她同代的美國作家是指哪些人),這不只是針對個別的蘇聯、中國或古巴等代表國家,而是拋棄對整個共產制度的信念。要不是後來跟約瑟夫.布羅茨基的深厚關係,我不敢說她的情感和心靈會產生這麼大的變化,或許這也是她一生當中唯一段平等的感情關係。儘管布羅茨基晚年與她有所隔閡,但是他對她的重要性,不管是在美學、政治或個人上,都是數說不盡的。她臨終前住在紐約紀念醫院,報紙頭條全是南亞大海嘯的新聞。在她去世的前兩天,氣喘吁吁掙扎求生之際,只談到兩個人:一位是她媽媽,另一位就是約瑟夫.布羅茨基。改寫拜倫的話:他的心才是她的法庭。
她時常感到心碎,而這部日記裡頭有許多關於感情失落的詳細描述。就某方面來說,這似乎讓人對她的生活留下錯誤印象,以為我母親只在她不快樂,尤其是很不高興的時候才會寫下大段的日記,而日子過得還不錯時就寫得很少。這種篇幅上的落差或許並不是很適當,但我認為她在愛情上的不幸也是她的一部分,就跟她從寫作獲得的巨大成就感,或尤其是在不寫作的時候永遠抱持的學生般的生活熱情,都足以跟前述那一部分等量齊觀。她對偉大文學作品是個理想讀者,對偉大藝術是理想鑑賞者,對偉大戲劇、電影和音樂是個理想觀眾。也正因為她忠於自我,亦即忠於自己的一生,這部日記會從情感失落的紀事跳到博學的記聞,並一再反覆。我個人當然希望她的生活不是如此,但這已是無關緊要了。
大衛.瑞夫(David Rie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