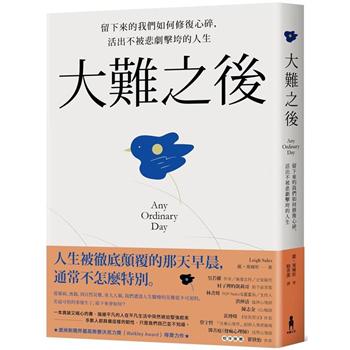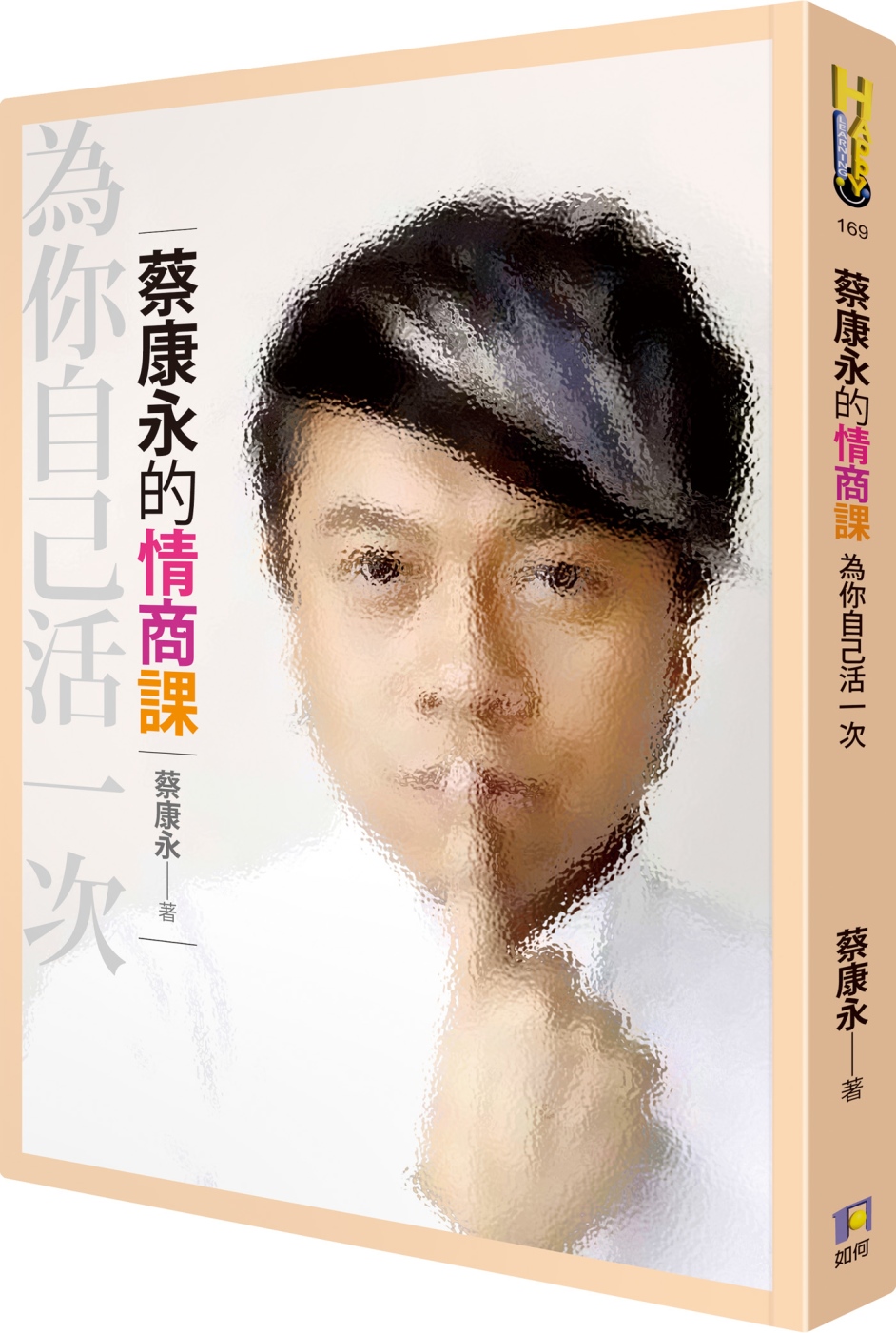◎ 本書收錄91張黑白、12張彩色攝影作品
吳明益│專文推薦
沈昭良│郭力昕│張世倫 │短評推薦
約翰‧伯格、艾倫‧狄波頓推崇的英國文壇焦點人物
視編年為暴政的攝影史;徹底經驗式的攝影評論。
偉大的攝影改變了我們觀看世界的方式;傑夫‧代爾改變了我們觀看兩者的方式。
這本書值得和桑塔格的《論攝影》一起收藏在書架上──《蘇格蘭週日報》
對卡提耶─布列松而言,攝影是「一種理解之道」,而本書,是媒體眼中「英國最聰明的當代作家」傑夫‧代爾企圖理解攝影藝術的故事(儘管他連一臺相機都沒有!)。藉由鎖定攝影師拍攝相同主題的不同手法,代爾帶領讀者親歷靈光乍現的現場,潛入攝影師的集體心靈,化身精心安排或堅持不設計的鏡頭,觀看盲人、帽子、椅子、階梯、理髮店……那些讓史蒂格利茲、史川德、艾凡斯、韋斯頓、蘭格、阿勃絲和伊格斯頓等攝影大師在書中一再相遇的創作主題。閱讀本書,彷彿展開「穿越攝影史的一趟絕妙旅程」(《藝術評論》)。
《持續進行的瞬間》獲2006年ICP國際攝影中心「攝影書寫獎」,是給熱愛攝影與思考之人的非典型攝影書,從一件攝影作品,看一群攝影大師,交織成一張值得細究蒐藏的攝影地圖。
作者簡介:
傑夫‧代爾Geoff Dyer
1958年生於英國切爾頓罕,著作頗豐,包括四本小說、一本關於約翰.伯格的評論研究:《說故事的方式》(Ways of Telling)、一本論文集:《盎格魯英國人的意見》(Anglo-English Attitudes),以及六本無法歸類的作品:《然而,很美》(But Beautiful,獲1992年毛姆獎,麥田出版)、《錯失的索穆河》(The Missing of the Somme)、《出於純粹的狂熱》(Out of Sheer Rage,入圍美國國家書評獎)、《給懶得做瑜珈之人的瑜珈》(Yoga for People Who Can’t Be Bothered to Do It,獲2004年史密斯最佳旅遊書獎)、《持續進行的瞬間》(The Ongoing Moment),以及討論塔可夫斯基經典名作的《潛行者:關於一部前往房間之旅的電影》(Zona: A Book About a Film About a Journey to a Room)。他定期為《衛報》、《新政治家》等主流報刊撰稿。現居倫敦,但大部分時候希望自己住在舊金山。
譯者簡介:
吳莉君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譯有《觀看的方式》、《觀看的視界》、《我們在此相遇》、《留住一切親愛的》、《建築的法則》等。任職出版社多年,現為自由工作者。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2006年ICP 國際攝影中心「攝影書寫獎」
名人推薦:
然而,很美
吳明益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我很少會因為推薦書的人而買書的,但村上春樹為傑夫.代爾(Geoff Dyer)《然而,很美》(But Beautiful)寫的文章除外。我本就是半個爵士樂迷,看到這本書不免好奇,翻開村上的譯記時,看到他提到依代爾的說法,這書是用一種「想像式批評」(imaginative criticism)的方式寫成的,就吸引了我的好奇。我打開書,讀完書之前就未曾再闔上了。
代爾用多樣化的敘事觀點、洗練的文筆重現眾多爵士樂手的生存狀態,也呈現了一個時代的精神狀態。而我最著迷於代爾將很難具體陳述的樂手風格與音樂感受化成文字。比方說他寫次中音薩克斯風手班.韋伯斯特(Ben Webster)的演奏:「慢慢地把樂音吹得如此柔和,彷彿見到某位農場工人把一頭新的牲畜抱在懷裡,也宛如看到某個當建築工的男人為心愛的女人送上鮮花⋯⋯他樂聲的力道如職業拳手般厚重,但他吹奏起慢曲時,就彷彿在呵護著一隻身體冰涼、奄奄一息的脆弱小動物,只有你呼出的熱氣才能使得牠起死回生⋯⋯」把盡是纏綿的韋伯斯特樂句化為具體畫面。我當時想,代爾一定對影像有像貓一樣的敏銳直覺吧。
當我收到《持續進行的瞬間》(The Ongoing Moment)的書稿,果然印證了我的想法,代爾不但對影像敏銳,而且下了大工夫把兩百年來的攝影史做了清理後,再用自己獨特的觀點展開。
許多投身學術研究的人都知道,清理資料是建立藝術批評的第一個難關,接著從荒煙蔓草中尋找一條相對明晰的詮釋之路,則是第二個難關(當然這條路有沒有創造性的風景是非常重要的事)。事實上還有第三個難關,就是用準確又不失優美的文字表現。但因為太多人做不到這點,所以常常有些學者就乾脆否定這個關卡的存在。代爾本身就是D. H. 勞倫斯的知名研究學者,他的《出於純粹的狂熱》(Out of Sheer Rage)就是將論文材料消化後以小說手法寫就的。而在《然而,很美》中,代爾以艾靈頓公爵(Duke Ellington)和哈利.卡尼(Harry Carney)開車到某個小鎮的旅程作為穿針引線的楔子,另一線以傳記小說手法讓眾樂手步向舞臺,逐一上場,彷彿一場獨奏與合奏穿插的競技。這樣勇於突破傳統藝評寫法的代爾,會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寫攝影史?
雖然代爾書中提到他不想使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用的「刺點」(punctum)這個詞來解釋羅伯.法蘭克(Robert Frank)的攝影作品,而改用「小細節」。但我還是要說,代爾這本攝影書的寫法很接近「刺點分析、敘事」。
什麼叫做「刺點」?巴特在他著名的《明室》這本書裡,說自己意在討論攝影過程中,被觀看者的經驗與觀看者的經驗。問題是怎麼「選擇出」那些照片來討論呢?巴特說第一項元素就是照片的時空與場面,這是他用自身的知識文化就可以駕輕就熟地解讀的,稱為「知面」。第二個元素,則稱為「punctum」,這個字又有「針刺、小洞、小斑點、小裂痕、擲骰子、碰運氣」的意思。巴特說:「所謂相片中的刺點,便是其中刺痛我(同時謀刺我,刺殺我)的一個危險機遇。」
整本書代爾都從某個刺點轉到另一個刺點,它們包括「盲人、手、裸體、帽子、階梯、椅子、床鋪、籬笆、窗戶、車窗、雲朵、門」⋯⋯而代爾以「持續進行的瞬間」的敘事,既常停留在一個刺點上,又不斷地讓時間流轉,中間則以引文讓讀者喘息思考。只是巴特講的是「照片中的刺點」,這本書裡還包括了攝影師本身人生的刺點、拍攝過程中的刺點等等。因此,讀者不僅讀到了代爾對相片美學、倫理、社會學的詮釋,還連帶地讀到了攝影家的人生片段、創作觀,與迷亂、傳奇的創作行為。
比方說移居美國後不被重視的攝影師安德烈.柯特茲(André Kertész, 1894-1985),曾沮喪地對年輕的攝影家布萊塞(Brassai)說:「眼前這個與你重逢的人,是個死人。」他甚至把自己的作品分裝在兩只購物袋,放到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的門口。代爾寫道:「身為一名攝影大師,他必須像個街頭藝人,滿足於最微不足道的認可,滿足於漠視和忽略他才華的路人投進他杯子裡的銅板。他的目光銳利、優美、纖細、極富人性,但他得到的對待卻和盲人無異。」只是幸運終究回到柯特茲的身上,在戰爭中他曾交付給一位巴黎女子以致佚失的一批底片,竟傳奇性地再次出現,讓柯特茲重拾偉大攝影家的聲譽。
每讀到此,我都要懷疑,代爾根本是為那些拍下無數動人照片的攝影師們,留下另一種文字的身影。
而書中往往也將他的藝術觀點注入某些段落,讓我們彷彿讀到精采論文的睿智。比方說人們常說攝影在留取肖像的功能上幾乎取代了繪畫,但代爾說:「攝影無法像繪畫那樣自由。」因為皮耶.波納爾(Pierre Bonnard)畫他妻子瑪特(Marthe)畫了四十年──但她永遠是二十五歲時的樣子。而攝影大師史蒂格利茲如實地拍攝他的妻子歐姬芙,卻只能隨著她的轉變與年華老去。那段似談攝影史,也似談史蒂格利茲戀愛史的段落,讓我低迴不已。
傑夫.代爾是個學者,但他的著作都在嘲弄學究們如何拆毀、殺害藝術與美,他因此找出了一個辦法,那就是以另一種美學形式來詮釋他所要分析的美。這和中國「以詩應詩」、「以詩解詩」的方式,異曲同工。這樣的詮釋雖然常不見容於現代學術界,一些對某種藝術類型也有自己定見的讀者也常會覺得:「可以這樣解釋嗎?」然而,你不可否認的是,代爾的書寫真的很美。
But beautiful,它就像那些留在我們腦海中的經典影像,帶著偶然性卻又必然存在的一種持續進行的瞬間,打擊我們、刺傷我們、啟發我們。
媒體專家推薦
十足原創之作。讀完之後,生命似乎變遼闊了。──約翰‧伯格
《持續進行的瞬間》是關於攝影的精湛沉思。──艾倫‧狄波頓
現實與想像的交疊,歷史與時空的穿越,不僅讓人流連於細膩繽紛的文采與轉折起伏的讀趣之間,也讓我們相信,攝影詮釋與評介在書寫形式上的遼闊與可能。──沈昭良,當代攝影師
代爾悠遊於攝影、文學、電影典故之中,廣徵博引,文字深刻而慧黠。他閱讀攝影的「刺點」,不僅是對影像細節的敏銳梳理,更是一種對歷史與文化的全面關照。──郭力昕,攝影評論者
代爾博學聰敏、見多識廣,彷彿全能的傳統歐洲知識分子,文章卻從不故弄玄虛,他書寫爵士樂、攝影,乃至塔可夫斯基的電影,筆法平易近人,觀點秀異出眾,使他成為當今英國文壇備受矚目的意見領袖之一。──張世倫,藝評人
這部傑作值得和桑塔格的《論攝影》一起收藏。──《蘇格蘭週日報》
代爾另闢蹊徑,偷偷對學者專家的領域從旁突襲。──《新政治家》
堪稱攝影書寫史上的最優雅反芻。──《週日電郵報》
讀者感覺自己已進入攝影師的集體意識。──瑞秋‧柯恩,作家
直到此刻,我們才徹底消化了這些藝術家的作品。──《紐約時報書評》
得獎紀錄:2006年ICP 國際攝影中心「攝影書寫獎」名人推薦:然而,很美
吳明益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我很少會因為推薦書的人而買書的,但村上春樹為傑夫.代爾(Geoff Dyer)《然而,很美》(But Beautiful)寫的文章除外。我本就是半個爵士樂迷,看到這本書不免好奇,翻開村上的譯記時,看到他提到依代爾的說法,這書是用一種「想像式批評」(imaginative criticism)的方式寫成的,就吸引了我的好奇。我打開書,讀完書之前就未曾再闔上了。
代爾用多樣化的敘事觀點、洗練的文筆重現眾多爵士樂手的生存狀態,也呈現了一個時代的精神...
章節試閱
我不是第一位從波赫士(Borges)筆下「某本中國百科全書」裡尋求靈感的研究者。根據這本神祕奇書,「動物可以分成:(一)屬於皇帝的;(二) 充滿香氣的;(三)受過訓練的;(四)乳豬;(五)美人魚;(六)傳說中的;(七)流浪狗;(八)包含在這個分類裡的;(九)發瘋似不停顫抖的;(十)多到數不清的;(十一)用很細的駱駝毛毛筆畫出來的;(十二)等等;(十三)剛剛把花瓶打破的;(十四)遠看很像蒼蠅的。」
雖然本書所進行的攝影調查,就嚴謹和古怪程度都不能與之相比,但在前人立意良善做法的鼓舞下,本書嘗試將攝影的無窮樣式排列成某種散漫秩序。沃克.艾凡斯(Walker Evans)曾說,這是他的「拿手好戲」之一──像詹姆斯.喬哀思(James Joyce)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這樣的作家,都是「無意識的攝影師」。但是對華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而言,沒有任何東西是無意識的。他堅稱:「在《草葉集》裡,每樣東西都跟照片一般真實。」「沒有任何東西被詩意化。」渴望效法「太陽神的祭司」,惠特曼創造出來的詩作,有時讀起來宛如一本巨大且不斷擴充的攝影目錄的延伸圖說:
看哪,在我的詩篇裡,內陸堅實而廣大的城市,有鋪石的街衢,有鋼鐵 和石頭的建築,川流不息的車輛和貿易,
看哪,那多滾筒的蒸汽印刷機──看哪,那橫跨整個大陸的電報,﹝⋯⋯﹞
看哪,雄壯而迅速的火車駛開之際,喘氣、鳴響著汽笛,
看哪,犁田的農夫──看哪,採礦的礦工──看哪,數不盡的工廠,
看哪,機械匠手持器具在工作臺上忙碌著﹝⋯⋯﹞
至於艾凡斯,他在1934年整理了一份照片目錄,藉此釐清自己
究竟想在作品中傳達哪些東西:
人,所有階級,被一連串新出現的窮困潦倒包圍纏繞。
汽車和公路風景。
建築,美國都會品味,商業,小規模,大規模,俱樂部,城市氛圍,街道氣味, 可惡的東西,女子俱樂部,冒牌文化,壞教養,式微的宗教。
電影。
城市人讀了什麼,吃了什麼,為娛樂看了什麼,為放鬆做了什麼卻還是無法放鬆。
性。
廣告。
還有其他一堆,你知道我的意思。
文化史家亞蘭.崔藤博格(Alan Trachtenberg)曾經指出,這目錄讓人想起路易斯.海恩(Lewis Hine)早年的《社會與工業攝影目錄》(Catalogue of Social and Industrial Photographs),「只是添加了艾凡斯的諷刺」。然而,這兩本傑作的差別可不只有諷刺而已。海恩的目錄合乎邏輯,嚴密精準:「移民」、「工作中的女性工人」、「工作中的男性工人」、「一名工人的人生插曲」等等,由一百多項主題和八百多項次主題組成。該書是井然有序的範本,完全欠缺艾凡斯企圖在他目錄中呈現的特質:充滿挑釁、高度偶然且極度不充分(「還有其他一堆」)。
艾凡斯最知名的一些作品,是1935至1937年間,在農業安全管理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資助下所拍攝的。該局原名移墾管理局(Re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是羅斯福推行「新政」的機構之一,成立宗旨是為了改善貧農與佃農因大蕭條而瀕臨飢餓邊緣的命運。當時經濟學家雷克斯佛.塔格威爾(Rexford Tugwell)主掌農業安全管理局,1935年,他指派昔日助教羅伊.史崔克(Roy Stryker)打理歷史部門。這兩個男人深信,攝影的力量可為經濟論述增添人性的真實面向,但一直到該年秋天,史崔克獲命全權負責,為管理局的政策與工作拍製一套攝影紀錄,那時他才對自己的任務及權力有了更清楚的認知。當他看到委任攝影師已拍出的一些照片後,這項使命的焦點就變得更加犀利。那些照片是艾凡斯拍的,令人印象深刻,為他贏得史崔克的「資深報導專員」一職。艾凡斯將這項任命視為某種「得到贊助的自由」,不過,就像其他替史崔克工作的許多攝影師一樣(班.夏恩﹝Ben Shahn﹞、桃樂西.蘭格﹝Dorothea Lange﹞、羅素.李﹝Russell Lee﹞和亞瑟.羅斯坦﹝Arthur Rothstein﹞等等),他發現他的自由受到贊助者的掣肘。隨著史崔克的使命感日益增強,他發出的「拍攝腳本」也越來越嚴格,不僅按照季節,往往還細分地點,並以極端瑣碎的細節逐項列出他想要的拍攝內容。下面就是摘自「夏季」腳本裡的一段內容:
行駛在開放公路上的擁擠車輛。加油站的服務人員正在替敞篷旅遊巴士和敞篷車的油箱加油。
假山;陽傘;海灘傘;海浪輕拂的沙灘:濺灑在遠方帆船上的白浪。
站在樹蔭與涼篷下的民眾。電車與巴士搖下的車窗;就著噴泉或老井喝水的民眾;背陽的河堤,陽光在水面上閃耀;在泳池、河流和小溪中游水的民眾。
在「美國人的習慣」這個標題下,他指示負責「小鎮」生活的攝影師尋找:「火車站──看著列車『穿越』;在前門廊閒坐;女人站在門廊上和過街民眾閒聊;修剪草坪;幫草坪灑水;吃甜筒冰淇淋;等公車⋯⋯」在「城市」這個標題下,則是要求攝影師鎖定人們「在公園長椅上閒坐;等電車;遛狗;婦人牽著小孩走在公園或人行道上;小孩玩遊戲⋯⋯」以上照片,還會搭配「整體」鏡頭予以補充:「『加油』──汽車加油;『修補房屋』;塞車;繞行標誌;『工作中』⋯⋯柳橙飲料。海報張貼工;看板畫工──群眾看著正在繪製的櫥窗。空飄文字⋯⋯圍觀遊行;彩帶;坐在路邊⋯⋯」
這些腳本有獨特的詩意──一種無所不包的偶然詩意,它們如今讀起來就像圖說,證明了史崔克的攝影師們儘管不情願,仍然極為勤奮地執行他的命令。除了這些腳本外,史崔克還會附上更詳盡的指示,以免任何疏漏。1939年在德州的阿馬里洛(Amarillo),他問羅素.李:「榆樹成蔭的街道到哪去了?」還有一次,他要求羅素.李找出「一家小鎮理髮店,店裡要有每個人專用的(刮鬍膏)杯子,上面寫了每位公民先生的大名」。在丹佛時,史崔克要羅斯坦留意「耙燒樹葉。整理花園。準備過冬」的景象,他還加上一句:「別忘了,要有人站在前門廊上。」有些攝影師,像是艾凡斯和蘭格,會在履行史崔克命令的同時,順便把自己的攝影計畫夾帶進去,於是時而拍出呈現異類混雜或異類融合結果的照片。
1950年代,艾凡斯和瑞士年輕攝影師羅伯.法蘭克(Robert Frank)結為好友,他鼓勵法蘭克申請古根漢獎助金(Guggenheim fellowship)。為贏得獎助金,法蘭克列出一張極為個人化的拍攝清單:
一座夜晚城鎮,一座停車場,一間超市,一條高速公路,擁有三輛車的人和沒有半輛車的人,農夫和他的小孩,一棟新房子和一棟牆板歪扭的房子,品味的獨裁,富麗堂皇的夢想,廣告,霓虹燈,領導者的臉孔,追隨者的臉孔,瓦斯桶和郵局和後院⋯⋯
1955年,法蘭克拿到獎助金,踏上橫跨美國之旅,並拍下將近七百捲底片。沖洗出三百張負片之後,法蘭克將照片分成諸如「標誌,汽車,城市,人民,招牌,墓園⋯⋯」等類別。等到攝影成果以《美國人》(The Americans)的樣貌出版(法國1958年;美國1959年)時,上述初步分類在書中僅殘留蛛絲馬跡。書中依然有汽車和墓園的照片,但不再照著原先預定的目錄編排。
撰寫本書時,我充分理解還有其他更明智的組織方式,但我選擇借鏡極其偶然、臨時且經常被棄之不顧的嘗試,而放棄仿效海恩有條不紊的做法。就像法蘭克在他的古根漢申請書中所寫的:「我構想中的計畫,會在進行過程中逐漸塑造出自己的形狀,它的本質是非常有彈性的。」蘭格也認為,「如果事先就知道你在尋找什麼,意味著只能拍出預料中的東西,而那是非常有限的。」就這點而言,她認為攝影師「完全沒計畫」,只拍「他直覺想拍」的東西,是一種很好的做法。謹記蘭格的話,我試著對所有事物盡可能保持開放態度,「就像一件尚未曝光的感光材料」。某些照片攫住了我的目光,就像曾經有某些事情發生攫住了當初拍下它們的攝影師的目光。在這兩個過程中,最初的偶然性都扮演關鍵角色。不過,過了某一階段,我開始看出當中有些照片具有共同點──比方說,都有一頂帽子──而一旦我察覺到這點,我就會開始尋找有帽子的照片。我希望我對照片的看法是獨斷的、偶然的,但過了某一階段後,事情自然而然地匯聚到特定的興趣領域。當我理解自己被帽子吸引,帽子這個概念,就會變成一個組織的原則或節點。
在分類學的既定概念中,不同的類別涇渭分明,沒有重疊空間,例如貓和狗。無論是因為分類學裁定事情就是這樣,或是因為它反映分類的內置區隔是無意義的爭論,總之生活中就是不存在某種稱為「膏」或「牟」或「狗貓」的東西。(中略……)儘管人們期待分類學既全面又客觀,但是我很清楚,對我的興趣而言,局部而偏袒的分類學才是最有用的。
因此,我猜這本書可能會惹惱許多人,尤其是那些比我更了解攝影的行家。關於這點,我可以理解,但如果我們想要有任何進展,有一類批評我連聽都不想聽。那就是「那X怎麼辦?」或「為什麼他沒提到Y?」關於不被允許的忽略,均指控無效。套用惠特曼的話,我們是否同意,「許多看不見的也在這裡」,為了學習有關帽子照片的有趣知識,討論乃至提及攝影史上每一張曾經拍下帽子的照片,並非必要。我希望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做這種學習的人,正是寫這本書的人,也是讀這本書的人。開車的人,也是一塊兒兜風的人。對卡提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而言,攝影是「一種理解之道」。而這本書,就是我企圖理解他所掌控的那項媒介的故事。
約翰.札考斯基(John Szarkowski) 認為,蓋瑞.溫諾格蘭(Garry Winogrand)最好的照片,「不是描繪他已經知道的事,而是描繪新的知識。」我希望觀看照片時,能看到我從中汲取了什麼樣的新知識──雖然為了做到這點,我必須帶入某些與他們有關的舊知識。我也希望能對不同攝影師之間的差異有更多了解,或至少能變得更加敏銳,因而對他們的風格更有頭緒。如果風格是內容與生俱來的,那我想知道,是否能從內容中或藉由內容來指認風格。想要做到這點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去觀察不同的人如何拍攝同樣的事物。
這本書寫著寫著,最後變成一本主要(但並非完全)關於美國攝影,或至少是關於美國的攝影的書。這並非我的意圖。一開始,我並未鎖定任何攝影師,或任何攝影照片。任何人任何事都有可能被選中。書中提到的攝影師,有些之前我從未聽過,也沒看過他們的作品(我從未宣稱自己是這方面或任何方面的專家)。有些重要的攝影師我碰巧不太感興趣(例如艾文.潘﹝Irving Penn﹞);有些攝影師我曾經寫過,或找不出任何新東西可寫(例如卡提耶──布列松和羅伯.卡帕﹝Robert Capa﹞);有些攝影師我以為我會長篇大論,但最後只寫了一點點(例如尤金.阿特傑﹝Eugene Atget﹞,我們最好就此打住,別再列舉);有些攝影師我則是壓根沒打算提,最後卻寫了很不少。麥可.歐莫羅德(Michael Ormerod)就是其中一位,本書好幾個主題都在他的作品中達到最高潮。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幸運突變。他就像作者安插在書中的代表:一名考察美國攝影的英國人。
歐莫羅德享有從媒介內部考察的優勢,也就是透過攝影本身,但我可不是攝影師。我的意思是,我不僅不是一位專業或嚴肅的攝影師,我甚至連一臺相機都沒有。我唯一拍過的照片,是觀光客請我幫他們拍的,用的是他們的相機。(這些希罕難得的作品,如今散布於世界各地的私人收藏,大多在日本。)這當然是一大缺陷,但這同時意味著,我是從某種非常純粹的位置來理解這項媒介。我還有個預感,以不拍照的身分書寫攝影,會很像我在1980年代末書寫爵士相關書籍時的情況,那時我也不會演奏任何樂器。當年我寫那本書,是因為既有出版品無法滿足我對音樂及其創造者的好奇心。攝影書籍的情況,也幾乎和音樂書籍並無二致。市面上早有討論攝影概念──或史蒂格利茲所謂的「概念攝影」(the idea photography)──的傑作,出自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約翰.伯格(John Berger)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針對攝影史或攝影史曾出現的各種類型與運動,也不乏精闢研究。由策展人和學者為特定攝影師所撰寫的高水準專著,更是不勝枚舉。攝影師群體也證明了他們對自己所使用的媒介雄辯滔滔。這一切讓事情變得加倍輕鬆。既然門檻被拉得這麼高,我大可在門檻下自由行走。不過,套用黛安.阿勃絲(Diane Arbus)的話,我仍然希望「在論述有關事物的性質時,我能占據某個無足輕重的角落」。
蘭格曾說:「相機這項工具教會人們如何觀看,而無須使用相機。」我或許不會成為攝影師,但現在我知道如果我是一名攝影師,我可能已經拍下怎樣的照片。
我正在思考
一種顏色:橙色。
法蘭克.歐哈拉(Frank O’Hara)
蘭格記得祖母曾經對她說:「這世界上沒有比一粒柳橙更美的東西。那時我還小,但我知道她的意思,分毫不差。」
1958年,蘭格曾在西貢的市場拍攝一堆柳橙,或者應該說,試圖拍攝一堆柳橙。你無法完全肯定它們是柳橙的理由很簡單,那是張黑白照。這是一個重大的哲學問題:你能用黑白底片拍柳橙嗎?柳橙之為柳橙的特質就該用彩色攝影呈現,難道不是這樣?
十九世紀末,色彩基本上是一種黑白問題,因為當時的攝影化學藥劑對光譜顏色還不夠敏感,某些色度的紅色和藍色看起來都是同樣的深黑色。到了1900年,這些難題已大致克服了:日益精密的黑白色調變化讓色域能夠被完全地辨識。(不過,即便到了1929年,其精細程度還是無法滿足紅鬍子的勞倫斯:「看看我兩天前拍的護照照片,」他抱怨道:「這親切的傢伙留著我從沒留過的黑鬍子。」)不過,色調的限制也有它的好處。1916年夏天,史川德在雙子湖拿陶器和水果進行攝影實驗時,他發現當時使用的正色片會把任何帶紅色的東西都顯影成黑色。當時他正試圖把尋常物件拍成抽象造型,這反而有助於去除物件給人的熟悉感,強迫觀看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被創造出來的圖案和形式,而非它們是由什麼創造出來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唯一不能用來界定柳橙的方式,就是看它的顏色是不是橙色。在一張史川德的靜物照中,柳橙和香蕉的「顏色」一模一樣,毫無差別,都是一種深黑色。
多重反諷和一個堅定不移的邏輯在此緊緊糾纏。隔年,史川德將宣稱,攝影最重要的特質是它「絕對且毫無保留的客觀性」。他如此確定,因為他對這項媒介進行了嚴謹的實驗。這般堅持己見是他研究繪畫的直接成果,尤其是塞尚的繪畫,塞尚已達到里爾克所謂的「無限的客觀性」,能「單純用顏色將柳橙」再現。而史川德毫無保留的客觀性,恰恰相反,是拜攝影技術沒有能力區分顏色所賜。
在史川德進行這些實驗的時候,一些彩色顯影技術已研發上市。(中略……)史蒂格利茲、史泰欽、柯本和法蘭克.尤金(Frank Eugene),都捲入這波「彩色熱潮」。史泰欽率先於1908年4月號的《攝影作品》中刊出三張他的奧托克羅姆彩色照片,趕在史蒂格利茲對彩色照片失去興趣之前。至於歐洲和美國的其他攝影師,則是繼續運用奧托克羅姆和其他彩色顯影技術,像是屈光彩色,直到1930年代。1936年,舉世聞名的柯達彩色底片上市,但這項耗費巨資的科學研究與發明,並未撼動黑白照片對攝影作為藝術工作的影響力。
史川德以一貫的嚴苛態度反對色彩。「那是染料。它不具備顏料的稠度、肌理或密度。目前為止,它根本無法提供任何貢獻,反而為這個原本就很難控制的媒介徒增一項無法控制的元素。」到了1961年,彩色攝影的技術限制已得到全面克服,但這卻更加強化一個信念,其中法蘭克說得最為出色:「黑白就是攝影的色彩。對我而言,它們象徵了支配人類的希望與絕望。」對卡提耶─布列松這位善於掌握偶然構圖的大師來說,組織一團混亂的現實已經夠複雜了──「試想,除此之外,你還得把色彩考慮進去。」1969年,艾凡斯對彩色攝影發表了著名的看法:「彩色會腐化攝影,絕對的彩色,絕對的腐化⋯⋯關於彩色攝影,人們只需口耳相傳八個字:彩色攝影是粗俗的。」幾年後,艾凡斯會得到一臺拍立得相機,並用他的餘生津津有味、不遺餘力地探索它的創作潛能。「矛盾是我的習慣,」他說。「現在,我將投注全心發展我的彩色作品。」
那時,有些美國攝影師不僅拍彩色照片,還開始重新思考攝影應有的面貌。班雅明曾如此形容攝影的起源:「這項發明的時機已成熟,而且不只一人感受到這點──那些為了相同目標各自獨立奮鬥的人們就是明證。」這段話也適用於1970年代初期,彩色攝影的興起。史丹菲特就是這些人之一,他把這段時期比喻成「彩色攝影的基督教初創時期」,少數的轉換信仰者會聚在一起,討論他們新創立的顛覆信仰。這項信仰在1976年5月紐約現代美術館舉行伊格斯頓攝影展時,得到了正式的認可。蘭格坦承,「熱帶地區,或許也包括亞洲,無法用黑白底片拍攝。」美國精神還是應該繼續用黑白底片拍攝,但從現在開始,美國各州──尤其是南部各州,因為熾烈陽光和滂沱大雨,也該擁有近似熱帶的明亮。「由電子藍、喧鬧紅和毒藥綠所組成的咆勃爵士(bebop)」曾為艾凡斯所駁斥,如今卻已成為美國攝影調色盤最重要的色彩。1966到1974年間,伊格斯頓拍了一張照片,取名為《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這張照片以廣告招牌的形式展現了他從攝影傳統(尤其是艾凡斯)得到的恩澤,以及他的創新能力。那是一張從路邊小吃店拿的手寫飲料菜單,以大特寫的方式呈現。飲料口味清單簡直就像一張顏色表,可作為美國色彩分類學的標題:
草莓
藍莓葡萄
巧克力綠薄荷
花蜜
柳橙
野莓⋯⋯
最後一項幾乎帶著某種宣告的意圖:
彩虹
如果說這裡面有某種文盲的詩意(strawberry﹝草莓﹞拼成starwbery,chocolate﹝巧克力﹞拼成choclate),那麼它也展現出一種粗俗美感。艾凡斯本人深知這點。其實他譴責色彩的著名宣言,後面還有一段較少被引用的內容:「當粗俗本身變成照片的重點時⋯⋯那麼只有彩色軟片才適用。」說句不好聽的,伊格斯頓1976年的展覽證明了,在高超技術和精細美學的加持下,粗俗也可以很美麗。粗俗就和美一樣,都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略……)
伊格斯頓的照片不僅將生活的平庸必然如實呈現,同時也解決了長久以來占據攝影師思緒的問題。韋斯頓曾在1946年攝影生涯即將結束之際,以極富先見之明的眼界表達過這點,當時他被說服,決定用柯達彩色底片拍攝海狼岬(Point Lobos)。一開始,韋斯頓態度保留。雖然他對海狼岬的了解「勝過還活著的任何人」,但他「不懂彩色」。不過他並未墨守成規;不僅沒就此放棄,還努力改變自己厭惡彩色的習慣:「對色彩的偏見,是出於不把色彩想像成一種形式。你可以用色彩訴說黑與白無法訴說的事。」他曬印了一些照片,並「像個業餘愛好者看著他的第一批沖洗照片」那樣盯著成果瞧──「老天,它們洗出來了!」從那一刻起,韋斯頓就確定他「喜歡彩色」。他比所有攝影師更了解柳橙並非唯一的水果,但他也敏銳地意識到它們──也就是色彩──所帶來的特殊問題。「我們這些一開始用黑白底片拍照的人,耗費好多年的光陰試著避開那些因為色彩而讓人感到興奮的主題;如今換了這種新媒介,我們勢必得為了它們的色彩去尋找主題。我們必須把色彩視為形式,避開只能為黑白『添上色彩』的主題。」
彩色攝影的另一位先驅邁爾羅維茨,曾經用大片幅相機在位於普羅文斯頓(Provincetown)鱈岬(Cape Cod)的海灘小屋拍了一些照片,比較彩色照片和上了色彩的黑白照片之間的差別。這些作品後來集結成《岬光》(Cape Light, 1978)一書,其中有兩張照片和這裡的脈絡特別有關。第一張是一道尖角狀的白色籬笆,籠罩在藍天與低垂的雲朵下方(彩圖3)。籬笆有一部分閃耀著陽光,但大半覆蓋在陰影之中。我們可以把這張照片當作重新拍攝史川德經典黑白照的嘗試,而且不是用染的(套用史川德的說法),而是用彩色。透過籬笆間的縫隙,可以瞥見籬笆後的乾枯草地和綠樹,也就是說,可以瞥見超出黑白照構圖需求的世界。邁爾羅維茨藉由從背後拍攝籬笆的手法──和史川德籬笆的拍攝方向剛好相反──向世人宣告,對於攝影是什麼,如今已有另一種觀看方式。
該書後來的增訂版收錄一張新照片,把這點表現得更為明確,那是一張散放在摺起的《紐約時報》上的蜜桃靜照,它們染著夕陽的色彩(彩圖4)。報紙擱在門廊的桌子上,拍攝地點很可能就是邁爾羅維茨的小屋。1916年,史川德在早期抽象階段,也曾於雙子湖小屋的門廊上拍過陶器和水果,讓角度銳利的影子畫過桌面紋理。在邁爾羅維茨這張照片中,報紙刊登了一張塞尚水果靜物的副本,換句話說,就是一張黑白照片。
邁爾羅維茨從1962年起開始用彩色底片拍照。他在1970年代初完成的街拍作品,充斥著「溫諾格蘭式」的活力和「勁道」(thrust),但在鱈岬這個「都是單層樓房的地方」所拍的照片,卻散發緩慢而著重形式的氣息。當時令他著迷的東西,是另一名彩色先驅蕭爾所謂的「光之色彩」。對札考斯基而言,在這群探索色彩潛力的攝影師中,伊格斯頓的重要性(他是受到邁爾羅維茨作
品的影響,才下定決心從黑白攝影「改信」彩色照相)在於,他的形式和經驗是一致的。札考斯基在伊格斯頓1976年展覽圖冊的序言中,認為伊格斯頓所屬的那類攝影師:
不是把色彩當成一個獨立的議題,一個需要單獨解決的問題(不是用七十年前攝影師思考構圖的方式來思考色彩),而認為這世界本身就是以彩色的狀態存在,就像藍色與天空根本是同一件事。艾利歐.波特(Eliot Porter)最好的風景照,就和萊薇特、邁爾羅維茨、蕭爾等人最好的街拍照一樣,都是把色彩視為存在性與描述性的元素,這些照片拍的不是色彩,也不是形狀、紋理、物件、象徵或事件,它們拍的是經驗,是經驗在相機所加諸的結構中被整理和闡明過的模樣。
對韋斯頓而言,之所以要拍柳橙是因為柳橙的橙性(就像他的黑白照片,拍青椒是因為青椒的青椒性)。然而,伊格斯頓拍柳橙,是因為柳橙是這世界的一部分,而這世界就像札考斯基所提醒的,是彩色的。它也可以是一瓶番茄醬或一塊肥皂。事實上,這一粒柳橙就代表了全世界。只有在黑白世界裡,柳橙的橙色裡才會是一個議題。一旦伊格斯頓「真正學會用彩色觀看」之後,柳橙就失去了特殊地位,充其量只是另一種水果。伊格斯頓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現他想尋找的東西,而其中最特別的,莫過於當它們被大量製造的時候。1989年他在南非川斯瓦(Transvaal)拍了一系列照片,在一家商店櫥窗裡,數量驚人的柳橙快速通過某種分類機器,好像照片從沖印機裡源源流出一樣。這些還沒成熟的「柳橙」保有他作品中常見把熟悉事物變陌生的陌生特質,其中有很多根本是綠的。
我不是第一位從波赫士(Borges)筆下「某本中國百科全書」裡尋求靈感的研究者。根據這本神祕奇書,「動物可以分成:(一)屬於皇帝的;(二) 充滿香氣的;(三)受過訓練的;(四)乳豬;(五)美人魚;(六)傳說中的;(七)流浪狗;(八)包含在這個分類裡的;(九)發瘋似不停顫抖的;(十)多到數不清的;(十一)用很細的駱駝毛毛筆畫出來的;(十二)等等;(十三)剛剛把花瓶打破的;(十四)遠看很像蒼蠅的。」
雖然本書所進行的攝影調查,就嚴謹和古怪程度都不能與之相比,但在前人立意良善做法的鼓舞下,本書嘗試將攝影的無窮...
目錄
插圖列表
然而,很美(吳明益,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持續進行的瞬間
注釋
參考書目
攝影師年表
致謝
插圖列表
然而,很美(吳明益,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持續進行的瞬間
注釋
參考書目
攝影師年表
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