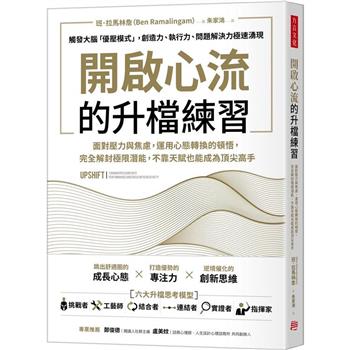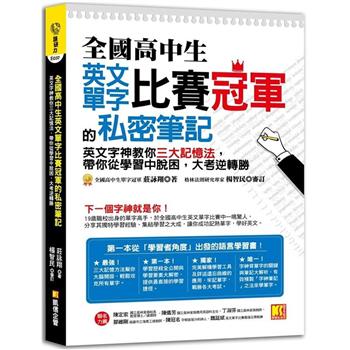推薦序
流浪,讓人發現自己
嚴長壽
在一個作夢都沒想過的人生際遇中,我在出社會沒幾年就實現了以職業領隊的身分出國旅行的機會,如今想來我絕大部分的人生學習大多與旅行有關,也因此更希望鼓勵年輕人能夠為了實現自己的夢,勇敢的走出去,好的經驗是學習,壞的經驗也是學習。好壞冷暖之間,點滴自在心頭。
對我而言,流浪是一件奢侈而浪漫的事。朝五晚九的工作,忙得沒有時間度假的行程安排,怎得空閒流浪?如果說流浪是一種心境上的放空、眼界上的刺激,或許我那大大小小的旅行經驗差堪比擬。在一次次的旅行中,藉由與國際友人的接觸以及親身體驗異國的文化與風情,似乎總在與異己的對照中,發現自我更為內在不易察覺的部分。或許旅行與流浪一樣,最終都是一種自我追尋的過程。
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之下,年輕人未經世事就已世故老成,他們或許不清楚真正的方向與內在的渴望在哪,就早已在世俗與他人所期待的道路上循序漸進。「無災無難到公卿」或許是一種無知的幸福,但總有一天,當陷入孤獨、無助之境,被迫重新審視最內裡的自己之時,或者手足無措、或者退縮逃避。看著書中幾位年輕的創作者,及早發現教育體制所給予個人的不足之處,無寧使流浪這件事,更顯出非凡的意義。
感謝懷民的發起,我深信,無論年輕人選擇去奉獻,去挑戰,或者只是去放空自己,「雲門流浪者計畫」將會是台灣年輕人最重要的生命推手。流浪,讓人發現自己。
推薦序
看到台灣的另一種力量
施振榮
「流浪者計畫」緣起於二○○四年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老師榮獲行政院文化獎,當時林老師為了鼓勵年輕的藝術家勇於「出走」,到海外實踐自己的夢想,於是將獎金捐贈給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成立了「流浪者計畫」,資助這些年輕人去海外流浪。
從第一屆來申請「流浪者計畫」的年輕人身上,我看到了他們追求夢想的勇氣與執著,也對於他們勇敢「出走」到一個陌生的國度去實現夢想感到佩服,這些年輕人在極度有限的資源下流浪,體驗完全不同的人生經驗,並在汲取經驗後回到台灣,更有自信地繼續實現夢想,讓人看到台灣的另一種力量。
基於認同「流浪者計畫」的理念,我所捐贈成立的智榮文教基金會決定自第二屆開始長期贊助「流浪者計畫」,希望能繼續林老師的理想,並鼓勵及協助更多年輕人有機會到海外去流浪,我也相信這些年輕朋友在海外學習成長後,在回到台灣後將會挹注更多的力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此次「趁著年輕去流浪」書中訪問了九位曾經參與「流浪者計畫」到海外流浪的年輕人,分享他們的流浪經驗,每位流浪者的流浪經驗或許不盡相同,不過由他們分享的故事中,都可以令人深刻感受到出走,原來反而是要去找到生命最初的原點,在流浪的過程中,逐步找回內心的自我。
其實「流浪」是需要勇氣的,在我印象中,我第一次離家去「流浪」,是在高中的時候,當時我以準備大學聯考到台北補習為名,母親也充分地信任我,就讓我獨自一人到台北,那時我還去看了四國五強籃球賽及亞洲鐵人楊傳廣,還到台北圓山的兒童樂園去玩,前後流浪了一個多月,且這次的獨特經驗一直很深刻地留在心中。
我相信有機會參與「流浪者計畫」的年輕朋友,這樣的流浪經驗對其一生的影響,也將是段刻骨銘心的回憶,從勇敢出走,一個人獨自到陌生的地方流浪,去學習新的事務,可能是這一輩子原本都沒機會去做的事情,過程中也可能充滿不確定、孤獨、挫折與挑戰,只為實現年輕時的一個夢想,而義無反顧地去流浪。
我相信在台灣有許多對未來充滿夢想與期待的年輕人,我也希望藉由這個計畫,可以繼續幫助更多有夢想的年輕人,勇敢踏出這一步,勇於實現自己的夢想……
前言
出走與回家
林懷民
一九六九年九月,我初到美國讀書。在舊金山機場看到通往全球的航班表:紐約、倫敦、巴黎、東京、阿姆斯特丹、莫斯科、斯德哥爾摩……
那是個驚嚇的啟蒙經驗。世界如在眼前,地理課本的地名,原來是真的可以去的城市!
那年五月,搖滾樂、大麻、性愛,五十萬人大聚會的伍茲塔克音樂節,震動了全球的年輕人,而我來自戒嚴的台灣。一年多以前,巴黎、東京、紐約、柏克萊,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在台北,我衷心崇拜、曾在明星咖啡廳仰望的作家陳映真被警總抓走,寫作圈子的朋友私下轉告,不知所措,也有人徹底避談。
可以這麼說,到了美國,我才開始走進世界。
七○年聖誕假期,我從讀書的艾荷華,一路候補機位,用學生票旅行,混到西岸。忘了如何抵達太平洋高速公路的一個水族館。我第一次看到海豚,樂得張開了嘴巴。
看完海豚戲球,我對著太平洋的落日發呆,轉頭才發現人全走光了。到了館外,停車場是空的,也沒公車了。天色昏沉,我只能在路邊橫著大姆指等便車。
一位長髮嬉皮讓我上他的車。弄清楚我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不知要往何處去,便安靜地說:「那麼,到我家過一夜吧。」
睡到半夜起來上廁所,只見起居室五六個長髮男女安靜坐著,看了我一眼,沒說話。房間裡有印度線香的味道,也許都吸了大麻,一屋寂靜。我回房繼續睡。第二天早上,另一個長髮嬉皮順路把我在公路邊放下。我橫起大姆指等車。
七二年,我打工存了錢,經歐陸返台。紐約到盧森堡的學生包機每人九十美元。在阿姆斯特丹,我根據手上的「每天十元遊歐洲」,找青年旅館過夜,也睡過公園,認識了人就一起去玩。
有一個人要去巴黎,我改了行程和他同行。他找到幾個朋友,一起混了幾天。吃飯,大家湊錢買幾條麵包,幾瓶便宜紅酒就打發了一頓。這些來自各國的背包族,有人初抵巴黎,也有人要離去,大夥兒就在便宜小酒館為隔日要啟程的朋友送行。喝得太晚,第二天爬不起來,誤了車程,因此晚上再度送行,喝到凌晨……
在巴黎認識的瑞士青年要去葡萄牙、西班牙,邀我同行。到了葛那達,他要去摩洛哥,我的中華民國護照要等上一個多月才能取得簽證。從此我一人獨行,去義大利和希臘。
在羅浮宮、在烏菲茲美術館我第一次感覺到「顏色」。從希臘的天空和愛琴海,我終於知曉藍色有無限的層次和變調。在日內瓦,我看到一本美麗的畫冊,那是我第一次認識敦煌壁畫。
通往曼谷的學生班機由雅典起飛。才走進世界,又得回到窒息戒嚴的台灣;觀光尚未開放,一般人收入極少,我不覺得自己還有機會出國,躲到廁所狠狠哭了一場。
沒想到我竟然一次又一次出國,頻繁的程度使我想起機場和坐飛機就要自閉地憂鬱起來。跟雲門出國是工作;十次九次,演完第二天必須離開;沒有主辦單位可以大方地讓三四十個人不演出,住旅館。
一九八八到九一年,雲門暫停的三年,我隨心所欲地跑來跑去。背起包包,住十元美金的民宿,我去了印尼、菲律賓、尼泊爾和印度。
印度!許多人怕去印度,因為髒亂和貧窮,因為火車飛機從不準時。這些,正是讓我一再回到印度的理由。生了兩回氣後,我有了「頓悟」:即使慢上七八小時,火車一定會來。我放心地在火車站讀了一本又一本平日沒時間讀的書。人生可以不必急吧,我終於擺脫時程表!
印度的燥熱飛塵,天天在街頭上演的生老病死,為我曉示生命的本質。我也去過恆河畔,看到骨灰灑入河中,焚燒一半的殘屍逐波而下,下游的印度信徒面不改色地掬起「聖水」,仰頭吞下。生死有界,流水無痕。我驚悸而感動。
不知不覺,去了九次印度。印度安頓了我。毛躁起來時,閉眼想起聖牛踱步的火車站月台,流水悠悠的恆河,心就靜定一點。我開始覺得雲門的工作不是磨難。得失心淡了以後,作品慢慢成熟。
一次次的出走,孤獨的背包旅行,讓我看到許多山川和臉孔,見識到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背後共通的人性。旅行為我打開一扇扇門。回了家,我閱讀,追尋曾經碰觸過的文化,關心去過的國家,遠地的戰爭彷彿也與我有關。更重要的是:離開台灣,隔了時空的距離,台灣,還有在台灣的自己,變得特別的清明,因而逐漸培養出對付自己的能力。
台灣解嚴二十多年,但是,我們仍然容易陷入島國的自閉,陷入消費主義的迷障。我懷念六七十年代年輕人沒有特定目的的貧窮旅行。我希望有更多年輕人出走。
二○○四年,我把行政院文化獎的六十萬獎金捐出來,成立「雲門流浪者計畫」,承蒙許多朋友,特別是施振榮先生和他的夫人葉紫華女士,以及吳清友先生、嚴長壽先生,熱心支持,使這個計劃可以持續進行。五年間,四十一位年輕朋友在「流浪者」的獎助下到亞洲各國學習,去奉獻,去挑戰自己,或者,只是去放空。
台灣受了太多西方影響,對於近鄰的亞洲文化缺乏認識,我們希望年輕朋友去紐約、巴黎之前,先到亞洲看看。我們要求流浪者單獨旅行:一個人走才能增加與當地人互動,確保和自己對話的機會。我們也期待旅行的時間不低於兩個月:希望他們可以完成緊張、興奮、疲累、挫折與重建的幾個階段才回家。
常有人問,對「流浪者」有什麼期待。我們祝福他們帶著新的視野,以及對自己的新觀點,重返台灣的生活。如此而已。
然而,事情的發展讓人喜出望外:
第一屆的謝旺霖書寫鐵騎西藏高原的《轉山》成為二○○八年誠品中文書籍排行榜第二名的暢銷書;簡體版在大陸「火紅」。
吳欣澤透過演奏與CD,以西塔琴豐富台北的音樂文化。
劉亮延的「李清照私人劇團」新作不斷,令人驚豔。
鍾權的紀錄片在公視、在大陸播放。
吳耿禎的現代剪紙這兩年來,成為台北眼亮的風景。
薛常慧的伊朗之旅,促成台灣與伊朗紀錄片的交流。
楊蕙慈去廣西學蠟染,回來發願募款,要為當地瑤族孤兒蓋一所小學。
盧銘世持續在全國推廣種樹,綠化台灣……
「流浪者」的旅行只是他們生命的逗點,沒有這趟旅行,他們的才華與熱情一樣會燦爛開花,但因為有過這番交會,我們沾染了年輕朋友圓夢的喜悅,也以他們的成就為傲。
二○○八年,雲門穿針引線,七位「流浪者」到四十所學校,分享他們旅行的經驗,參與的學生高達兩萬五千人。有些學校因而企劃了「小小流浪者計畫」,鼓勵學生進行島內自助旅行。二○○九年,十位「流浪者」接棒,到七十所學校演說,繼續擴大青少年的視野。
年輕人逐夢的勇氣,落實夢想的毅力,是社會進步重要的本錢。而告別年輕多年的我,因為這個計畫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勵。工作膠著苦悶之際,遙想張子午騎著自行車穿越哈薩克、俄羅斯、土耳其,直至葡萄牙大西洋海邊;林乙華到尼泊爾參加喜馬拉雅山登山訓練;陳乃綺辭去台大醫院研究員工作,「捐出」八個月,到柬埔寨和寮國,參加當地登革熱的衛教、防疫的活動;輔導台北遊民多年的楊運生在日本深入觀摩遊民輔導機構的運作;我的世界變得寬闊,對自己的沮喪感到可恥,因而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聖經》裡,浪子的故事以落魄的浪子回家,得到父親寬容的擁抱作結。紀德的〈浪子回家記〉顛覆了《聖經》的道德教訓:回家的浪子,幫助弟弟離家出走。
出走。回家。再出走。我希望看到一代代人不斷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