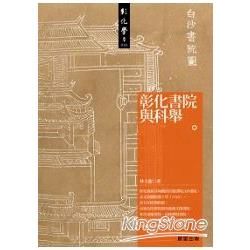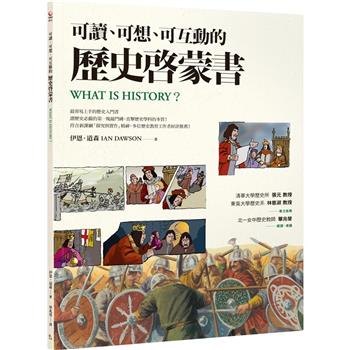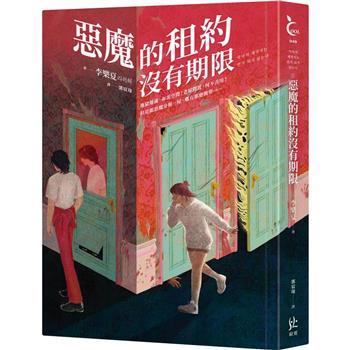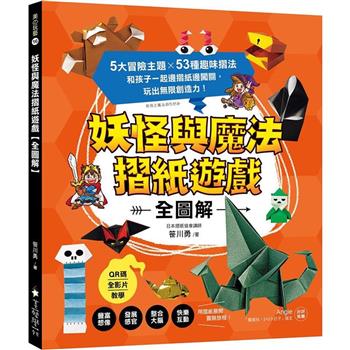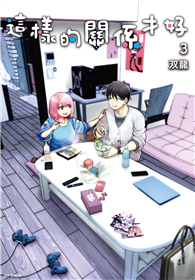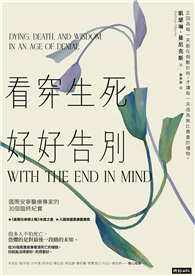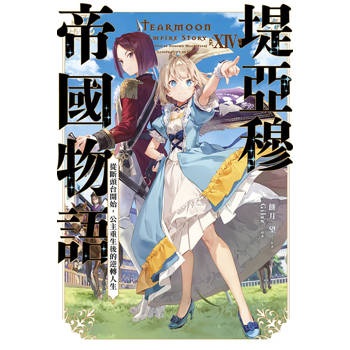自序
政府用人唯才,甄拔才俊之士,使其發揮所學,貢獻國家社會,透過選舉機制,是不二法門。歷代修纂地方志書,例有「選舉志」一門,內容悉屬科舉考試變革,以及科貢人物總表,以是往往令人產生錯覺,誤認為選舉等同於科舉,其實科舉不過是眾多的選舉方式之一,他如察舉、徵召,也都屬於選舉範疇,乃至官吏的選拔、任用與考核,亦可概括為廣義的選舉。
朝廷設科取士,考試不失為最公允的制度,即使是備受批評的以八股、試帖規範應試文字,其出發點也是出自公平性的考量,設定格式,俾儒士有所遵循,而試官閱卷也有取捨標準。窮經致用,為天下讀書人奮鬥目標,科舉考試正是跨越仕途的重要門檻,因此書院教育應運而生;科舉肇端於隋朝,書院則出現於唐代,從此成為培育科舉人才搖籃,與科舉制度相輔相成,歷經千餘年不衰。
光緒三十年甲辰科,為一千三百餘年的科舉考試劃下了休止符,自是應試的制藝時文,成為無用之物;影響所及,書院功能也隨之而式微,荒廢者有之,移充他用者有之,轉型者有之,情況不一而足。這種情形,在臺灣則提早了十年,光緒二十年的甲午恩科,為臺灣各學舉子參與科舉考試的最後一科。翌年臺灣割讓日本,迫使科舉提早結束,不過不少儒生內渡,寄籍閩粵各學,參與甲乙兩科考試,取得舉人、進士以及翰林等功名。臺灣的科舉考試,在明鄭時代因有「全臺首學」的創設,乍現曙光,但止於取進生員階段,正式開科取士,為康熙26年丁卯科鄉試,遲於清人入關之初的順治3年丙戌科達三十餘年,實為科舉史上的「異數」。
為了紀錄臺灣科舉制度下的書院經營,我曾經寫過《臺灣的書院與科舉》一書,交由常民文化公司出版,以淺顯文字,細數臺灣書院與科舉相關制度、人物掌故,以及民俗、遺跡。本書的發行,使年輕一輩,重新認識科舉與書院制度,某些殘留民俗也能藉此而追溯,找到源頭。有位朋友讀過書後曾告訴我:「以前讀過某專家的論叢,資料詳瞻博引,不過終篇仍不知所云,但讀了你的書,很快便弄清楚原委。」有此肯定,殊堪告慰!只是書中有幾個關鍵性誤植文字,沒有機會更正或製作刊誤表,不無憾焉!
好幾年前,在彰化縣某個文學會議的場合,得知林明德院長、康原兄正在進行「彰化學叢書」編印計畫。鑒於彰化縣為臺灣現存書院古蹟最多的縣份,叢書中應有一席之地,邀我為這項計畫寫一本《彰化的書院與科舉》。當時公私兩忙,參與的鄉鎮志正在進行,館內的特展也在策劃,不敢貿然答應;康原兄一再勸說,道是時間不趕,基礎已經打好,只要稍作刪補便能成書,剛好常民的合約已滿,就勉為其難接受了這個任務。
時間逐漸流逝,面對舊稿,茫然毫無頭緒,原因是抽出了非彰化部分,篇幅便嚴重不足,以致遲遲未能動筆。而康兄催稿殷勤,不僅密集電話催促,凡有見面機會,也不放過。而我一再因循,幾度想放棄,有天永靖張瑞和兄寄贈其大作《維繫傳統文化命脈 : 員林興賢書院與吟社》,彰化學叢書之一,心想現存彰化三所書院之一已完稿其一,我的彰化書院正好趁此良機做個逃兵。去年春夏之交,仍是彰化縣文化局的會議場合,將打退堂鼓的念頭告知兩位;哪知得到的答覆是:彰化書院的書還是要出,交稿時間可以延到暑假之後。眼看無法置身事外,只能積極安排撰寫章節了。
彰化縣境內現存書院只有文開、興賢、道東,篇幅顯然不足,於是將範圍擴大,先從「彰化歷史書院」著墨,追溯正音、白沙、主靜、螺青等,再殿以「彰化書院延伸」,及於今南投縣境的藍田、登瀛兩所,總共九所書院,成為本書的骨幹。書院與科舉密不可分,於是再就科舉部分擇要敘述,制度、民俗、人物之外,並及於書房、社學、詩文社等,大抵以彰化為主,不過因考量資料完整,仍有部分例外。數月辛勤,終底於成。彰化素稱人文淵藪,科甲雄冠全臺,見微知著,本書正堪相與印證。至於疏漏謬誤,或諮訪未周,敬請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林文龍謹序於臺灣文獻館
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