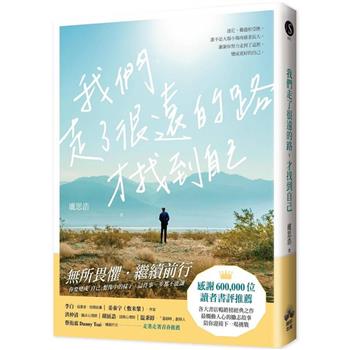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井月澎湖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10 |
小說 |
電子書 |
$ 210 |
華文創作 |
電子書 |
$ 210 |
文學小說 |
$ 225 |
小說/文學 |
$ 237 |
小說 |
$ 237 |
中文現代文學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小說 |
$ 270 |
中文現代文學 |
$ 270 |
小說 |
$ 27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井月澎湖
西元1895年,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割臺、澎與日。時代動盪決定小人物的悲劇命運,澎湖許、李兩家族的興衰糾葛見證浮亂的時代苦況。作者藉人物李蓮子敘述兩家族的悲歡喜怨;從世代的遞嬗、時勢的流變道盡人世興衰及人性轉變。其間有切實動人歷史之真、溫柔敦厚親情之善及樸實精緻台語之美!寫時代也寫人性,寫家族也寫個人成長,是一部值得再三品味的台灣小說!
●台語的使用落實於現實生活中,這本小說有高度的本土性和真實性,是相當傑出的小說!
──葉石濤
●台灣人在大中國主義的教科書中很容易學到歷史,卻學不來歷史的真確。井月澎湖是作者身為澎湖人所寫的澎湖事,是小說也是歷史。
──王家祥
●為讓更多族群英文人士瞭解台、澎歷史,特將《井月澎湖》翻譯成英文,2011年於美國 Xlibris出版 Penghu Moon in the Well。
──李秀
本書特色
井月澎湖是以澎湖家族興衰為著墨點的真實小說,此書出版後榮獲吳濁流文學獎、高雄文藝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