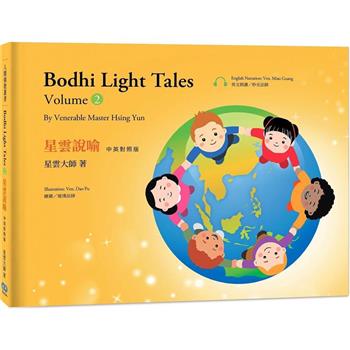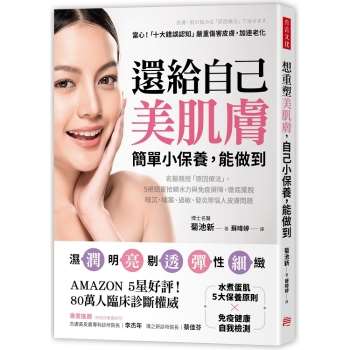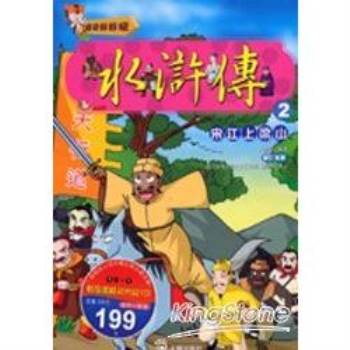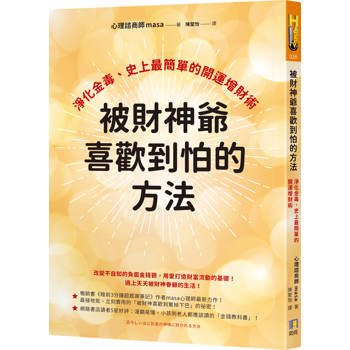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夢幻巴士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夢幻巴士
一趟地獄住客的天堂之旅
地獄的大門是由內鎖上的,
我們若執意保有地獄,必定見不到天堂。
發現自己身在地獄,等待著搭上駛往天堂的巴士。
想留在天堂的人將可留在天堂,這是一個神奇的機會,
卻開啟了在善與惡、恩典與審判之間的奇特冥想。
「假若機智和智慧、風格和學識是通過那扇珠白色大門的必要條件,那麼路易斯先生會是天使之一。」
——《紐約客》(The New Yorker)
「對於半信半疑的人,對於想成為基督徒、卻又發現自己才智不足的好人來說,路易斯是最完美的說服者。」
——《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路易斯或許比二十世紀的其他作家更能迫使他的傾聽者和讀者接受自己在哲理上的假設。」
——《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