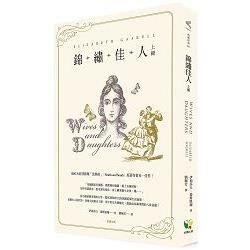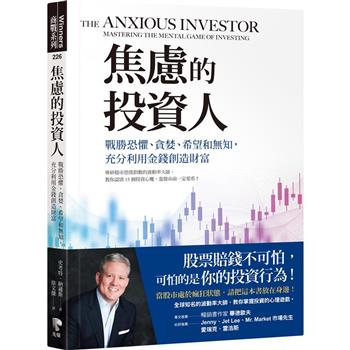情韻雋永如《曼斯菲爾德莊園》,溫暖詼諧如《唐頓莊園》,
揭述英國鄉間風物,莊園魅力全開!
揭述英國鄉間風物,莊園魅力全開!
★ BBC大好評影集「北與南」(North and South)原著作者 蓋斯凱爾夫人 另一佳作!
「從前某個國家有個郡,那郡裡有個鎮,鎮上有棟房屋,
屋中有間臥室,臥室裡有張床。床上躺著個小女孩,她……」
從小鎮姑娘茉莉的日常,窺見1830年代的英國莊園生活面貌。
伯爵夫人的打扮、老地主的排水工程、青年男女共舞幾次,都能成為鄰里間的八卦話題!
茉莉‧吉布森,何陵福特在地醫生的獨生女,從小失去母親,最期待的就是鎮上熱鬧的慶典集會,那天難得前去伯爵宅邸,硬生生被遺忘在貴族世界角落,留下了不甚愉快的童年回憶。
數年過去,少女茉莉的生活原本很單純,除了照顧忙碌行醫的父親,就是到鄰居家串串門子,漫遊鄉間小路。直到某天差點被跟著父親學醫的青年示愛,由此掀起了一陣陣波瀾。親愛的爸爸為幫女兒趕蒼蠅,不僅將她送往地主漢利家暫住,還打算再婚為茉莉帶來新媽媽當保護人。
茉莉與漢利家日漸熟稔,與纖細的奧斯朋和樸直的羅傑兩兄弟情若兄妹,還不小心聽到這家子最重大的祕密!而美麗的繼姊辛西雅從法國返歸家鄉,儘管讓茉莉多了個閨密友伴,卻也為她的感情之路增添變數。到底茉莉能否抓住夢想中的幸福呢,英國錦繡佳人的故事即將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