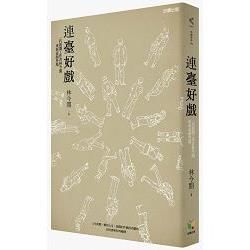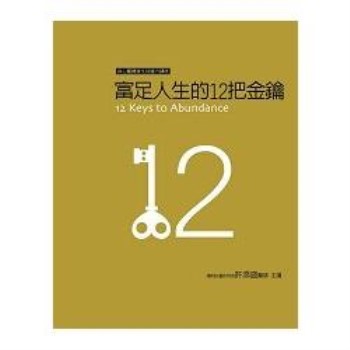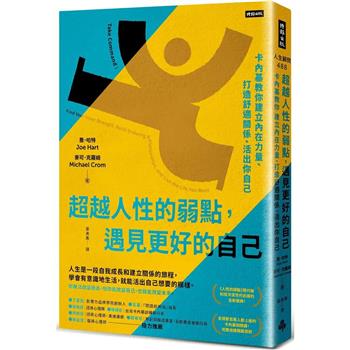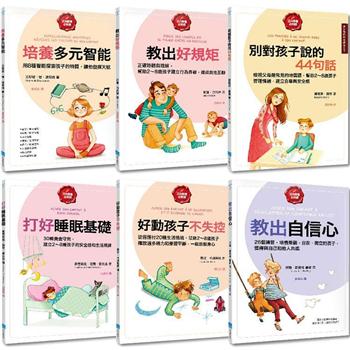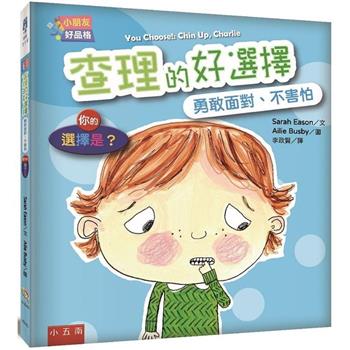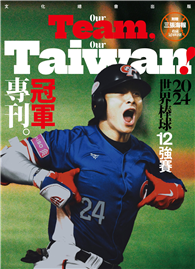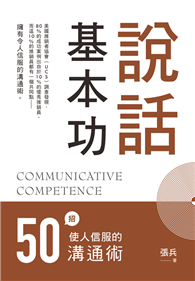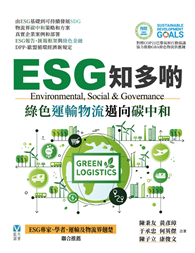推薦序 1
《連臺好戲》──讓我更以記者工作為傲
文/詹怡宜
這幾年記者這個行業的負評越來越多,我總是很不甘心。拜讀林今開前輩的《連臺好戲》,那種不甘心的記者魂又被召喚出來。不是跑新聞要跑出獨家來證明自己的那種熱情,是一種想認真把「成為好記者」作為一生志業的尊貴記者魂。一篇篇高度真實的故事提醒我,記者有以下幾個特質,不因時空改變:
記者是有趣的人。有趣的人是對事情總有高度興趣的人,對生活感到好奇才會積極發問,問對問題才能得到好答案和好故事。我對林今開先生描寫的糧食局長李連春的故事讚嘆不已。特別是從一張〈包龍眼的紙〉窮追不捨,推敲出一九五一年一幕臺北松山機場傳奇見聞的過程,若非本身是好奇有趣之人不可能做到。
記者是富正義感的人。通常因使命感而來的傻勁的確讓記者們願意不眠不休,但林今開先生的〈黑驢子之夢〉把他自己使命感的由來說得格外具體。「當年為了討叔叔喜歡,曾放過田邊的一批黑驢子,作踐的只是幾根稻穗而已,今天,我如果再聽從『叔叔們』的話,放任社會上的『黑驢子』,受作踐的就不再只是幾根稻子了。」我們記者的工作總是不斷在面對社會上的鄉愿「叔叔們」,勇氣是記者的必要條件。
記者是會說故事的人。既稱故事,不是抽象論述,是從人的生活對話、細微情感、前因後果的具體描述,給人身歷其境的時空錯覺。唯有對生命經驗感興趣、懂得生活且能設身處地的人,才能把故事說得觸動人心。而且他的文字中「故事」多於「意見」,證明他一直是記者,沒有成為名嘴。
佩服這位有著尊貴記者魂與精采生活的前輩,《連臺好戲》讓我更以記者工作為傲。
推薦序 2
新聞記者眼中的浮世繪
文/王御風
如果要說有哪一種職業,可以增廣見聞、拓展人脈,加上鍛鍊文筆,那應該就是新聞記者。
當新聞記者,必須要交遊廣闊,這樣才有源源不絕的情報。也必須要樣樣「懂一點」,否則無法與採訪者暢所欲言。這些特點,都在新聞前輩林今開的《連臺好戲》中展現無遺。林今開的書中,可說是橫跨多個領域,題材相當多元,有醫學、有藝術、有糧食、有幫派、有對各國的文化比較,雖說這是林今開用多篇文章串連起一生,也可看到新聞記者閱歷豐富的一面,也是本書的一大特點。
但閱歷豐富,只是新聞記者的基本條件,一般人很難接觸的大官,對新聞記者來說,也只是個採訪對象,甚至有時候,還是個「諜對諜」的對手。〈李連春的連臺好戲〉一文中,就可看到糧食局長李連春如何與林今開「鬥智」,藉由林今開的筆,幫他解決一些問題。
實際上,在我短短的新聞經驗中,也常發生這種事,大家都以為記者有三頭六臂,可以發現只有「我、當事人及老天知」的弊案,實際上,這往往都是「高級線民」提供的情報,這些局長處長等級的「高級線民」在新聞見報時,SOP模式就是裝無辜,說他不知情,也感到驚訝,回去一定徹查,如有不法,一定查辦。這都是「連臺好戲」,因為要「處理」的人,背景太雄厚,如果公事公辦,必然無疾而終,倒不如訴諸輿論,藉人民力量解決。這種記者與官員的「共生」,在這篇文章中展現無遺。
只是記者何其多,真能脫穎而出,必須要有敏銳的「新聞眼」,在眾人不疑處看到蛛絲馬跡,循線追查,同樣是李連春擔綱主演的〈包龍眼的紙〉也看到林今開的功力,在一張包龍眼的紙中,看到了與平常不同的「異象」,遂展開新聞大追擊,上窮碧落下黃泉,終於找到真正的答案,這種「新聞大追擊」的功力,可以看到林今開的記者魂。
記者魂中除了鍥而不捨外,更重要是追尋「公平正義」,從林今開全書中,可以看到這種精神貫穿全書,〈黑驢子之夢〉更是展露無遺。〈黑驢子之夢〉講的是高雄醫學院院長杜聰明及當時高雄市長陳啟川的一段公案。臺灣首位博士杜聰明當年離開臺大醫學院後,立志要辦一間超越臺大的醫學院,後來拜訪高雄首富家族:陳家的陳啟川,陳啟川慨然捐出土地與金錢,辦了如今我們熟知的高雄醫學院,由杜聰明擔任院長,陳啟川家族掌管董事會,但後來杜聰明與陳啟川鬧翻,董事會要求杜聰明下臺,學生群起抗議,當時陳啟川已是高雄市長,這起「市長」與「院長」對決的事件轟動一時,最後則是杜聰明辭去院長、陳啟川退出董事會,雙雙下臺收場。在這種新聞場合中,新聞記者該如何報導?我們看到林今開在文中迂迴表達他經過深思後,最後決定仗義執言,但不為高層所喜,也被迫離開新聞圈,因此在〈黑驢子之夢〉中,林今開不再提此事件,改以一段寓言來說明他堅持的新聞之道,這也看到新聞記者「說實話」的難處。
既然不能說實話,那就插科打諢。《連臺好戲》中的每個小故事,應該都是林今開本身的經歷及所見所聞,但很多事情不能寫成新聞,只好寫成小說,不管是〈高處不勝寒〉、〈郵差父子〉都是如此,在〈傳家之寶〉中,更藉著老頑童柯傅夫子自道,「我寧願相信小說,而懷疑所有歷史」。
在林今開戲謔的文章背後,其實有更多對人性、「真實」的觀察,讓我們思索,我們看到的新聞,究竟有多少是真實?這應該是林今開輕鬆有趣文字背後,最深刻的反思。
序言
妻之序言──把林今開還給讀者
文/周碧瑟
我認識林今開有十一年,嫁給他也有八年,在最近一年中,他相繼出了兩個集子。這本集子定名為《連臺好戲》,這原是書中一篇名,用之於書名,對書和人都很切題,因為他的一生相當戲劇化,又很能從現實生活中吸取戲劇的素質,而表現在他的散文和小說裡,串連起來讀,真的很像觀看幾場連臺好戲。
林今開的「戲路」著實很廣,連臺角色各有千秋,時間和空間涵蓋也很廣,這顯然跟他大半生從事新聞工作,又兼是個「雜學家」,很有密切的關聯;職業又使他成為徹頭徹尾的寫實主義,因此,他的短篇小說的廣度和真實度都很高。這集子,他不以作品的類別或年代編排,大致按「劇情」發生的年序而輯成。全書各篇我早已熟讀,而且大半由我手抄謄正。如今,輯成集子,從頭到尾讀了一遍,雖然各篇自成單元,互不相干,可是,綜覽整體,倒像是林今開的一本相當完整的自傳,縱使請他認真用傳記體寫一本自傳,恐怕也很難比這集子來得更自傳而更自然。
我是他的第二任老婆,從《連臺好戲》的戲目來看,我是在第十目〈焚稿嫁女報平安——喜帖〉的年代(一九七七年)起,登上了他的「戲臺」。那時我和林今開相識三年,已決心嫁他,只因父母以我這個才廿八歲「臺大醫學院碩士」的女兒,竟然下嫁為人續弦,當人晚娘,堅決反對;我又矢志不改,於是只好慢慢拖著,一直拖到林今開打算嫁女兒,而且女兒似乎有了「訊息」,我才真的著急起來:我再不結婚,恐怕就要當未婚祖母了,於是積極進行我的家庭「婚姻革命」,當時我家人以為我是奉「兒女之命」不能再拖了(其實也對,可不是嗎?),我就將計就計,終於如願以償。一轉眼,我已是兩個小學生的外婆了,大概我是世界上最年輕的祖母。
從嫁女的〈喜帖〉起,我重讀一遍,如同回顧我過去十一年人生旅程的影集。正如已故的前任國立陽明醫學院韓偉院長所言:「今開和碧瑟兩人是一體的。」我和今開是夫妻兼同事,生活的每一環節和景象幾乎完全緊扣重疊在一起。我一直伴著他走,走遍臺灣及世界好多角落,眼看他如何在「大千世界」中捕捉人生的素材,由我替他作筆記,然後帶回巢去,讓他慢慢釀製成文,再由我替他謄正,只一轉手,他又大改特改,我再謄正,每篇文章起碼反覆修改三、四次,甚至於七、八次之多。
在反覆謄改的過程中,個中滋味,唯我知之。最近在電視及廣播訪問節目中,我看到、也聽到幾位年輕名家很得意地自道:他們寫過的文章從不再看第二眼。此輩固屬「天才」,但失去那份跟文字「苦戀」的情趣。我們在王安石先生〈泊船瓜州〉一詩稿中,見得那句「春風又綠江南岸」的「綠」字,起初原用「到」,由「到」而「過」,而「入」,而「滿」……改了十來次,終於選定最貼切的「綠」字,而成此千古佳句。今開無此才情,書中少有佳句,而他勤能補拙,在反覆修正過程中,我也能體味出類如〈泊船瓜州〉詩稿中那種推敲文字的情趣,尤其他的散文和小說,何止是斟句酌字?常在謄正中,突見佈局結構起了變化,此中驚喜之情,只有身為第一讀者的我才欣賞得到。
我人小膽粗,在抄寫今開的草稿時,有時會遇到很拗口的對白或不貼切的字眼,我會忍不住動它兩筆,今開大致同意照改。前幾年,今開收到一封遠自新加坡的老友馮龍雲先生來信說:「近來你的文字大有進步,而且偶爾在某些筆觸中會出現嫂夫人的影子。你的文章就是燒成灰燼,我也辨認得出。」讀了馮先生的信,今開和我無不心服,而且因得「文字知己」而喜不自勝。
兩年前的一個春夜,我正在美國紐奧良市杜蘭大學宿舍中沉睡著,被一陣電話鈴催醒,坐起接聽,那是林今開的三弟金楢遠自印尼雅加達打來的,他先為我當選中華民國第十屆十大傑出女青年而道賀,接著通知我:「今天我匯了一筆學費給妳。」在酣睡初醒,昏昏沉沉中,我對這突如其來的賀辭及贈款,一時不知如何以對,只輕輕說一聲「謝謝」!
「謝什麼?學問是用來服務人群,又不是妳私人的!」金楢此語擲地鏗鏘有聲,比他匯給我那筆學費重得多,在我心中,永烙難忘。因此,使我聯想到「作家原屬讀者的」。在我學成歸國之後,重新調整了我的生活,從今——一九八六年元旦起,也是我認識林今開的第十一年,我盡全力支持他卸下中華民國防癌協會的職務,全然把他交還給讀者,要他做個專業作家,不必再為瑣務而分心。
他確實這樣做了。不料,不出數月,就起了變化。蕭孟能先生為籌備《文星》復刊,跟我倆商量徵召林今開歸隊去。我雖生晚了,未逢《文星》之極盛,但從舊誌中頗為了解這一段光輝的事蹟,如今,今開有機會參與承繼此一使命重大的文化事業,並未違背今年元旦我倆所共同期許「作家還給讀者」的心願。寫序此刻,他已投入新《文星》,謹借此深深為他及所有文星人祝福。
周碧瑟
寫於國立陽明醫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