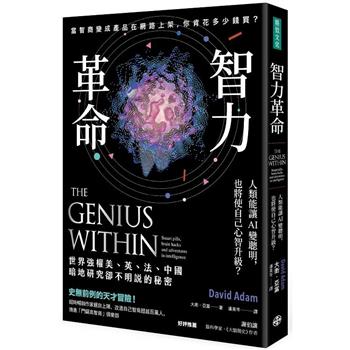一場瑰麗夢幻的神秘海底探險!
多次改編為電影、影集、動畫,暢銷全球經典奇幻小說。
多次改編為電影、影集、動畫,暢銷全球經典奇幻小說。
《海底兩萬里》是儒勒‧凡爾納的巔峰之作,
本書根據法文原版全文翻譯,並收錄由法國插畫家艾德華‧利烏為法文原版繪製的一百多幅插畫。
在這部作品中,他將海洋與人類科技的想像發揮到極致,表現了人類認識和駕馭海洋的信心,其筆下擁有近乎無限潛航能力的潛艇「鸚鵡螺號」更成為之後潛艇的嚮往,至今已有超過十座潛艇被命名為鸚鵡螺號,可見凡爾納此小說的魅力。
「凡爾納到今天仍受到數以百萬的讀者歡迎的原因很簡單,他是有史以來最會說故事的人之一。」──英國科幻小說家亞瑟‧C‧克拉克
「誰能探得深淵之底?」如今世上,只有兩人有資格回答,尼莫船長和我。──《海底兩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