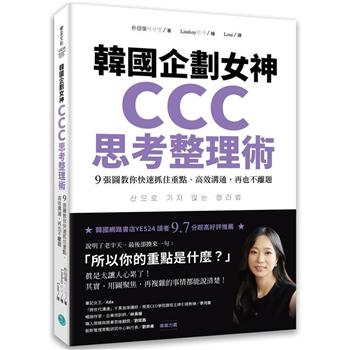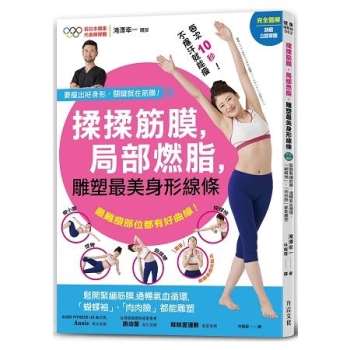《人性枷鎖》,入選英國《衛報》(The Guardian)世界100大最好的小說
《人性枷鎖》,「英國莫泊桑」毛姆自傳體小說,他一生最想寫出來的就是這本
●一部追尋愛、追求人生體驗,以及追索信仰的生命巨作
●愛與被愛,一定要對等嗎?愛與慾望之間有必然的關係嗎?
最懂年輕人的毛姆,把自己的困惑與追尋說給你聽
為什麼有必要看《人性枷鎖》這本寫於1915年的小說?!
‧書寫,以療癒悲苦的成長過程,毛姆在100年前就這麼做了
‧青少年的苦悶、被同儕霸凌的酸苦,毛姆在100年前就寫出來了,而且撐過來了!
‧內心的糾結、對人生的諸多提問,毛姆在這部自傳體小說中一直勇敢追尋
‧最終,毛姆內心自由了嗎?他的人生追尋又與你我何干?有干,有關,我們誰在幽微難行的人生裡不需彼此借點光、取點暖,毛姆的這本書,照亮撫慰我們內裡脆弱的心
他還不知道,一個旅人在跨入現實的國度之前,要越過多大一片乾旱險惡的荒原。
說年輕就是幸福,這是一種幻想,一種不再年輕的人才有的幻想。
只有年輕人知道自己有多悲慘,因為他們腦子裡被灌滿了不切實際的理想,每次接觸現實,總要撞得頭破血流。
他們看起來就像一場陰謀下的犧牲品,他們讀的書和長輩的談話,
都為他們備好了一個不真實的生活。
他們必須自己發現,所有讀過的書與所有的教誨,都是謊言、謊言、謊言;
而每一次發現,都是在那具已經釘在生活十字架上的身軀再釘進一根釘子。
作者簡介: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
英國小說家、劇作家。
出生、居住於法國巴黎,8歲時母親肺結核去世,10歲那年父親癌症過世,後被送回英國由叔叔撫養。因身材矮小、口吃嚴重而飽受同學師長取笑,亦不受叔叔疼愛,童年生活憂傷而孤寂(三位哥哥較年長,都已唸大學或入社會)。
17歲前往德國海德堡留學一年(學習哲學、文學)。18歲返回英國唸醫學院,5年後順利畢業,取得內科、外科醫師資格;求學期間多方閱讀文學作品,投入寫作,並在畢業這年出版第一本小說《蘭貝斯的麗莎》(Liza of Lambeth),頗受好評。
決定棄醫從文,就此展開超過一甲子寫作人生。初期多於雜誌發表短篇故事,後與戲劇寫作雙管齊下,劇作產量大且質佳,戲劇不斷上映公演,名利雙收,當時年僅34歲。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先後在醫院與諜報單位服役,並於1915年出版首部長篇小說《人性枷鎖》(Of Human Bondage),帶有濃厚自傳味道。1919年,發表《月亮與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立刻在美國成為暢銷書,至今仍是最暢銷的長篇。1944年,另一長篇傑作《剃刀邊緣》(The Razor’s Edge)出版,滿溢印度風情。
事實上,毛姆40歲之後,即經常前往當時的第三世界如大溪地、中國、馬來半島、印度、婆羅洲、加勒比海一帶島嶼旅行,後發表多部異國風情濃厚的遊記與上百篇短篇小說,被譽為「英國的莫泊桑」。
1965年12月16日,於法國里維拉過世,享年91歲。毛姆長於觀察,筆鋒如刀,總能犀利劃開幽深的人性,他的作品讓人深思低迴,將永為後世讀者銘記珍藏。
譯者簡介:
王聖棻
譯有《大亨小傳》、《基督教的故事》等。
魏婉琪
清大中文所畢,曾任《自由時報》編輯,譯有《冰狗任務》等。
兩人合譯的作品有《黃昏時出發》、《卡娣的幸福》、《星星婆婆的雪鞋》、《死亡大事》、《活在一個愛恨剛剛好的世界》《月亮與六便士》《毛姆短篇小說選集》等。
章節試閱
28
海沃德和維克斯都沒想到,他們拿來消磨無聊夜晚的那些談話,會在菲利普活躍的腦子裡掀起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此之前,他從沒想過宗教這件事是可以討論的。對他來說,宗教指的就是英國國教,不信仰國教教義就是任性的表現,不管在今世或來生都必然要受懲罰。但對於不信國教的人就要遭受懲罰這件事,他心裡其實也有些懷疑。說不定會有這麼一位仁慈的審判者,把地獄之火都留給異教徒,像是相信穆罕默德的人、佛教徒和信奉其他宗教的人,而特別饒恕非國教派的基督教徒和羅馬天主教徒(儘管不知他們得承受多大的羞辱,才能理解自己的錯誤)。上帝也可能會憐憫那些過去沒有機會認識真理的人(這也很合理,雖然傳教士協會一直在進行這種活動,但範圍畢竟不夠廣),但如果他們明明有機會認識真理,卻存心忽視它(羅馬天主教徒和非國教派顯然就屬於這一類),那麼懲罰就是必然的了,是他們咎由自取。只要是異教徒,就置身於危險之中,這件事再清楚不過。也許沒有人教過菲利普這麼多,但他確實日久形成了這種難以動搖的印象──唯有英國國教派的信徒,才真有希望獲得永恆的幸福。
有一點菲利普倒是很明確地聽人提過,那就是不信奉國教的人,都是邪惡而墮落的傢伙。但是像維克斯,雖然菲利普信的東西他幾乎都不信,他卻過著一種基督徒的純淨生活。菲利普長到現在沒受過多少善意對待,卻被這個美國人的助人熱忱打動了。有一次他因為感冒,在床上躺了三天,維克斯像媽媽一樣地照顧他。在維克斯身上,沒有邪惡,也沒有墮落,只有真摯和仁愛。一個人不信國教,卻道德高尚,這件事顯然是可能的。
而同時,有些人也給菲利普一種感覺,他們之所以死死抓住其他信仰不放,只不過是因為固執,或是有私利可圖,其實他們心裡很清楚那些信仰是假的,卻仍處心積慮地矇騙別人。為了學德語,他本來已經習慣在主日早上參加路德教會(註1)的敬拜儀式,但自從海沃德來了之後,他就改跟他一起參加天主教的彌撒了。他注意到,新教教堂裡幾乎沒什麼人,會眾就算出席了也無精打采。但另一方面,天主教耶穌會(註2)卻座無虛席,來敬拜的人好像都在虔誠地祈禱,他們看起來一點也不偽善。
這種對比讓菲利普十分驚訝,當然他知道路德教會的教義跟英國國教比較接近,正因如此,自然也比羅馬天主教更接近真理。在座的大部分男性(來做禮拜的會眾多數是男性)都是德國南部人,他不禁暗想,要是他也在德國南部出生,那麼他必然要成為一個羅馬天主教徒。他也可能出生在一個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國家,就像他出生在英國一樣;而在英國,他也可能出生在衛理宗、浸信會或循道宗家庭,就像他幸運地降生在一個正統國教家庭一樣。想到這一路處處都有投錯胎的危險,菲利普有點喘不過氣來。菲利普跟那個一天要同桌兩次的矮個子中國人交情不錯,他姓宋,總是謙虛有禮地微笑著。倘若只因為他是個中國人,就必須下地獄受焚身之苦,那也太奇怪了。但是,假若不管一個人的信仰是什麼,都有可能獲得救贖,那麼身為英國國教派的一員,似乎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好處。
菲利普這輩子從來沒有這麼困惑過,為此他去探詢維克斯的想法。去問他必須非常小心,因為菲利普自己是個敏感得出奇的人,這個美國人說起英國國教那種尖酸的幽默口氣,總是讓他不知該怎麼對應才好。結果維克斯讓他覺得更糊塗了,他讓菲利普承認一件事實──他在天主教耶穌會看見的那些德國南部人,對於羅馬天主教真理的堅定信仰,和他對英國國教的堅定信仰是完全一樣的;而由這點出發,又讓他承認伊斯蘭教徒和佛教徒,對他們宗教認定的真理信仰也同樣堅定不移。由此看來,「認為自己是對的」這件事毫無意義,因為所有人都認為自己是對的。維克斯不打算破壞這個年輕人的信仰,他只是對宗教很有興趣,覺得宗教是個很吸引人的話題而已。當他說自己「幾乎不相信其他人相信的所有東西」時,已經很精確地說明了自己的觀點。菲利普問過維克斯一個問題,是有關他還在牧師宅邸時曾聽伯父提到的一部溫和的理性主義(註3)著作,當時在報紙上掀起了一陣激烈討論。
「為什麼你就是對的,而像聖安瑟倫和聖奧古斯丁那些人(註4)卻是錯的呢?」
「你的意思是,他們都那麼聰明、那麼博學,而你強烈懷疑我真的能跟他們相提並論嗎?」維克斯問。
「是的。」菲利普含糊不清地回答,因為覺得自己剛剛問問題的方式有點失禮。
「聖奧古斯丁相信地球是平的,而且太陽繞著地球轉。」
「我不知道這證明了什麼。」
「嘿,這證明了你只是跟著同代人信仰而信仰。你心目中的聖人活在一個信仰的年代,今天對我們來說絕對不會相信的事,在當時卻幾乎是不可能質疑的。」
「那麼,你怎麼知道我們現在相信的就是真理呢?」
「我不知道。」
菲利普思考了一陣子,然後說:
「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現在絕對相信的事情,就不會和過去他們相信的事情一樣出錯。」
「我也不明白。」
「那你怎麼還能相信任何事物呢?」
「我不知道。」
菲利普問維克斯,對海沃德的宗教有什麼想法。
「人們總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形塑他們心目中的神,」維克斯說,「漂亮別致才是他相信的東西。」
菲利普沉吟了一會兒,然後說:
「我完全看不出來,為什麼人應該信上帝。」
這話一出口,他馬上意識到自己不能再說下去了。這句脫口而出的話,讓他彷彿掉進了冷水裡,連呼吸都突然停了。他用驚嚇的眼光看著維克斯,突然害怕起來。他趕緊從維克斯身邊離開,他要一個人靜一靜。這可說是他有生以來最震驚的一次體驗了,他想把這件事想個透徹,他非常激動,因為這件事似乎關係到他整個人生(他覺得他在這件事上的決定,對未來的人生方向絕對有非常重大的影響),要是出了差錯,可能從此萬劫不復。但是他思考得越多,就越確信自己是對的。儘管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為了了解懷疑主義,他飢渴地讀了幾本相關的書籍,結果只是更堅定了自己本能感覺到的東西。
事實是,他已經不再相信上帝了,並不是出自這樣或那樣的理由,而是他本來就沒有宗教氣質,信仰這件事,是外力強加在他身上的。這是環境和榜樣的問題,如今新的環境和新的榜樣給了他一個尋找自我的機會。他輕而易舉擺脫了兒時形成的信仰,就像脫掉一件從此不再需要的披風。一開始,沒有信仰的生活似乎有點怪,也有點寂寞,儘管以前從未意識到這一點,但信仰一直是他最可靠的支柱。他覺得自己像個本來拄著柺杖、卻突然被迫扔了它自己走路的人。拋掉信仰後,白晝似乎添了幾分寒意,深夜也分外孤單,但心中有股興奮支撐著他,生活彷彿變成一場驚心動魄的冒險,只要再過一陣子,那被他扔在一旁的柺杖和從他肩上滑下的披風,都會有如難以忍受的重擔自此從他身上卸去。多年來強加在他身上的那套宗教儀式,已經成了他宗教信仰的一部分。他想起被要求背誦的短禱文和使徒書信,還有大教堂裡冗長的禮拜儀式,那些儀式坐得他四肢發麻,好希望能活動一下筋骨;他想起夜裡在泥濘的路上走向布萊克斯泰伯教堂的情景,想起那棟荒涼的建築裡有多陰冷,他坐在那兒,雙腳凍得像冰塊,連手指都僵了不聽使喚,四周彌漫著髮油噁心的氣味。噢,他對這一切曾經如此厭煩!一想到自己從這當中掙脫了,心情就忍不住激動起來。
他這麼輕易就不再有信仰,其實自己也很驚訝,他不知道會有這樣的感覺,是因為他內心深處某種天性微妙地作祟,他把這件必然要發生的事歸功於自己聰明,興奮得飄飄然。出於年少氣盛,對於和自己不同的生活態度缺乏同理心,令他完全看不起維克斯和海沃德,因為他們只滿足於那種被稱為上帝的模糊情感,不肯再往前跨一步,而這一步在菲利普看來是非跨不可的。
有一天,他獨自爬上某座小山,在那裡可以飽覽腳下風景,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的景色總令他充滿狂喜。那時已是秋天,但白天依然常常萬里無雲,天空的光線變化比夏季更璀璨,彷彿大自然有意將更為飽滿的激情一口氣傾注在這所剩無幾的好天氣裡。他看著眼前那一大片在陽光下微微顫動的廣闊平原,遠方曼海姆的建築屋頂隱隱可見,更遠處是朦朧的沃爾姆斯(註5),最耀眼奪目的,是波光粼粼的萊茵河,寬闊的河面閃著厚重鮮亮的金光。菲利普站在山頂,心臟因純粹的喜悅而跳動著,他想到撒旦如何與耶穌一起站在山巔,讓祂一覽天下萬國。對沉醉在美景中的菲利普來說,眼前展現的這片風光彷彿就是全世界,他迫不及待飛奔下山,投身其中盡情享受。他擺脫了那羞辱人的恐懼,也擺脫了偏見,他能夠走自己想走的路,不再害怕那嚇人的地獄之火。突然間,他意識到自己同時也脫下了責任的重負,那讓他在生活中做每件事都受到後果箝制的重負,現在他可以在更輕盈的空氣裡自由自在呼吸,只需對自己做的事負責。自由!他終於成了自己的主人。他不自覺按照舊習慣感謝了上帝,那位他已不再信仰的上帝。
菲利普為自己的才智和大無畏精神心醉,也認真地開始了新生活。但失去信仰並未如所預期那樣,對他的言行舉止造成巨大的影響。雖然他已把基督教的教條扔到一邊,卻從未想過要批判基督教的道德觀。他接受基督教認定的美德,而且深深覺得,如果只是因為美德本身而身體力行,而不是為賞罰所驅使,那麼其實也是件好事。在教授夫人家,能展現這些優良行為的機會不多,但他仍努力表現得比過去更真誠一點,也逼自己對那些偶爾會找他說話的乏味老女人更體貼一點。文雅的詛咒、激烈的形容詞,這些向來是英語中的典型特色,過去菲利普一直把它們當成男子氣概的象徵,用心培養過這方面,現在也小心翼翼地避而不用了。
圓滿解決了整個宗教問題後,他打算把這件事丟到腦後,但說來容易,要做可不簡單,他沒辦法不後悔,也沒辦法克制那不時冒出來折磨自己的不安。他還太年輕,朋友也太少,靈魂永生這件事對他沒有特殊吸引力,放棄信仰在他心裡不是什麼困難的事。但有件事還是讓他覺得悲傷,雖然他也告訴自己這麼想太不理智,想把這些哀愁情緒付之一笑,但每當想起再也見不到美麗的母親,就忍不住熱淚盈眶,從她過世後,隨著時間流逝,他越來越感到母愛的珍貴。有時候,好像有無數敬畏上帝、虔誠得不得了的祖先一直在潛移默化地影響他,讓他突然陷入恐慌,說不定這一切確實是真的,在這藍色的天幕之外,確實有一個生性好妒的上帝存在,會用永不熄滅的烈火懲罰無神論者。碰到這種時候,理智也幫不了什麼忙,他想像著永無休止的肉體折磨產生的巨大痛苦,嚇出了一身冷汗,幾乎要暈過去。
最後,他絕望地對自己說:「這畢竟不是我的錯。我不能逼自己去信。如果真的有上帝存在,而且要因為我誠實地不信祂而懲罰我,那我也沒辦法。」
28
海沃德和維克斯都沒想到,他們拿來消磨無聊夜晚的那些談話,會在菲利普活躍的腦子裡掀起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此之前,他從沒想過宗教這件事是可以討論的。對他來說,宗教指的就是英國國教,不信仰國教教義就是任性的表現,不管在今世或來生都必然要受懲罰。但對於不信國教的人就要遭受懲罰這件事,他心裡其實也有些懷疑。說不定會有這麼一位仁慈的審判者,把地獄之火都留給異教徒,像是相信穆罕默德的人、佛教徒和信奉其他宗教的人,而特別饒恕非國教派的基督教徒和羅馬天主教徒(儘管不知他們得承受多大的羞辱,才能理解自己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