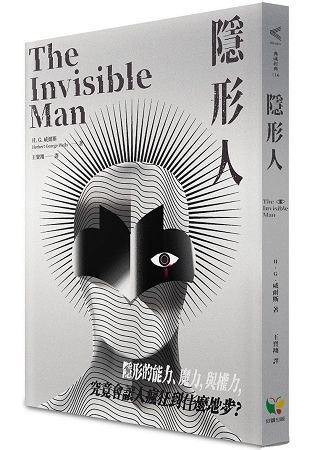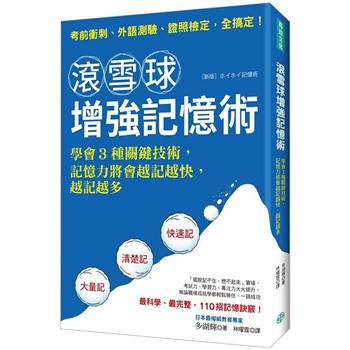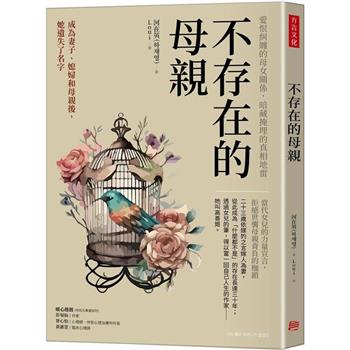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隱形人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隱形人
陷入瘋狂的,究竟是一個人,還是整個世界?
《隱形人》的故事並不複雜,威爾斯從不故弄玄虛。一個陌生怪客,某天突然來到英國小村,由於他舉止怪異,招來人們議論,隨後,小村開始發生種種怪事……不被看見的隱形人,既是一個至高無上的恐怖權力,也是一種不被社會接納、注定走向毀滅的孤身隱喻。
H. G. 威爾斯的作品不單只是述說某個科學奇想,更重要的是他試圖透過故事傳達其社會思想與哲理,以及對人類道德的深刻批判。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啟發了後世無數科幻作家,奠定了科幻文學的反思性格及反烏托邦主題,也因此被稱為「科幻小說之父」。
在引人入勝的詭譎情節中,威爾斯生動地描繪了瘋人的心理過程與人們的集體恐慌,雙方各有可憐可惡之處,在讀者心中上演一場激烈的道德辯論。《隱形人》得以名列經典,成為科幻史的不敗題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