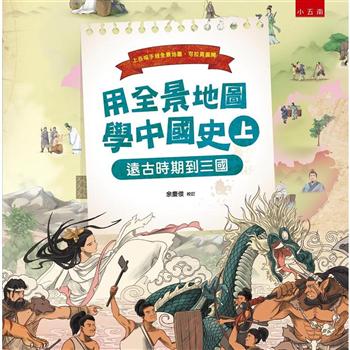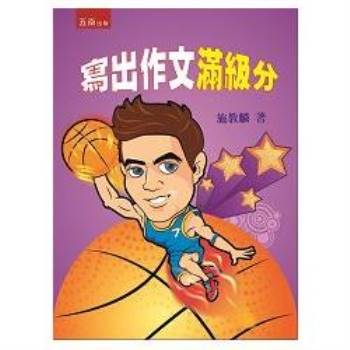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
精選作品套書,附風格設計書盒典藏!
「不,我不是存在主義者。」──卡繆(Albert Camus)
【異鄉人──卡繆告訴我們人生有多荒謬】
「沒錯,我只有這些,不過至少我掌握真實,真實也掌握我。」
故事描述一名渾渾噩噩的平凡男子,在阿爾及爾海灘莫名其妙犯下一樁謀殺案,卡繆藉此探究他所謂一無所有、面對「荒謬」處境之人。
●20世紀最廣受閱讀的小說,也是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哲學寫作小品。
●本書出版於1942年,為卡繆贏得了不朽名聲(並入選為美國高中文學課教材),某種程度上,深刻揭示了個人乃至時代的焦慮──疏離感、沒沒無名的恐懼、內心深處的迷惘。
●卡繆於1957年獲得諾貝爾獎,被視為存在主義大師。然而《異鄉人》卓越之處,卻在於它跳脫了當時的哲學觀框架。
●收錄專文導讀
—中央大學法文系助理教授 翁振盛:「好讀的譯本十分用心,譯者字斟句酌,詳實而流暢,簡潔而有力,完全貼近卡繆原著的精神。」
—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姜文斌:「此書譯筆相當不錯,讀起來很清楚順暢,能讓讀者毫無窒礙進入《異鄉人》的說故事情境。」
【瘟疫──欲證明苦難的珍貴之前,得先治好苦難】
——「您信神嗎,醫生?」
——「不相信,但又如何呢?我一直身處黑夜,一直試著看清楚,早就不覺得奇怪。」
一隻接一隻的老鼠屍體,引出前所未見的死亡風暴;
瘟神籠罩在奧蘭城上空,黎明的腳步彷彿再也不會來到......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永垂不朽的人性詰問
這是一份歷史的見證、眾生相的預言,報導式的平實文字,更顯事實赤裸無情,以及人性的真實、平庸與偉大。
●收錄專文導讀
中央大學法文系副教授 徐佳華:「瘟疫之中,我們都是被監禁的俘虜。書中不斷出現的囚犯二字,代表受疾病圍城下的居民、受極權宰制的百姓,也暗示著人類生而為死囚的現實。」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卡繆經典套書:異鄉人×瘟疫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卡繆經典套書:異鄉人×瘟疫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阿爾貝.卡繆 (Albert Camus,1913-1960)
法國文學家,1913年生於北非的法屬阿爾及利亞蒙多維城。自阿爾及爾大學畢業取得哲學學位後,從事過許多工作,並且投身參與多次政治運動及組織,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投入抵禦德國的法國反抗運動,負責編輯極具影響力的地下報《戰鬥》。
卡繆的主要作品包括──《異鄉人》、《瘟疫》、《墮落》、《放逐和王國》這四部廣受讚譽的小說;另有《卡里古拉》、《圍城》等劇作,以及《反抗者》、《薛西弗斯的神話》兩部哲學文集。1957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是第一位出生於非洲的得獎者,也是法國當時最年輕的獲獎者。1960年1月4日死於車禍意外,當時身上帶著未完成的自傳性小說《第一人》。
譯者簡介
吳欣怡
輔仁大學法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曾任高中法語教師。喜歡文學,熱愛翻譯,譯有《福樓拜短篇小說選集》、《海底兩萬里》、《異鄉人》、法文繪本《三隻小豬不一樣》,以及亞森羅蘋冒險系列《奇怪的屋子》、《古堡驚魂》、《羅蘋的財富》、《名偵探羅蘋》(穿羊皮的人)、《羅蘋最後之戀》等書。
阿爾貝.卡繆 (Albert Camus,1913-1960)
法國文學家,1913年生於北非的法屬阿爾及利亞蒙多維城。自阿爾及爾大學畢業取得哲學學位後,從事過許多工作,並且投身參與多次政治運動及組織,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投入抵禦德國的法國反抗運動,負責編輯極具影響力的地下報《戰鬥》。
卡繆的主要作品包括──《異鄉人》、《瘟疫》、《墮落》、《放逐和王國》這四部廣受讚譽的小說;另有《卡里古拉》、《圍城》等劇作,以及《反抗者》、《薛西弗斯的神話》兩部哲學文集。1957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是第一位出生於非洲的得獎者,也是法國當時最年輕的獲獎者。1960年1月4日死於車禍意外,當時身上帶著未完成的自傳性小說《第一人》。
譯者簡介
吳欣怡
輔仁大學法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曾任高中法語教師。喜歡文學,熱愛翻譯,譯有《福樓拜短篇小說選集》、《海底兩萬里》、《異鄉人》、法文繪本《三隻小豬不一樣》,以及亞森羅蘋冒險系列《奇怪的屋子》、《古堡驚魂》、《羅蘋的財富》、《名偵探羅蘋》(穿羊皮的人)、《羅蘋最後之戀》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