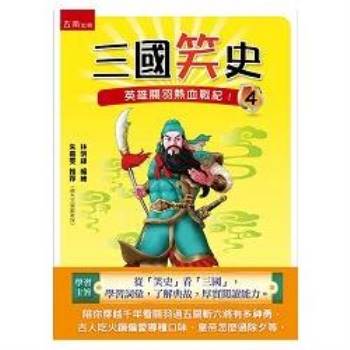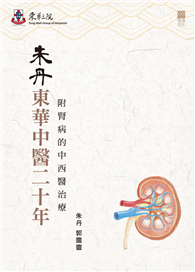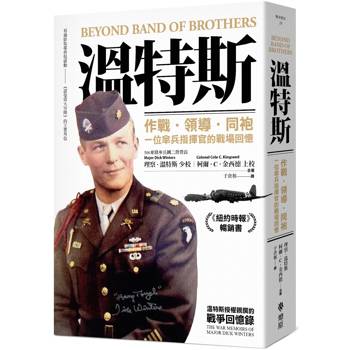英國雀巢聰明豆文學獎銀牌
英國藍彼得「愛不釋卷」獎
英國梅德維獎
英國南方學校書獎
世界讀書節推薦讀物
美國YALSA最佳推薦讀物
美國圖書館協會最佳讀物
美國學校圖書館期刊年度最佳好書
Book Sense 選書
美國大眾廣播電台夏日推薦好書
2007年紐約公立圖書館最佳讀物
內容試閱
一名竊賊在屋頂上飛奔逃命,卻從玻璃天窗跌落,險象環生。但一名有企圖心的年輕醫師卻修補了他殘破的身體,帶著他的成就到科學學會向倫敦城的知識份子展示。就在科學學會,這名竊賊拾起了新生的鑰匙,出獄之後立刻過著雙面人的生活。他變成了富裕可敬的蒙特莫倫西以及他墮落的僕人斯卡波──一連串神秘無解的竊盜案發生,警方疲於奔命……
但蒙特莫倫西必須時時刻刻提高警覺,最小的錯誤就足以揭穿他的秘密,毀掉他的雙重生活。
蒙特莫倫西的蛻變帶領我們從貧民窟到光鮮亮麗的紳士俱樂部,從歌劇院到跑馬場,再進入國際外交及陰謀的核心。第一本以蒙特莫倫西為名的小說文筆不凡──是一篇節奏緊湊、引人入勝的冒險故事。
作者簡介:
關於愛麗諾˙阿普戴爾
在英國倫敦南部的坎伯威爾長大。畢業於牛津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在英國廣播公司從事電視和廣播的製作人多年,製作了像是「The World at One」 「The Week in Westminster」「 Newsnight」等節目。。二OO二年重回校園到倫敦大學繼續研讀歷史。目前在大歐蒙街兒童醫院的醫院倫理委員會工作,並擔任「威爾斯王子藝術和孩童基金會」的贊助者、「古本江藝術大獎」的董事以及「有聲書」慈善機構的董事。目前和丈夫詹姆斯‧諾提及三名子女定居在英國的里奇蒙。
《怪盜莫倫西》的故事是從小孩子的房間產生的。作者每天晚上都會跟小孩說床邊故事,經過不斷地增加修改,就產生了《怪盜莫倫西》系列故事。
章節試閱
一八七五年:血腥的開場
他痛醒了過來。不是那種一刻也不停的刺痛,不,那種痛好像已經纏了他一輩子,熟得不能再熟。這次的痛倒像是在他大腿的傷口上又戳了幾刀。法賽醫生切割得很深,一直割到看見碎裂的骨頭為止,撕扯開的肌肉想從內部再結合起來,但手術縫線卻拉扯著肌肉不放。經過了年輕敏銳的醫師再三的治療,蒙特莫倫西對劇痛應該心裡有了譜才對,但每次後遺症發作,都一次比一次厲害,而數量有限的鎮痛劑(酒精,偶爾會有還在實驗階段的麻醉氣體),則一次比一次沒作用。
中央桌子上的蠟燭點了等於沒點;外面必然是凌晨了,可是牆上高高的鐵欄杆卻沒有光線透進來。蒙特莫倫西知道犯不著白費力氣去叫夜間警衛。沉默穩重、不茍言笑的馬斯頓認為他在監獄醫務室的職責就是防止犯人逃獄,他可不管蒙特莫倫西是不是躺在病床上連翻身都有困難,更別提舉起腳來逃跑。不管他要什麼,他都得在黑暗中等達恩利護士來了再說。達恩利護士的體型非常魁梧,心地倒是不壞,她相信壞人也可以變好,讓生病的罪犯喝口水就可能是幫他改頭換面的契機。
等待的同時,蒙特莫倫西又像之前好幾次那樣,任腦海浮出一年前的影像,回想起他被捕的那晚。他就像頭狂奔逃命的動物,躍過工廠屋頂,要不是緊抓住那袋偷來的工具不放,他八成就會在落腳前先看見那扇天窗,而不會跌落到那台輾碎機的鐵殼上。他記得猛然的撞擊,皮膚感覺到冰冷的金屬,然後就什麼也不知道了,只知道後來有人在談論他,當他不在場似的。
「我很肯定醫務室基金裡連一塊錢都沒有,我會負責所有的設備和監督。」
後來他才知道說話的這人是羅伯•法賽,一位外科醫生,想要治療蒙特莫倫西的多重傷勢,藉此揚名天下。
蒙特莫倫西只能憑想像去臆測當時發生了什麼事。顯然是警察在工廠裡發現了他扭曲的身體,看見他罪有應得,想必是心花怒放。就這麼摔死了不但可以省下打官司的麻煩,還可以省下醫療費用。可惜他偏偏就不讓警方如願,所以他那個血肉模糊的身體就給抬到了倫敦橋附近的教學醫院去了,法賽醫生也就是在那裡第一次看見他。這具身體的傷勢非常嚴重,不過身體的主人倒是一看就知道非常強壯。
法賽正在準備一篇論文,討論複合傷的治療,準備在皇家外科手術學院發表。他曾考慮到巴爾幹半島去考察戰場的傷亡率,以便用真實的例子來闡述自己的理論。偏就這麼巧,就在他埋頭書案的時候,一個再完美不過的題目就送到了他的眼前。法賽要是不插手,這人就非死不可;要是他活了下來,那麼法賽的聲望可能也會永垂不朽。
於是醫師和這具怵目驚心的血人就慢慢發展成一個計畫。血人沒死,熬住了一口氣,終於有了人樣,可以上法庭受審了。檢方稱他「蒙特莫倫西」,這名字是醫院人員給他取的,因為他給送進醫院時胸前緊抓的工具袋上就寫著這名字。他得由兩名法警攙著聽判。蒙特莫倫西成了第四九三號囚犯,在新監獄裡服刑。典獄長對法賽醫師重建他身體的計畫非常有興趣,約了醫師吃晚飯,順便交換一下彼此對懲凶罰惡和大眾健康的看法;他們兩人都同意沒有知識而且環境衛生差的家庭容易產生罪犯,而要打擊犯罪就必須要讓這些家庭有工作、受教育、提高衛生條件。
法賽醫師後來成了監獄的常客,典獄長也允許他帶著蒙特莫倫西到城裡(當然是有戒護人員)去參加會議,讓成就卓越、求知若渴的醫生、科學家在講述自己的成就同時,也聽聽法賽的先進技術。
在這樣的聚會裡,蒙特莫倫西幾乎一絲不掛,只裹條毯子,坐在講台後面。也就是在這樣的聚會裡,他吸收了和出席眾人一樣多的知識。除了把他的傷疤展示給在場來賓看之外,沒有人會注意他,但他卻把醫學、工程學、數學、自然哲學方面的先進知識都聽進了耳朵裡。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做慣了小偷,當然不能入寶山空手而回。雖然沒有口袋可以放贓物,他卻偷盜思想和事實,牢牢記住每一場演說的細節。他並沒有計畫要把偷來的資訊加以利用,純粹只是感興趣,讓他在監獄工房做苦工的漫長時光中有東西可想,或是在接受法賽醫師手術後躺在醫務室裡無所事事的時候可以動動腦筋。
而在這個陰暗寒冷的早晨,蒙特莫倫西忍痛躺在病床上,思索著大都會勞委會的總工程師所發表的長篇演講,後來的事實證明,對他來說,這篇演說至關重大。想著想著,他忽然靈光乍現。等到達恩利護士拿著個破錫杯來到他的床邊,改變他一生的計畫已經在他的腦海裡有了雛形。
約瑟夫•貝柔吉特爵士
那篇演講的主題是倫敦的新下水道系統。倫敦市將近二十年來都得忍受骯髒不便的道路工程和建築工地。一幫又一幫的工人把成噸的泥土鏟走,砌了上百萬塊磚頭,建造了總長八十三哩的地下管道,此後倫敦市內腥臭危險的廢棄物就可以從這些地下管道排送到泰晤士河河口附近了。如今浩大的工程總算完工了,設計而且督導工程的這位約瑟夫•貝柔吉特爵士驕傲的描述他的工程,這項成就不僅讓他享譽國際,而且女王還特別晉封他為爵士。
站上了科學學會的舞台,約瑟夫爵士是既自信又害怕。他對自己的主題瞭若指掌,但蒙特莫倫西看得出他還是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比不上聽眾裡的許多人,像是幾名上議院議員,一些傑出的學者,國外來的訪客。貝柔吉特身材矮小,外表很整潔,鼻子小,聰慧暗色的眼睛,似乎能夠盯住屋裡每個人。他的衣著整潔時髦:方格花紋長褲、素色外套、黃色背心。襯衫領子扣得很高,打著一條絲領巾。他的頭頂禿得發亮,想用幾綹頭髮遮蓋,卻是欲蓋彌彰。可是到了耳朵兩側頭髮卻又濃密又黑亮,和三角形的鬢角連接起來,又接上了濃密的八字鬍。臉頰其餘的部分卻和頭頂一樣的清潔溜溜。蒙特莫倫西忍不住納悶是怎麼回事,既然他臉部的毛髮這麼茂密,又何必費力氣去把臉頰到下巴的部分刮得那麼乾淨呢?是他自己弄的,還是有專人來判斷刮鬍刀應該刮到哪裡?他又得多久刮一次臉呢?現在已經是晚上六點了,他的臉上卻一點也沒有鬍碴冒出來。
為了討聽眾的歡喜,貝柔吉特的開場白很輕鬆,先介紹自己不尋常的名字。
「原本是法文,不過我的家族在英國已經三代了,我很驕傲的說我父親曾是皇家海軍軍官。不過當然啦,從我的工作,我非常清楚人類不管是什麼國籍,什麼階級,相似的地方總是要比相異的地方來得多-要是提到大家製造的廢棄物的話,就算是貴族也跟最卑下的農夫一樣臭不可當。所以為了大眾的福利,不管是高高在上的也罷,市井小民也罷,大都會勞委會肩負起了處理廢棄物的衛生責任,而我十分榮幸的接受任命,也可說是十分感激能獲賜這項特權。」
正如約瑟夫爵士所言,今晚出席的每個人都有理由要心懷感激。就在幾年前,他們現在坐的這個地方,儘管有雕梁畫棟,卻是臭氣沖天,誰也不想在裡面待上一晚。
「今天下午到這裡來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科學學會的會址實在是選得太妙了。我直接從市中心來,信步走向河岸。孩童在街道上玩耍,人們沿著新建的維多利亞碼頭散步,盡情呼吸新鮮的空氣。不過在座各位可能還記得,就在不久之前,大家是多麼不喜歡到這一區來。就連國會殿堂都因為泰晤士河散發的腐臭味道而惡臭撲鼻。追根究柢,我們知道倫敦城漸漸變成了帝國的核心,但我們的祖先所建造的泄水道和地下河道已經不敷使用。廣受各家各戶歡迎的新式沖水馬桶完全超過了古老水道的負荷,而首都的人民也因為骯髒的環境衍生疾病而喪失了生命。而這些穢物只有一個途徑可以離開倫敦城:也就是流入我們身邊的河川。容我大膽的假設,如果我在二十年前公開我的原始計畫,而不是在此時此刻慶祝已經完成的工程,在座聽講的人數只怕是寥寥可數!」
與會的科學家、政界人士、興致勃勃的一般聽眾,很有禮貌的低聲竊笑,隨即又在座位上正襟危坐。環繞講台的座位呈馬蹄鐵形。約瑟夫爵士稍微的放鬆了些,準備要進入主題了。
「方才我提到了碼頭,忍不住要談談河邊的幾條大道。今天我以十分歡喜的心情向各位宣布,我們計畫在五年之內用新的電力來照明所有的河濱大道。不過我要先敦請各位先注意地底下的建設。不僅僅是今天帶各位來此的地下鐵,不僅僅是輸送能源到這個大會堂的瓦斯管線,不僅僅是帶來健康乾淨的水管。諸位先生,下次走在倫敦街頭,請低頭看看人行道,請找找人孔,那就是通往地下世界的大門。那是一個充滿了巨大管線的世界,有成千上萬加侖的水以及更多的『固體廢棄物』就在你的腳下流動,一小時又一小時,不斷流向大海。」
約瑟夫爵士拿出一張巨幅地圖來,是地下水道的分布圖,畫得很精美,五顏六色,貼在一塊大木板上。科學學會雇有兩名門房,負責舉高或傳閱演講人帶來的樣品。通常最重的東西也不過是玻璃瓶裝的腦部組織、植物,再不然就是從外國帶回來的動物標本。不過這張地圖卻比約瑟夫爵士還要高,而且幾乎有整個講台一樣寬,區區兩個門房完全無法應付。他們需要幫手,所以貝柔吉特就招手叫蒙特莫倫西上前來幫忙。那時他正坐在講台後面,等著法賽醫師上台後當他的展示品。
那時蒙特莫倫西的感覺是興趣有之,但尷尬卻更甚。就和往常一樣,為了要當醫師的展示樣本,他只穿著最單薄的內衣褲,儘管已經習慣了在眾人面前像物品一樣給品頭論足,可是兩手高舉起來,幫著撐住笨重龐大的地圖,他還是覺得像個笨蛋。誰知道還有更糟的呢。約瑟夫爵士拿著長棍指點著廢水流經倫敦的路徑,一面用力敲打地圖。每敲一次,木板就晃動得很厲害,而蒙特莫倫西和兩個門房也跟著晃動。有一次,約瑟夫爵士指著一條下水道,一坨虛構的屎從白金漢宮經過國會,沿著新的碼頭一路流出來,他重重的敲打地圖,力道之大,害三個扶住地圖的人踉踉蹌蹌的歪到了講台邊緣。蒙特莫倫西覺得褲子要往下掉了。大會堂後方傳來陣陣竊笑,他用眼角瞄到法賽醫師用雙手遮住了臉。
一八七五年:血腥的開場 他痛醒了過來。不是那種一刻也不停的刺痛,不,那種痛好像已經纏了他一輩子,熟得不能再熟。這次的痛倒像是在他大腿的傷口上又戳了幾刀。法賽醫生切割得很深,一直割到看見碎裂的骨頭為止,撕扯開的肌肉想從內部再結合起來,但手術縫線卻拉扯著肌肉不放。經過了年輕敏銳的醫師再三的治療,蒙特莫倫西對劇痛應該心裡有了譜才對,但每次後遺症發作,都一次比一次厲害,而數量有限的鎮痛劑(酒精,偶爾會有還在實驗階段的麻醉氣體),則一次比一次沒作用。中央桌子上的蠟燭點了等於沒點;外面必然是凌晨了,可是牆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