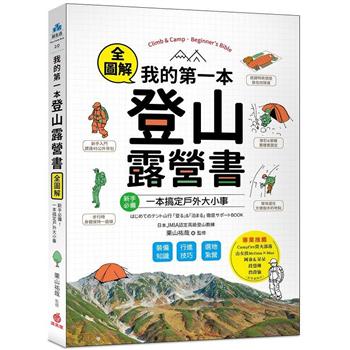文化評論家南方朔 專序導讀
蘇珊桑塔格以熱烈的獨到思維,披荊斬麻開闢閱讀價值的瑰寶路徑,
只有精力充沛的讀者才能從中找到細細密密的驚奇;
她提煉電影、舞蹈、攝影、繪畫、歌劇、空間的精緻批判,
凡視覺所及洞察力穿透概念、感覺、印象、刻板;
她顛覆那裡與這裡,她擁護的自由,提倡的激情,她從不熱中慣例,
她省思,以過去二十年間發表的四十篇長短不一的傑作,抵抗假象。
美國最重要的知識份子、最具爭議、最受注目的女作家蘇珊?桑塔格,冷靜的真知灼見,永恆維護思想的尊嚴與風格。
蘇珊桑塔格說:
我反對庸俗、反對道德與美學的膚淺與漠不關心。
我是好鬥的審美家,幾乎不閉門造車的倫理家。
我沒有準備寫那麼多宣言,
但是我壓抑不住警句似的品味陳述,
加上我堅定的對抗意志,
呈現方式有時候會讓我吃驚。
作者簡介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
近代西方最受人注目、最具爭議的女作家及評論家。
與西蒙?波娃、漢娜?鄂蘭並稱西方當代最重要的女知識份子。
被譽為「美國公眾的良心」。
2004年12月28日去世。
著有四本小說:《恩人》(The Benefactor)、《死亡工具》(Death Kit)、《火山情人》(The Volcano Lover),《在美國》(In America)(本書獲得二○○○年美國國家書卷獎(National Book Awards)的);其他作品還有短篇故事集《我等之輩》(I, etcetera)、幾部劇本,如《床上的愛麗斯》(Alice in Bed),以及《反對詮釋》(Against Interpretation)與獲得美國全國書評界(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的評論獎《論攝影》(On Photography)。
《疾病的隱喻》是蘇珊?桑塔格以無比的勇氣和銳利之筆,揭穿疾病的隱喻外衣,帶我們看重重迷思之下的疾病面貌。當結核病、癌症、愛滋病成為令人聞之驚慌的病,桑塔格的透視猶如一扇窗,使我們取得了觀照這三種病的歷史/文化角度,我們才能擺脫歧見、理性面對疾病,並知道如何給病人適當的對待與治療。
她的著作已經有二十三種語言譯本。
二○○一年獲頒耶路撒冷國際文壇獎(Jerusalem Prize)。
二OO三年獲德國圖書和平大獎。
譯者簡介
陳相如
中國文化大學俄文係畢業,莫斯科普希金學院俄語碩士,倫敦大學Goldsmiths College文化研究碩士,曾任出版社編輯、網路企畫等職,翻譯作品有《附上我的愛-英國老書商與小女孩的書信情緣》、《日本女人不會胖也不會老》、《平均率》、《萊特》、《聖女貞德》、《俄羅斯奢華愛戀》、《童玩手工皂》、《融化倒模皂大全集》、《童玩手工皂》等書。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重點所在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92 |
二手中文書 |
$ 255 |
小說/文學 |
$ 334 |
中文書 |
$ 334 |
英美文學 |
$ 34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內容簡介
序
導讀
蘇珊.桑塔格的詩意世界
資深文化評論家◎南方朔
這本《重點所在》(Where the Stress Falls),乃是蘇珊.桑塔格於二OO一年輯集若干一九八O年代後的文章而成。這也是她生命中最後的著作之ㄧ。本書的扉頁引了美國著名女詩人伊莉莎白.碧許(Elizabeth Bishop1911-1979)所寫〈客中問〉的如下詩句:
大陸、城市、國家、社會:
從未能廣泛且自在地選擇。
這裡或是那裡……不。我們是否都應該留在家園,
不論家園在何處?
伊莉莎白.碧許遠遊巴西,被人問到而寫此施以自況。由碧許該詩的思維脈絡,她似乎就是要抹消掉「這裡或那裡」的差別,而表達出某種悲劇性但也更豁達的「處處非家處處家」的世界心懷。碧許少孤,半生流離,這種生命情境與蘇珊.桑塔格相似。或許這就是她引這詩句為本書作注腳的原因。
因此,作為一本選集,它看似蕪蔓,但卻是「微型蘇珊.桑塔格」的體現。她在本書的第一部份「閱讀」裡,為那些她認為重要但卻顯然受到世人忽視的各國作家做出呼籲,包括美國作家格連威.威斯考特(Glenway Wescott)和伊莉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巴西作家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波蘭作家亞當.札嘉耶斯基(Adam zagajewski)及貢布羅維奇(Witold Gombrowicz),德國作家錫巴德(Winfred G.Sebald)和瓦澤(Robert Walser),匈牙利的契斯(Danilo Kis),墨西哥作家胡安.魯佛(Juan Rulfo),以及英國前代作家史坦恩(Laurence Sterne)等。由蘇珊.桑塔格提到這些作家和他們的作品,一方面印證了她嗜好閱讀,把閱讀作為發現自己的態度外;另方面也印證了她在自己的經典之作《反對詮釋》裡對文學作品的觀點。那就是她拒絕把作品的內容視為被論定、被凍結的意義,她認為過度在內容上詮釋,乃是「知性對藝術所做的報復」,因而她的閱讀乃是形式、感性、文本的行進過程,以及聯想、質問等面向並重的理解方式,乍看起來有如天馬行空、難覓蹤跡,而其實則是透過閱讀,不但豐富了作品也豐富了自己。她論作家作品的這些部分,乃是所謂「蘇珊.桑塔格體」的具體見證,這也是我們不能因為它看起來駁雜散漫而予以疏忽的原因。
眾所週知,蘇珊.桑塔格本質上乃是歐化極深,而且也如昆德拉一樣,乃是對中歐人文傳統理解極深的知識份子型文人。因而能出入文學、劇場、電影、建築、攝影,甚至音樂、園藝等各個領域,這乃是她得以會通並成其他的原因。而她在本書第二部分「視覺」裡,就以這方面的文章為主,這乃是第一部分的延長。
至於最可以拿來參照她生平的,則是第三部分「那裡與這裡」了。其中有許多篇章涉及她的人生反思,以及對知識份子角色的定位,特別是一九九O年代中期南斯拉夫聯邦動態,她曾九次遠赴塞拉耶佛並演出「等待果陀」。這些篇章其實也反映出她做為一個「公共知識份子」的本色與風格。
因此,這本《重點所在》,雖然是文章集合而成,夾敘夾議,但卻是蘇珊.桑塔格這個人具體而微的展示。這也是人們在她逝世已滿四年的此刻,在懷念崇仰之餘,不宜偏廢的一本著作。在閱讀本書時,蘇珊.桑塔格那驚人的才情,那作為知識份子的人文胸懷,等於又再次重現到了眼前。
蘇珊.桑塔格逝世已滿四年。總結她的一生,我們不能不承認她其實早已成了二十世紀後半期在美國幾乎已不可能出現的「文化明星」。在她之前,要在紐約成為作家及文化工作者這種名劉並不困難,紐約及美國東岸有許多極具影響力的雜誌是以造就出龐大的「紐約才子才女幫」。但這種盛況到了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就已不再。戰後大學體系的擴張,幾乎將所有的文人知識份子都納入了校園。另外則是「專業化」的觀念盛行,也就取代了文人知識份子發言的空間。但就在這樣的變局裡,蘇珊.桑塔格卻以個人的才情維繫住了一片天。她晚年當多少有點欣慰的表示:「隨著移居紐約(時在一九六O年代初),我的生活激烈改變,埋藏在怡居中的改變,是我不再勉強接受成為學者。我在誘人,極為安全的文學世界之外紮營。」由於身在大學之外有更好的觀察位置,遂使得她:
我有這麼多讚賞,有這麼多事務可讚賞。我環顧四周。看到沒有得到應有讚賞的重要事務,或許由於我的書卷氣、我的親歐、我隨意搜尋美學極樂的精力。我特別適合看到我看到的,適合瞭解我已經瞭解的。然而讓我驚訝的是大眾第一次發現我說的事務是新的(但之於我不是那麼新),我被認為是鑑賞先鋒,從第一篇論文問世起,我被視為品味締造者,當然,意識到我筆下主題到注意,我是第一人,讓我洋洋得意。
在此刻引述她自己的話,可以看出她在一九六O年代初那個消費主義已然抬頭,文學藝術作為政治社會批判領域的時代則快要過去的時刻。由於文學藝術已被稀釋出新的空間和新的類型(如電影、現代舞蹈等),她遂靠著自己和靈敏和聰慧光芒,在校園外的陣地建立起自己的聲望。由她很多次提到像大詩人及評論家奧登這一次的人物都對這種變化趨勢,無所覺,可見她欣然自得的程度。
因此,就文化的角度而言,過去的論者認為德國的班雅明乃是「歐洲最後的文士」,那麼蘇珊.桑塔格則可以說是戰後美國的「第一個新文士」。在她眼中,文學藝術已不再是文以載道的陳腐載具,而成為探索多元、解體二元、開拓表現方式及提高自主鑑賞能力的新領域。她是與她同質的法國羅蘭.巴特的引進者與代言人,羅蘭.巴特的第一個英文選讀本即由她操刀並執筆導讀。她和羅蘭.巴特的同質性,乃是理解蘇珊.桑塔格的第一步。
正因為蘇珊.桑塔格替業已陳舊的「紐約才子才女幫」開創出新的可能性,才子才女們不再是政治社會及價值批判的先鋒,而是品味及鑑賞這種新型態都市文化階級的趨勢帶領者,這遂使她成了新興的「文化明星」。但像她這樣的「文化明星」可與許多後進地區的文化名流不同,她涉獵淵博,深刻的閱讀極其廣泛,而且行文精確,每次從大處會通,掌握住了時代的脈搏。儘管美國文化保守主義者對她一向惡意抨擊,認為她是文化上的「黑蜘蛛」,是「隨意批判」的壞榜樣,但她是「美國最聰慧的女子」這個稱號卻不逕而走,成了她終身的冠冕。而她腳跨多個文學藝術種類,比起前代「文化教母」如瑪莉安摩爾(Marianne Moore),葛楚德史坦因(Gertrude Stein),瑪莉麥卡錫(Mary McCarthy)已遠勝一籌。
蘇珊.桑塔格跨文學評論、小說創作、電影編劇及導演評論,以及攝影、舞蹈、建築、園藝,以及總體文化評論等,由於著作等身,已無法逐一點評。但無論她在文學藝術上的興趣如何廣泛,我們終究不能否認,作為猶太人「紐約才子才女幫」繼承者之ㄧ如她,在公共事務上也終究不可免的承襲了這個傳統的左翼人文價值,並因此而常常引發重大爭論。如果我們不健忘,就當記得二OO一年「九一一」慘劇發生後,美國朝野在絕對的「政治正確」下,幾乎舉國一致抨擊「九一一」是「懦夫」行為。當時美國的知識份子群落,蘇珊.桑塔格乃是第一個站出來做出「反批判」的人物。她投書「紐約客」雜誌,捐出那些與敵偕亡的恐怖份子,和另外那些在高空上按個電鈕即殺人盈萬但自己卻很安全的人相比,究竟誰才是「懦夫」?她在投書裡說道:「就勇氣而論,不管我們對星期二殺戮的這些加害者如何稱呼,他們並不懦弱。」她的投書當時招致排山倒海的攻訐可想而知,而她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氣,也的確讓人欽佩得無話可說。惑與正因為她的率先提出異議,稍後美國,甚至包括英國,才有一大群文人知識份子站了出來,像「南大西洋學報」、「格蘭達雜誌」等文人菁英雜誌也紛紛出版異議專號!
這就是蘇珊.桑塔格的公共知識份子異議角色的最佳說明。儘管她在文學藝術上擺脫了過去那種泛政治的觀點,也亟力反對沙特的「介入文學」觀點,但在公共事務上,她那種以浪漫人道主義為核心價值卻始終未曾放棄。她並對歐美進步知識份子大舉參加西班牙反法西斯內戰的傳統緬懷不已,這種緬懷也常見諸她的文章中。這也是儘管她深知當今世局紛紛,知識份子的熱情早已因過度消耗而逐漸退卻,但她從早年反越戰起,卻始終有所堅持,她對南聯的塞拉耶佛特別關心,對巴勒斯坦問題也長期注意,但或許因為她的猶太人血統,像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即有所偏,而受到人們指責。現代的國際政治早已成了大黑缸,縱使人道關懷,只要手接觸到黑缸,就不可能保持乾淨,這部份或許乃是她此生最遺憾的事吧!
我從早年最先接觸到她的經典論文《假仙筆記》(Notes on Camp)起,就對她的許多觀點感到興趣,她聰慧、靈巧。由於見聞及閱讀用心,每能動見機先,開創一家之言。特別是她的文論,已等於非常辯證的由「主觀批判──客觀批判──再主觀批判」這個脈絡發展,達到了一種「詩意散文」的境界,這點才是她最大的貢獻。也正因此,對於這本不是太小的小書,我們恐怕也應該像對「詩意散文」那樣,其體會她那聰明的世界吧!
側記南方朔:
他大部分的時間都拿來讀書,經史子集包羅萬象,建議每個人的床頭書都應該擺上一本《漢賦》,為了寫作他典藏許多冷僻豐富的書籍,其中還包括一本愛爾蘭語字典。
他極少曝光媒體,卻堪稱文化上的「台灣奇蹟」,年輕時毅然脫離體制、催發民間力量,擔任黨外雜誌總主筆,並策劃參與街頭運動;現在他掌握社會脈動,關心年輕族群,論述鏗鏘有力,是文化政治上重量級的大師。
南方朔,本名王杏慶,一九四六年生,台大森林系、森林研究所畢業,文化大學實業計劃研究所博士結業。曾任中國時報記者、專欄組主任、副總編輯、主筆等職,目前為新新聞總主筆。大田出版《語言是我們的居所》、《語言是我們的星圖》、《語言是我們的海洋》、《在語言的天空下》、《世紀末抒情》、《有光的所在》、《給自己一首詩》、《語言是我們的希望》、《語言之鑰》等豐富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