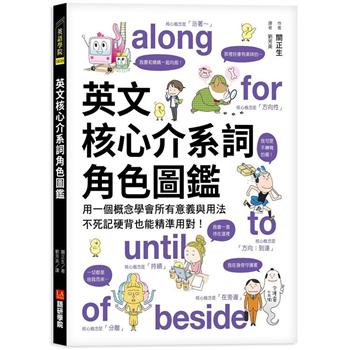推薦
【世界宗教博物館榮譽館長】漢寶德
王俠軍先生的「八方新氣」,是他所推動「新瓷革命」的成果。這是近年來,國內一片「文化創意產業」聲中最成功與最典型的案例。他兼具創發力與生產力,是成功的主要因素,值得公、私各部門倡導文創事業者參考。在創造力方面,他能溶傳統、美感、與生活於一爐,最為難得,也因此具有世界級的競爭力。
對我而言,最使我傾心的是他對美感的執著。我一直覺得美是一種國際競爭力。他在琉璃工藝上努力了那麼多年,建立起現代中國琉璃藝術的範式,已經在海峽兩岸廣為傳播,進而向全世界推進,幾乎成為新玻璃美學的代表。他又抓住新世紀時代的精神,為古老的瓷藝接續傳統,在潔白的基礎上,注入新的美感。他鍥而不捨的,把自己的理想與美感的標準凝而為動人的作品,呈現在我們眼前,實在是值得喝采與效法的。
【文化評論家】南方朔
有耳目即有聰明,有心思即有智巧,但若自劃為愚,未嘗竭思窮慮以試之耳。──清.李渙《閒情偶寄》
有一種人,對社會的最大貢獻,乃是促成了生活的藝術化。在法國,他們被稱為「波希米亞人」(Bohemia)。十九世紀的上半,巴黎的「波希米亞人」首次出現。他們是隨著城市擴張,文化需求漸增,而產生的一群高學歷年輕人,希望在時代的變化中能夠在文學藝術上伸展抱負。這些「波希米亞人」多半出身於巴黎或外地的中產階級,他們或許後來的人生有幸與不幸。但大量的文化青年卻無疑的形成了「品味製造者」的角色,建構出新的藝術化生活,影響著後來的中產階級,甚至並左右著某些新之學藝術形式的創造。「波希米亞人」很難被定義為那種階級,他們有著極大的曖昧歧義特性,但他們擁有「文化資本」則無可置疑,「文化資本」是一種會對藝術及生活的感覺去思考的資本。 而「琉園」主人王俠軍的這本抒情述感的散文,或許就可視為台灣一個中生代波希米亞人的生活及品味沈思錄。
它不是甚麼「鉅型論述」,但就在各種生活瑣事的靜靜敘述中,他那種獨特且敏銳的感覺能力?具現無遺。清代的戲曲和生活美學家李渙(笠翁)在《閒情偶寄》裡說道:「有耳目即有聰明,有心思即有智巧。但若自劃為愚,未嘗竭思窮慮以試之耳。」王俠軍之所以能經營「琉璃工房」及「琉園」異常成功,將台灣的玻璃藝術帶到另一個境界,其實並不是沒道理的。 王俠軍是來自印尼的華裔子弟。在印尼的時候,家裡經營照相館、鑲金牙的店,以及成衣布匹為業,算是相當殷實之家。一九六○年代中期的印尼暴亂,他的父親被拘三個月,於是舉家分兩次遷至台灣。小學念士林、中學念仁愛、而後進世新電影科,畢業後陸續做過攝影、編輯、房地產及廣告企劃,電影等許多行業,而後中年改行,到美國的底特律去學燒玻璃,學成後,回台成立「琉璃工房」,五年後又改設「琉園」。他一路走來,真是路徑歧亂。但他說:「我想每個人都有那類似羅盤密密麻麻的表面,顯示了各種走向與方位,而好奇心使我們從來不放棄沿著興趣,帶著熱情和信心,再參與新遊戲的機會。」
而他顯然把握住了自己對生命的感覺和機會。 這本書裡,廿多篇感性的文字,都是王俠軍對生命的瑣細隨想。他沒有去寫當年印尼暴亂,也不寫自己創業的如何如何,他關心的只是生活,包括生活裡的記憶和感想。他寫父親的高調品味、寫母親的能幹務實;他寫的多半是生活裡的瑣瑣細細的感覺,如空氣、觸覺、光影、酒、夢想、牛仔褲、咖啡、香水、錶、街道..等等。而就在這些瑣碎中,對生命不隨便的態度,以及自然流洩的生活審美觀點也就汩汩而出。讀他的書稿,有許多地方都讓我想到波特萊爾當年在巴黎閒逛時所寫的那些隨筆。
生活的美感是一種沒有目的之關心,也是一種對自己的感覺能力的挑戰。美存在於生活中。 美感經驗在生活中,這時候就讓人想到林語堂早年在《生活的藝術》裡說得非常清楚的道理。他顯然很受到德國思想家席勒(Johann F.von Schiller, 1759-1805)的啟發。他說: 「藝術是創造,也是消遣。這兩個概念中,我以為以藝術為消遣,或以藝術做為人類精神的一種遊戲,是更為重要的。我雖最喜歡各式不朽的創作,不論它是圖畫,建築或文學,但我相信祇有在許多一般的人民都歡喜以藝術為消遣,而不一定希望有不朽的成就時,真正藝術精神方能成為普遍而彌漫於社會之中我寧願學校中教授兒童做些塑泥手工,寧願一切銀行經理和經濟專家能自製聖誕賀卡。
我們知道這些都是出於自動的。而真正的藝術精神祇有在自動中方有的。」美感存在於生活的瑣事中,祇是在過去漫長的歷史中,一則由於中國人的太過沈重,再者由於缺乏了普遍的富庶,因而遂使得中國人社會裡在生活中尋找美感的傳統不發達。在歷代典籍中,凡涉及生活品質者每多被視為小道,差不多要到了宋代,有關生活品質的著作,如《文房四譜》、《墨經》、《酒經》、《糖霜譜》、《香譜》、《花經》、《梅譜》、《菊譜》、《荔枝譜》、《洛陽牡丹記》,等始告大量出現。到了明清之際,始對生活的美感產生普遍自覺。它充分顯示在豐富的筆記散文中。只是到了近代,由於戰亂頻仍,生活素質再告退化,這種生活的美感也漸趨蕭索。類似於林語堂這類作家的評價也就恆低於另外那些政治社會型的知識分子。這種情況到了近年來,始由於人們要重新關切起各種生活品味的問題,而逐漸有了改變。
我們必須重拾生活中的美感經驗,但那不是對名牌美食或華屋的耽溺式消費,而是一種藉著沈靜的反思,而對生活中的周遭事務做出美感意識上的探索,讓人的存在更符合人性的需求,也讓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共感更趨細緻。美感經驗經常會是一種創造的泉源。 王俠軍這本隨興式的散文,很有他的風格特性。它沒有眩惑的外表,但在平凡瑣碎中卻又有著很細膩的聯想與追求,這本書是值得的。 我和王俠軍並不認識,他透過友人請我先讀這份書稿。這是讀後的感想。本世紀最傑出的小提琴演奏家曼紐因最近逝世,我花許多時間閱讀他留下來的許多著作。曼紐因談到:一切美的事務,它終極的意義就是能增加我們的感應與體會溝通的能力,而使人成其為人。王俠軍的著作以另一種方式呈現著生活美感的沈思。 姑且稱這篇短文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