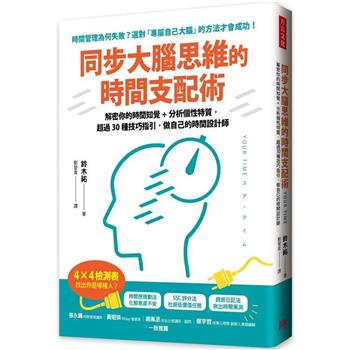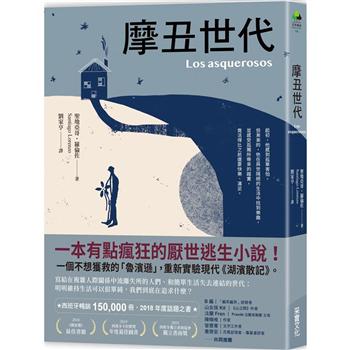《贖罪》獲各國文學獎與媒體肯定:
.入選美國《娛樂週刊》1000期,二十五年來百大最佳書籍
.入選英國《觀察家週報》百大小說:一部令人著迷的當代經典小說
.《贖罪》,一部動人的小說,整本書的架構和節奏,充滿了令人敬畏的自信和說服力。-英國獨立報
.無人能敵的大文豪......獨特又充滿不可思議的吸引力的小說。-週日獨立報
.緩慢燃燒的恐懼。即使是沈醉在文字的激情中,仍然知道可怕的事情即將發......-英國泰晤士報
.細膩又強而有力,兼具喜劇和暴力的因子,《贖罪》就是這樣錯綜複雜的小說。結合了想像力與主角自我追尋的華麗表現手法,造就了這部曠世鉅作。-英國太陽報
.故事的全貌,是如此的美麗壯觀。-約翰.厄普戴克
.2004年榮獲【Santiago Prize歐洲小說類獎】
.2002年榮獲美國【洛杉磯時報圖書獎】
.2002年榮獲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小說獎】
.2002年榮獲美國【時代雜誌年度最佳小說】並同時入選《時代雜誌》【跨時代百大小說】(ALL-TIME 100 Greatest Novels)
.2002年榮獲英國【WH Smith文學獎】
.2002年榮獲南非【Boeke獎】
.2001年入圍英國文壇最高榮譽【布克獎】
.2001年入圍英國【詹姆斯.泰特.布萊克紀念獎(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
.2001年榮獲英國【惠特筆獎 (Whitbread Book Award)長篇小說類獎】
我懦弱地面對一道道已湮滅的波浪。
除了我的想像力,沒有人原諒我......
罪惡存在,愛情也仍然存在。
我如此贖罪,用被改寫的結局......
13歲那年盛夏,白昂妮由於嫉妒與誤讀,杜撰一段指控,她的惡意,拆散了姐姐西希莉雅與羅比這對情意真切的戀人。
羅比入獄服刑,出獄後赴二次大戰前線打仗。
西希莉雅在後方等待,祈求羅比有朝一日能回到她身邊。
一年年過去,白昂妮日復一日悔恨。
但命運,卻總是阻擋在她的懺悔之前。
白昂妮只能試圖用文字,改寫西希莉雅與羅比的結局。
這是需要花一輩子時間書寫,但也許永遠都無法出版的小說......
伊恩.麥克尤恩在《贖罪》中精確刻劃幽微人心,筆觸細膩。道德與階級差異,愛與戰爭,嫉妒與善惡……在他筆下化身為長篇敘事詩,抑揚頓挫間令人或喟嘆、或憐憫,或起深度思索:「罪」,真能「贖」去?......
白昂妮:
我太老、太害怕、太珍愛我殘餘的這一點點的生命。
等我死了,小說終於出版了,我們這些人只會被當成是我創造的人物......
西希莉雅:
你每分每秒都在我心裡。我愛你,我會等你。
要回來。回到我身邊......
少女白昂妮,由於猜忌與嫉妒,她杜撰了一段故事,讓西希莉雅與羅比這對年輕戀人分離。
羅比入獄服刑,出獄後加入軍隊,赴二次大戰前線打仗。西希莉雅也加入軍隊,在後方支援。
悔恨不已的白昂妮,放棄高等學府,也加入軍隊做了護士,彌補心中對西希莉雅與羅比的悔恨。她用一輩子的時間寫作,試圖在創作中改寫結局。
但文字中的想像情節,又能彌補或改變什麼呢?
作者簡介
伊恩.麥克尤恩 Ian McEwan
生於1948年,英國當代文壇重要作家。
1998年以《阿姆斯特丹》一書榮獲英國文壇最高榮譽布克獎。
伊恩創作長篇小說有:《水泥花園》、《陌生人的慰藉》、《時間中的小孩》、《無罪者》、《黑犬》、《做白日夢的人》、《愛無可忍》(改編電影為「紅氣球之戀」)、《阿姆斯特丹》、《星期六》、《切西爾海灘》與《贖罪》(改編為同名電影,獲多項國際電影大獎)。
他並著有兩本短篇小說集《初戀異想》和《床笫之間》,以及《仿冒遊戲》、《簡單午餐》、《無罪者》等劇本。
其中,《初戀異想》是作者的處女作,獲得1975年毛姆獎。《時間中的小孩》則榮獲惠特布德年度長篇小說獎。
《贖罪》同樣獲得2002年布克獎提名,雖然最終未能如願獲獎,但評論界卻給予它比《阿姆斯特丹》更多讚賞,認為此書比《阿姆斯特丹》更飽滿,更好讀,既有討好讀者的動人情節,又不乏色調。
譯者簡介
趙丕慧
輔仁大學英文碩士,現任教於朝陽科技大學。譯有大田出版《非你莫屬》、《怪盜莫倫西》,與《少年Pi的奇幻漂流》、《戰地琴人》、《穿條紋衣的男孩》、《最後一場畫展》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