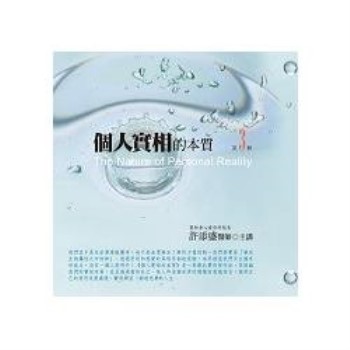這裡的每個人都困在深藍色的潮濕的空氣裡,
他們在內心深處掙扎,在愛與被愛的脆弱中,
想要逃離寂寞,卻一次又一次跌進更深的孤獨……
一到八月的下午,街上空盪盪的,塵土飛揚,白茫茫的一片,天空亮得跟玻璃一樣……
整個小鎮寂寥悲傷,冬天很短,冷得皮綻肉裂,夏天刮的風,酷熱乾燥,耀眼發燙,但在這遺世獨立的小城裡,愛蜜莉亞小姐與來歷不明的駝子表哥戀愛了……
誰也想不透這愛情,究竟是怎麼開始的?
雖說任何一場戀愛的價值與質量純粹取決於戀愛者本身,但街上紛紛傳說愛蜜莉亞小姐餵養的是寂寞的愛情,她釀的烈酒是苦的,卻能夠將隱藏在黑暗心靈的秘密解讀出來,可這熾熱的火苗無法燒盡寂寞,卻燒出比死亡,更憂傷的結局……
20世紀美國失去了一位最具影響力的孤獨獵手──卡森.麥卡勒斯。
她一生創作主題都圍繞在即便最深切的愛也無法改變的「孤獨」。
她不但是幾代人的偶像,從錢鍾書到蘇童,從文藝青年到美國媒體名人歐普拉,她的作品以愛的荒謬來印證孤獨的必然,她說,人的靈魂因為無聊而腐朽,直指人所改變不了的原罪,正是自我內心所深藏的,揮之不去的孤獨之魔……
「……我不禁要說,什麼叫人物,什麼叫氛圍,什麼叫底蘊和內涵,去讀一讀《傷心咖啡館之歌》就明白了。」──蘇童【知名作家】
作者簡介
卡森.麥卡勒斯
卡森.麥卡勒斯一九一七年生於喬治亞州哥倫布市,年少時展現出鋼琴天份,十七歲即到紐約市的茱麗亞音樂學院註冊,卻籌不出學費,無法入學。改而進哥倫比亞大學念寫作,催生了《心是寂寞的獵人》。這本小說讓她一夕成名。
她身體孱弱,成年之後即經歷過數次中風,三十一歲左半身癱瘓,有一陣子只能以一指打字。據她姐妹說,在她過世前數年都無法伏案寫作。一九三八年她嫁給了美國陸軍下士詹姆士.李維.麥卡勒斯,但以離婚收場。離婚後兩人仍通訊不輟,嗣後又再結婚,終於在一九五三年分手;他後來自殺身亡。
麥卡勒斯二十幾歲已是作家,二十三歲出版了《心是寂寞的獵人》,聲名大噪。其他作品有一九四一年之《金色獨眼中的倒影》;一九四六年之《婚禮成員》(贏得一九五○年紐約書評人獎,並改編為舞台劇,搬上倫敦皇宮劇院);一九五一年之《傷心咖啡館之歌》;一九五八年之劇本《美妙的平方根》;一九六一年之《沒有指針的時鐘》;一九六四年之《甜似酸黃瓜,乾淨如豬》;死後於一九七二年出版《抵押的心》。
她在美國境外受到矚目之前,就獲得英國小說家暨評論家普利契讚賞是「無與倫比的說故事人」。小說家格雷安.葛林說:「麥卡勒斯小姐還有福克納先生是繼D.H.勞倫斯殞落之後唯一具有原創詩情的作家。我更喜歡麥卡勒斯小姐,因為她寫得更清楚明白;和勞倫斯相比,我也更喜歡麥卡勒斯小姐,因為她不傳道。」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年方五十,在紐約州尼亞克去世,隨後也葬於此地。
譯者簡介
趙丕慧
輔仁大學英文碩士,現任教於朝陽科技大學。譯有大田出版《非你莫屬》、《怪盜莫倫西》、《珍愛人生》、《投降的勇氣》,與皇冠出版社《少年Pi的奇幻漂流》、《戰地琴人》、《穿條紋衣的男孩》、《最後一場畫展》等書。


 2010/04/30
2010/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