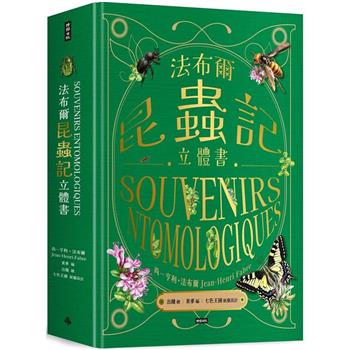我們要堅強,我們不能讓生命能量流失,因為我們是這樣的固執而真心。
老天會看顧我們,看著我們把曾經的信念找回來。
我從來沒有停止過寫字,不管以何種形式。
我寫,因為想誠實面對自己。
躲在謊言中可以是那麼安逸,甚至是一種幸福。
但為著那顆仍在跳動的心,我願意再咬牙試試,
再勇敢一點,再往前走一點,
再誠實一點,再自由一點,
再寫一點……
★各方推薦~
劉小姐謙遜,尊稱我老師,我當然不配。她的才華遮都遮不住,匆促間文字裏的幾粒沙石來日她更成熟了不難幡然省悟,我沒有挑出來,怕她下筆多了一層負擔,礙事。劉若英忙中還寫得出那樣好的作品,我這個老頭兒怕她分神分心,老想學她筆下的張叔在電話裡告訴她說:「家裡都好,家裡都好,你放心,你放心!」
──董橋
在這同時,我看到了別的,我看到了妳那驚人毅力的努力和妳的勇敢,在面對別人型塑妳時掙脫的勇敢,在隨時都在探索自己可能性的勇敢,在光鮮華麗的演藝圈努力做自己的勇敢,在大江南北獨自奔波而努力把自己的路走好的勇敢。還有,妳的誠實,它讓妳很帥,愈來愈帥。
最近跟妳合作時,不只是當年那個愛唱歌的奶茶出現了,而是多了一份堅定,一份自信,還有好多的美麗的全新奶茶。
那古靈精怪是完全沒變的。
──伍佰
【自序】
謝謝你
我從來沒有停止過寫字,不管以何種形式。我寫日記、寫信、寫傳真、寫伊媚、寫官網……一直在寫。為什麼呢?我從來沒認真想過這個問題,但每次到了要出書,回過頭去檢查那些「字」,我又不得不重新問自己。為什麼呢?
我顯然不是作家,這過往已再三聲明過,不會把自己的書寫習慣稱為寫作。我會因為感動寫,會因為寂寞寫,會因為談戀愛、會因為失戀寫,以及最重要的,我會因為想誠實面對自己而寫。
除了演藝工作提供的特殊經驗,我寫的都是平凡人的事,我寫家人、朋友、回憶、生活……。但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寫不下去了。因為自己不美好了,覺得這個世界不美好了,實在不願把那些消極悲觀的情緒再複製出去。我既不是專業作家,也不以此為生,那寫不出就不寫了吧。
奇妙的是,還是有本劉若英的書要出現了。如果,你想在這本書裡找到延續過去的浪漫?你會失望。如果,你想在裡面一探我情感私密,你會失望。但,如果儘管如此,你還是願意往下打開這本書,你會看見我仍在跳動的心。
我寫,因為想誠實面對自己,但有時候那是多麼不容易,甚至比欺騙別人都難。躲在謊言中可以是那麼安逸,甚至是一種幸福。但為著那顆仍在跳動的心,我願意再咬牙試試,再勇敢一點,再往前走一點,再誠實一點,再自由一點,再寫一點。
謝謝你!
作者簡介:
劉若英
唱過一些歌 有紅的 有不紅的
演過一些戲 有好的 有不好的
出過幾本書 都是誠實面對自己的字句
感覺做過很多事情 卻仍感覺不足夠感恩生命
文字作品:
一個人的KTV
下樓談戀愛
我想跟你走
◎【官網】 我的不完美
章節試閱
張叔
「張叔病了」,婆婆在電話的那頭說著。
不知道為什麼,我聽了竟覺得「應該沒事」。為什麼?是因為多年來張叔不管什麼病痛,都能很快好起來?是我心裡的張叔從不生大病?又或者,我打從心裡不允許他生病,不能接受他也會離開……
過去幾年來,身邊的老家人一個個都離開了我,我該有些心裡準備的,但……但他是「張叔」啊!他是老家人裡頭最年輕的,也是家人中唯一一個、我認識的時候還是一頭濃密黑髮的。我印象中,他會出狀況的只有牙齒,掉了好些顆也不補,就這麼齜牙咧嘴的笑,像是點綴性的帶點風霜痕跡。
張叔十四歲跟我們家結下不解之緣,那是我出生前二十年。聽祖母說,他小時候家境非常困難,非常瘦,皮膚黝黑黝黑的,常常到我祖父在南京的辦公室門口溜達。蕭副官見他相貌端正,想收留他,就讓他來當小小傳令兵!就這樣,小屁孩一個,被理了寸頭,握著比他還要高的槍桿在我祖父家門口站崗,一排整齊潔白的大牙吃吃露著,笑著。可以想像當時的他,對這一身行頭和歸宿充滿了期待。每天每天精神抖擻的……。祖父撤退到台灣,他也就順理成章的跟著來了台灣,從此以我家為他家。
從大陸到台灣的男丁裡,他是當時唯一還沒娶親的。但一切都遵循著「老芋仔」的套路走,他在台灣娶了個本省媳婦。由於祖父不再涉足軍政,不需維持排場,家裡不用那麼多人手,祖父鼓勵還年輕的張叔應趁此機會多讀書,不能一輩子都只是一個傳令兵。張叔從此奮發學習,靠著自己努力考上公路局,當了一個公務員。這期間,他生了兩個兒子,兩個女兒,一家人非常和諧的生活著。他的家人並不常出現,就是在年節時,張叔會帶著大大小小一起來拜年。記得小時候看見他兒子時我還會害羞,因為他兒子跟張叔長得很像,瘦瘦高高,相貌堂堂。
雖當了公路局的公務員,張叔每天還到我們家。有時是早上上班之前來看看,下班有空也會來幫忙,大約他覺得自己有兩個家。到他從公路局退休下來,他在我家的服務又從兼職恢復成全職。這時張叔已經六十多歲了,平頭已經泛白。
總騎著一台漆成螢光黃腳踏車的他,說這樣比較安全。也是,常常天沒亮就出門,怕大車看不到他。當我自己有了收入,買了一台單車送他,第二天就發現那車全身已被漆成螢光黃。我簡直崩潰,問他「我還為了買那個顏色挑選了半天……你為什麼不乾脆自己全身穿個螢光黃算了?」
年輕如我不懂珍惜生命,不能體會時間流逝的急迫感,直到親人不再理所當然地圍繞身邊。有一回祖父參加完朋友的追悼會回來,心情不好,我覺得莫名其妙,張叔跟我解釋「你祖父坐在下面,應該會想,坐在身邊的人越來越少,很快也會輪到自己……」祖父晚年的神志不太清醒,祖母的年紀也不小,扶不動祖父,我們請了菲傭照顧。當時擔心的是,張叔跟菲傭、菲傭跟祖父,一個口齒不清的湖南話,一個菲律賓英文,一個南京話,要怎麼溝通?但三人發明了只有他們聽得懂的共通語言。祖父的最後兩年,菲傭也敗下陣來,祖父的吃喝拉撒就全靠張叔一個人。有一回過中秋,祖父坐在輪椅上,大夥吃飯,喝點家鄉的甜酒助興,張叔說,祖父也說要一點,我自以為懂事的把白水倒進酒杯,心想祖父反正也分不出是酒是水,張叔立刻說「你公公肯定會知道!」我不信。祖父才一沾口,立刻說「張育才,你騙我……這是水……」。看來張叔比我了解祖父,或者說,他比任何人都了解祖父。
他對祖父雖必恭必敬,也有跟祖父鬧彆扭的時候。祖父是老軍人,說話嗓門特別大,說氣話就更大了。有回兩人為了什麼起了一點爭執,我祖父氣著說「張育才,你明天不要來我家了!」第二天,都到七點了,張叔果然聽從將軍的指示沒有出現。祖父嘴裡不說,但是一直在房裡走來走去,最後終於罵罵咧咧的「簡直反了,報紙到現在還沒有來!」祖母偷偷打電話到張叔家,張叔的太太接的,她當笑話說「老張啊,一早就穿好衣服坐在客廳,但就是不出門,不安的起起坐坐的,剛剛終於坐不住,出門啦!」說時遲那時快,大門有聲響,接下來就是一雙手捧進了當天的報紙。我跟祖母偷著樂,就是張叔跟祖父倆跟沒事人一樣。
祖父臨終時,張叔堅持親手為他擦拭身體,像是在跟自己的大半人生告別。這樣的兩個人——老將軍跟傳令兵,沒有血緣、沒有債務、沒有合約,憑的就是相互的感念。祖父應該是個講情份的人,以致他帶來台灣的部下始終不離不棄。祖父有付出,也獲得更大的福報,可見階級矛盾並不能適用所有情況,尤其是軍人。
每年上山幫祖父掃墓,必須帶上張叔,只有張叔找得到那條崎嶇的路。上山時,他除了鮮花,香,紙錢,還帶上一個自製半圓形的鐵網,說這樣燒起來又透風,灰絮也不會飛得到處都是,然後自顧自的開始跟祖父報告:「英英來嘍,她來看你嘍,太太都好,你放心啊……」。儀式結束,他不忘幫安息在我祖父身邊的幾位朋友掃掃地,弄弄花什麼的。彷彿受了他的體貼啟發,我會開玩笑說,你要請這些鄰居多擔待,祖父的脾氣不太好。
祖父離開之後,老家人只剩下張叔,他依舊堅持每天來家中招呼祖母。長年在外地的我打電話回家,只要是張叔接的,他總不斷重複著「家裡都好,家裡都好,你放心……你放心……」。的確,我也總因為他這樣說著,更加放心在外遊蕩。我知道,劉家大到存款,小到洗手台的螺絲釘,張叔叔都會一肩挑起,任何時候我回家時,他會一如以往的迎接我。
那幾天台北雨下個不停,整個城市浸的發霉。正在路上這麼想著,祖母來電話說,「張叔病了」。我真的從來沒有想過張叔也會真病。他不是最年輕的、髮絲烏黑的那個嗎?他不是每天游泳、健步如飛嗎?他不是一路背著蕭副官回大陸探親,還一路背他回來的嗎?他不可以生病,他生病了我們怎麼辦,祖母怎麼辦?這就是自私的我當時問的問題。
但是,他確實病了,祖母說。他太太也說,他不愛吃東西了。當時正趕著唱片宣傳通告的我,想去看他,祖母跟他的家人都勸阻,「張叔不放心你去,樹林很遠,下一趟,下一趟吧……」,要不就說怕我找不到路。就這樣,我失去再見他一面的機會。這是我的莫大損失,不是張叔的。
我終於去了他家。的確有點遠,不好找,但這也是這麼多年來,他每天每天出門來我家須走的路。也沒聽他提過遠,就這樣一趟一趟的,一趟一趟的幾十年來如一日……那條巷子,確實很窄,他確實需要螢光黃來保護他。我爬上了四樓,迎接我的依舊是那最燦爛的微笑,只是那微笑已被凝結在黑白相框裡。他家的氣味跟我家一模一樣,因為兩個家都是他打理的,都是他的家。我跟姐姐向他磕頭,姐姐念著「謝謝張叔您這一輩子為我劉家做的,你終於可以放假了……你安心吧!」說好不哭的我,一句都說不出來,只能啪啪啪的掉著眼淚。我除了難過,還有說不出的生氣……
跟他太太兒子聊天,我抬起眼來,玻璃櫃裡有一張有點眼熟的相片,我走近一看,是張他從報紙上剪下來的剪報,上面是多年前我去高雄慰勞海軍時,跟官兵合影的照片。他將它框了起來,放在顯眼處。小英英長大了去勞軍,想必對他有非凡的意義。這又讓我想起,我好像從來沒跟張叔好好合過影,永遠都是我們忙著要照相,把相機往他身上一丟,自顧自的站定了姿勢。而張叔,永遠都藏在鏡頭的後面,維繫著我的家,照顧我們一家人。他十四歲到我家,此後陪了我們六十多年。
他的太太這麼說著:「他這一生永遠把劉家放在第一位,再來才是自己的家人。每年的年夜飯,他都是招呼好劉家,才願意踏上歸家的路……」。張太太說時語氣淡定,不含悔怨,像是她充分理解並欣賞先生的先人後己。看來張太太也是張叔的福份。
離開張家時,我在樓梯間見到了我送的那輛腳踏車,螢光黃已成了墨黃。顏色再也沒能保護好我的張叔。
今年清明,我又想上山去看我祖父,拿起電話,才驚覺張叔已經不在了,有誰能再引領我走上那條慎終追遠的路?他是六個老家人中,最後一個離開的,他的離去,對我而言是一整個世代的結束——一個只問付出不求回報的年代,一個把忠誠視作基本教養的年代。他們對祖父,就如同祖父對民族和國家。祖父,連同老家人,前後陸續離開了我。從此我益形孤單,生活中少了活生生的典範,我只希望,他們的氣節永遠伴隨著我,留存在我的血液中。我只希望,祖父,張叔,易,蕭副官……,他們鮮明、巨大的形象,會在我無助的時候,在我抬頭處出現。
張叔 「張叔病了」,婆婆在電話的那頭說著。 不知道為什麼,我聽了竟覺得「應該沒事」。為什麼?是因為多年來張叔不管什麼病痛,都能很快好起來?是我心裡的張叔從不生大病?又或者,我打從心裡不允許他生病,不能接受他也會離開…… 過去幾年來,身邊的老家人一個個都離開了我,我該有些心裡準備的,但……但他是「張叔」啊!他是老家人裡頭最年輕的,也是家人中唯一一個、我認識的時候還是一頭濃密黑髮的。我印象中,他會出狀況的只有牙齒,掉了好些顆也不補,就這麼齜牙咧嘴的笑,像是點綴性的帶點風霜痕跡。 張叔十四歲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