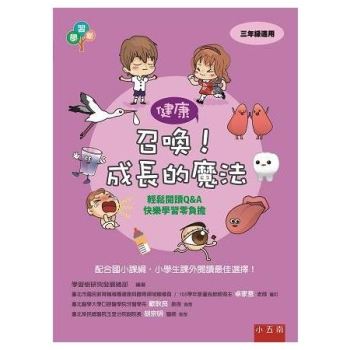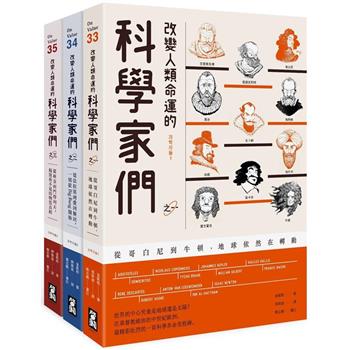卷壹 她們醒來歌唱
0.
聖母沙塵暴駕臨了。
聖嬰熱浪也在前方。
尖厝崙是她的村莊。
名字由來她們從未去探索過,她們無視歷史,也不畏懼歷史。不為任何歷史洪流存在的她們,一如墓誌銘不因石頭而改變其內涵。每個女人都是夏娃,世界以她始,以她終。在之前之後,在永不回歸的時間,許許多多的她是第一人也是最後一人,感性的女報信者,帶著傷痕奔赴述說的路途。
有一頁書等著被翻開
1.
島嶼南方的日子開始在他們都還很年輕的時候,時間流逝還沒有清楚的刻痕,物件稀有,感情也稀有。番界不遠,寥落熾盛。南方的日子不好過,起先是苦熱蠻雨,惡寒酷旱讓他們煩躁,還有疾疫纏綿,神出鬼沒山民,溪流、石塊、蘆葦、焚風、濕氣、暴雨、波濤、森林……有不明白起於何處卻又難以擊退的孤寂,足以吞沒肉身的許多事物都讓他們敬畏。他們的腰際多插有刀,開路防身,刀柄上飾有鬼頭,鬼頭好腥,刀力無窮,開疆者手染紅血,行人至此斷肝腸。
遼闊無盡的平原山野予他們人生幻想,舞天舞地,冶遊山海,四處風光。只是一到黃昏,日落地平線深鎖他們滾燙的目光,另一端的家園已然化成霧中風景,凝結成一封封家書,家書從沒寄至這鬼界之島,黑水染字,只餘相思。連問鸚鵡思鄉否?都說思鄉。羅漢腳豈知日後荒島上的這山這水,日後他們再也行不出它的天它的地。
偶爾被急流送來沿岸的漁舟稍來了鄉音,漁舟裡的彰洲人下船就說,暈死了,這輩子沒搭過船,生目珠沒見過海洋啊。太平洋的藍眼睛,原來如此深沈,如此遼闊。詔安客山城久居,沒聞過腥臊,沒見過大藍,沒嘗過海味。當捕魚者釣起第一尾魚第一尾蝦時,他們望著陽光下魚鱗搖曳出的水滴與蝦綻出如燕寶石的顏色時,他們想奔赴此島是對的吧,他們直接生吃活吞生猛蝦魚,很多年後他們髮禿齒搖了才知道阿本仔叫此沙西米。惡土前方有海洋洶湧,雖然他們不懂海,不懂藍下還有多藍,一如他們都還鮮嫩不懂女人,但他們目目相覷,知道雙手雙足是碇錨於此了。下漁船的人有的飛快赤足奔向海,有的彎身捧起一把沙,有的把臉浸在水裡,再仰起頭時臉上如畫了黑線,盡是海藻護膚。萬事待命名,跟著山民喚,或有竹叫竹圍,有圳名公圳,有丘稱崙,有房為厝。
舒家人又愛又懼的藍眼珠人曾經悄悄站立在這片寸草不生的島嶼沿岸惡地,說是惡地,這實是污衊。實則歐洲人早已帶走他們要的東西,歐洲人在此島的遺址不在建築,而在島民的臉上。鍾家某房太祖婆的臉白晰至看得見血管流動,那種近乎透明的白啊,他們不曾見。直到後輩子孫尋訪舊史方知血緣被紅洋番「透」過,透者混也,透即驂雜。不是白得看得見血管,要不就是黑如生番。
黑白混色譜系日漸在海的烘焙下已失去了原有色度。東印度公司揚帆的艦上夾雜著歐洲各國的逃亡者、偷渡者、失意客、囚犯,他們被這家以糖為暴發戶的公司分送至地球惡土上的許多角落,有人發現了哈得遜河,有人發現了金礦,有人發現了航線,有人發現了森林,有人發現了新大陸,有人發現了愛情……日耳曼人和某少女,那一夜發生什麼事?強行,或者柔順?無人知曉,但他們都知曉異鄉人要靠幻想與非法求生。捉摸不定的血統,解析出的成分卻不怎麼光彩。他們起初以為人生要有未來必須不讓「過去」靠近,但直至幾代過去了,才發現這一切徒勞。她們唱起祖婆在雷雨降下的陰暗閨房之歌,那奇異的聲調,不識字的這一代女子一直都沒搞懂祖婆唱的歌詞,她們記得了聲調,最後才知道原來是「身穿花紅長洋裝,風吹金髮思情郎,想郎船何往,音信全無通,伊是行船堵風浪?放阮情難忘,心情無地講,相思寄著海邊風……」有人羞怯一笑,對著行過的金髮傳教士,心想原來是放阮情難忘,而不是放阮眾人摸,情難忘與眾人摸,閩語同音,意義竟是天差地遠。藍眼睛,自此成了鍾家某一房的顯形與隱形封印。藍色河流愈流愈淡,不斷被海洋與山城子民的紅血刷淡了她的色澤,但光度卻愈刷愈亮,那鍾家後代目光常焚燒他者。小心和別人的眼睛對望,小心以愛之名的騙徒,鍾家查某祖流傳給後輩女人的祖訓之一。
2.
隨著漁船來的漢子佇立海洋時,其中的鍾郎遇見藍眼睛白皮膚少女時心生蕩漾,他尾隨她的腳步來到了更遠的異鄉部落,鍾郎在山豬的叫聲裡聽見了體內的春雷巨響,詔安從此成了後代陌生的追想曲。他們不知身世來處,常笑厭惡客人。就像被山民擄去的漢嬰,日久將視漢為仇。思鄉鍾郎的掙扎與相思隨夜而來,寂寞鬆動了堅強。晚上,鍾郎彈著古琴,讓老音囈語在新築的牆,悲傷的琴音使整座平原的稻米與甘蔗加速生長,白日眼見稻穗滿滿,眼見甘蔗滲出糖的氣味,他們遺忘了生活如此艱苦,遺忘了夜晚那去而復返的喫心相思。在這樣的南方生活,要懂得收攝與解放,開疆闢土者從來都有奇異的人格,不安逸的南方,恰好是他們流血流汗的濕樂園。黃昏時光,走向海洋的漢子,甩動著如尾的辮子躍入水中涼快。
那時他們還不認得這裡的許多生物。當鋤頭往土地一掘時,他們期待挖出黃金般的沈船古物,或者像大陸那些沈湮幾代人的古墓寶物。但這些傳說還不曾發生在這塊他們眼中的新大陸,他們掘起了泥土,跪下去聞著新土新地的氣味,幾乎是流淚的。漢子跪地此舉,惹得來送便當的女人家以為土地會咬人,把他們的漢子臣服了。
她們走近,發現土地爬出許多生物,煽動濕黏的翅膀後,牠們頓然飛上枝頭。那時她們都仰頭,但已未見,僅憑尋聲遙想一整個盛夏。蟬聲嘶鳴在最初一刻的夏宴中,村中人才意想到這是落腳這座島嶼第一次聽聞蟬聲,蟬聲讓夏日烈陽的幻覺變濃了,蟬聲彷如讓日頭拉長了影子,朝莊稼漢頭頂猛猛射去,炎熱氣候曬傷了屋子的色澤,曬螁了如深海的藍衫,白褐色鳥糞沾黏在紅磚上,四處熱塵紛飛,汗水淋漓,這激昂的分貝燃燒著溫度,讓漢子們捲起褲管,坐宴溪水裡,大口啖著生平在此的第一個收成,焚風過後的西瓜,甜蜜如夜晚的高潮,他們忘了黑水溝的那些黑風黑浪,直認此島一方是新天堂。他們的媽祖跟著飄洋過海,媽祖在岸上笑著,黑黑的臉彷彿也十分熾熱,黑檀木光亮聖潔,照亮整間矮厝。
在西娘的回憶裡,彼時台灣厝,窗子小如瓦片,驚怕土匪來。
直到蟬聲嘶鳴在最後一刻的秋決後,村中人感受到季風的冷冽,婆子們學織棉衣抵風,入甕釀酒,夜晚到來,從溪口一路灌進薄屋的烈風,使他們迫不及待地打開尚未釀透的酒甕,那時他們心想難道自己要老死在此?失望瀰漫在他們如惡兆般的夜之蒼穹下,他們失眠,他們俯仰在一張張輪廓深邃、陌生而美麗的臉龐之上,黑髮如瀑如森林,他們循女人的黑水溝一路挺進,喉頭發出蒸汽似的熱空氣,如火山擴散的熔漿,直至熱汗驅逐了冷風。頹然倒下的漢子們,在黑暗的霉味裡,聞悉豐收也目睹災難,往後迎接他們的不再是蟬聲,而是黑水溝裡被吐出的綿延啼聲。那些高低不勻的啼聲啊,才是把他們的命運牢牢釘在島嶼的骨血十字架。命運的軌道已然偏離,命運要彈回原樣近乎不可能,日子只能往前奔去。
3.
番婆好牽成,唐山公娶唐山媽。成年平埔女兒住籠仔,此番語稱貓鄰裡,即姑娘房。野性查某祖,若有喜愛的男子行經,她即可在房前吹口簧琴示愛。她喜歡就讓他住一夜,不喜歡就把他丟出去,再選另一個她喜愛的人。
這野性逐漸被他者馴服而消失,她們喪失了本能天賦,直到她們的肉身埋到了地底才看見命運的掌紋,愛情線上多軌而單薄,婚姻線單一而分岔,但什麼都來不及了,她們注定一個男人終老,即使意念裡不知攀爬過多少高峰巨柱。孩子無法塞回子宮去,時間無法重返。年華老去的女人們懊惱什麼叫愛情什麼是人生都不明白,日子已然過了大半。她們想如果早知道時光會一去經年,她們不應該閉上眼睛,她們應該在微光中牢牢地盯住每一個時刻,每一個細微的表情,每一個扭曲而即將渙散的夜慾。島嶼的深淵是沒有永恆這種撫慰人的神話,只有戳痛人生的時時刻刻。在命運的天空下,她們並不哀傷,只是突然想大聲吶喊,已百年了啊,該死啊,竟已百年了,時間像鱒魚游海,快速地沖刷而去。
這座美麗島,生養夢想,即使流犯至此,亦不再聞腳鐐的聲響,他們只看見一片黃金稻穗。曾經連續多日多月的的大旱災早使得腳下的土地龜裂,連草都枯萎。有人想起他們心中的貞節媽,到廖家請出貞節媽神主牌。將神主牌置於旱地中央,對天乞雨。天空移來烏雲,如日蝕,黑光蒙地。他們聽見雨,雨先落在貞節媽的神主牌,滴滴落落,如泣如訴,接著雲塊綻開縫隙露出藍色光芒,劈下一道閃電雷光。大雨傾盆,佇立旱地的農人微笑著用手用臉用嘴去承接雨水,快意雨水。貞節媽一生乾燥,如注之雨倒像是哭訴她一生荒瘠的淚水。貞節媽終於潮濕了,在三合院廊下觀雨落下的女人則這樣地想。眾農民集資金錢給廖家人好讓他們著手整修廖貞節媽已漸殘破荒蕪的墳墓與墓碑。水利會向地主鄉紳提議修建一貞節牌坊,貞節高高懸掛,擺盪在亙古寂寞陰風裡。(後代少女小娜日日穿過廖媽貞節牌坊下,感到自己極為不貞不潔,後來她都繞過貞節牌坊,一腳跳過崁柱,寧願走玉米田小徑,冒著掉落溝圳的危險。那是一個她無法想像的世界,但那個世界卻在她的心中,徘徊不去。)
春宵吟
4.
嘉慶、光緒、大正、昭和這種字眼在當代的台灣人眼中已經漸漸消失了它本身所具的時間象限,年輕人見到這類字眼將迷航在無所知的年代裡。
那個年代到處有「崙」「墘」「塘」「厝」命名之地。
一到這小村路口,往下看見的是芒草旁的石敢當,抬眼風光是茄冬樹芒果樹楊桃樹和龍眼樹,一排頭歪向東北長的木麻黃。風送來屎尿臊味,欲落未落的茅廁木門外盤旋著蒼蠅,陽光撒落在長了草的村莊屋頂紅瓦,他們想自己這個肉體有一天也會和這祖上蓋的老房子一樣,終有一天埋到地底後,頭上也會長草。那麼多年了,這村莊日漸有先人被埋到地底,春風草長,那時還沒有火化這件事,樹葬海葬未聞。土地包容一切生息,包括人身盡頭。
尖厝崙是她們的村莊,註生娘娘與死神同住於此,土地公婆守候出入口。她們以為台灣很大很大,大到一生也走不完看不盡。她們大部分人都沒有離開雲嘉祖厝,除了結婚那一天之外。有時候她們光是離開村莊到鄰近的鎮上就要花上好幾個小時,到大城市那可是要一天一夜,於是當男人說起台灣這塊蕃薯時,女人以為台灣就是所謂的世界,此即是天地盡頭,即是一切。
小村日夜是以身體為節奏,疲憊後好入夢,她們覺得夢很可怕,醒來後,她們的肚子不斷地大了,孩子開始爭相擠出下體的黑暗岩壁,人間啼哭。光陰以日晷、沙漏、線香、燭刻、香印、雞鳴、腹叫來告知她們該打開灶門好炊煙了,或者抬頭看一眼太陽,日久每個持家的女人都有自己所屬的計時器。就像她們的人生從來都不是那麼精準,糊里糊塗就隨手把人生翻了頁。
那時查埔祖上起的家厝,窗小,門小,樑低。野草四長,土匪打劫,六親不認。公媽神主牌還沒出現在楊枝淨水菩薩的案上,因為公媽都還年輕,還沒想到死亡,更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化成了一小片木板,上有三魂七魄。
男渡海者正生猛,也以為自己有朝一日會攢錢離開這島,生命荒瘠裡的外遇之島,他們熬過瘴癘熱塵烈風,熬過不同族群的廝殺,還熬過雙人枕頭的吵鬧不休,熬過異族屈辱,最終他們還是留下來了,且這一留,百年已過。
古早苦日子,卵葩乎人掛(割)去也無知啊,男人哈菸說。死神如影隨形,虎列剌、百斯篤、赤痢、疸瘡、發疹窒扶斯、格魯布……,這些奇異的日語是當時他們耳熟能詳的死神代號,每一個疾病都會將他們與所愛或所恨分離。霍亂鼠疫痢疾天花斑疹傷寒白白喉……,他們在死神漸漸遺忘他們時,偶爾憶起某日為了哪隻老鼠是誰抓到的吵得面紅耳赤而感到玩味,一隻老鼠換得一毛,誰也不想讓出這珍貴的一毛。鍾家漁觀古早有一陣子被叫三毛,因為他每回換到的錢都是剛剛好三毛。這些往事說來不到百年,但眾人回憶起來卻像是很久遠的事了。
5.
落戶於此,那時沒有外省稱謂,當然也沒有本省不本省的,唐山過台灣來的後代子孫烙印血緣地名在門上,他們口中的假黎、山番是當地居民。那時各省口音交錯,有人叫祖母為婆婆,第一個婆字三聲,第二個婆字二聲,婆頗也有叫奶奶的,或者叫姥姥、阿婆,阿嬤。鍾家逐漸在閩客械鬥與長居閩南村落而幾代後逐漸失去了母語,僅有些稱謂還是客語,但泰半已操閩南語。他們叫祖母阿媽,祖媽與公媽。孩子們也都喜歡這樣的叫法,說是帶了點鄉野氣味。阿媽已轉音成阿嬤。鍾家查某祖們喜歡被人叫伊阿嬤,即使她們早已是太祖婆了。
許多很老的老人到現在都還記得鍾家那愛賭博(博筊)又愛呷昏(抽菸)的阿嬤,她本來是個標準的美人胚子,結果被阿本仔抓去關在矮牢裡後,久了不能站直,出來後竟成了個駝子,野孩子在背後學她孤(駝背),常惹得鍾家祖上善拿棍子打人。被打的野孩子就是在廟埕述說往事的老人了。呷菜阿嬤曾偷偷夜裡對男人上善說伊就是前世因為在佛前禮敬姿勢不夠謙卑,我慢太盛故日後有駝背之果。上善原本在寬衣解帶,聽了倏地又穿上外衣,扯開門簾竟至離開呷菜阿嬤的房間,丟了一句話給她說我不懂因,也不懂果,但如是因如是果,妳也別出口。男人討厭是非,不管是或非,女人少說他人為妙。這是唯一一次溫順的呷菜阿嬤惹她的男人不悅,她那夜一人躺在紅眠床,望著床的雙魚雕花,明白有些話是不能說的,尤其關乎因緣。但她常忍不住說起自己看見的未來畫面,有一回她就說著當鐵鳥飛上天,鐵線會說話,女人就逐漸自由了。大家悶聲吃飯,習慣呷菜阿嬤常吐出怪語。直到有一天當鍾家裝起村裡的第一支電話,在摩西摩西裡,才恍然想起呷菜阿嬤說的鐵線就是這個玩意啊。而鐵鳥就更不用說了,美軍轟炸台灣時,村人都恨死那在天上朝射地球亂射子彈的鐵鳥了。
村裡的人曾繪聲繪影說庄裡也有個查埔郎因為抗日被抓去關,這個姓廖的,關了六、七年出來,鬍鬚都長到胸前了。大家都覺得說的人也未免太澎風了,那裡知道還有人接著說這哪有什麼啦,接著壓低聲量說,鍾家呷昏阿嬤走出牢房時陰毛都長到膝蓋了。不管鬍鬚或陰毛,鍾家人稱呷昏阿嬤的高祖蹲過牢房卻是真有其事。
有時聽到這個傳言的查某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傷歌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87 |
小說/文學 |
二手書 |
$ 23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66 |
小說 |
$ 300 |
現代小說 |
$ 300 |
中文現代文學 |
$ 334 |
中文書 |
$ 334 |
小說 |
$ 342 |
中文現代文學 |
$ 342 |
小說 |
$ 342 |
現代小說 |
$ 34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傷歌行
島嶼百年三部曲,重返鍾文音心中的島嶼野性
這流逝的百年時光,
男子,有殤;
女子,有傷;
島嶼,有慯……
在原鄉,鍾小娜站成了一個弧線。
往前凝視,她看見了早逝男人的壯志未酬,孤寡女人的唏噓凋落。
往後張望,她看見了離鄉遊子淚汗交織的機械生活,無根,漂流……
她在每一個眼眸裡,
看見閃爍著生命哀愁與荒謬際遇,隱喻的吉光片羽。
她將那些人的滄桑碎片,俯身一一拾起。
以虛實交錯,深情凝視……
身體的野性──《豔歌行》
土地的野性──《短歌行》
感情的野性──《傷歌行》
島嶼百年三部曲,重返鍾文音心中的島嶼野性。
作者簡介:
鍾文音Wen-Yin(nina),Chung
淡江大學大傳系畢,曾赴紐約視覺藝術聯盟習油畫創作兩年。現專職創作,以小說和散文為主,兼擅攝影,並以繪畫修身。長年關注家族寫作、愛情等題材,並熱愛旅行。持續寫作不輟,已出版短篇小說集、長篇小說及散文集多部,質量兼具、創作勃發。
被譽為九0年代崛起之優秀小說家和散文家,曾獲中國時報、聯合報等十多項全國重要文學獎(1997-2000),2002年台北文學創作年金,2003年雲林文化獎,2005吳三連獎、第一屆林榮三短篇小說獎暨散文獎。
2006年出版的長篇鉅作《豔歌行》,一出版即獲2006年中時開卷版中文創作十大好書,2008再入圍台北國際書展小說大獎及台北十書。2010《短歌行》出版,入圍台灣文學長篇小說獎,並獲得文建會補助日文翻譯及出版。
鍾文音成立美學網 www.bestlife.tw
鍾文音之驚世花園 www.wenin.tw
鍾文音之中時部落格 http://blog.chinatimes.com/wenin/
◎【特刊】 鍾文音:我熱愛寫作,就如農夫熱愛那塊自己的田地

章節試閱
卷壹 她們醒來歌唱0.聖母沙塵暴駕臨了。聖嬰熱浪也在前方。尖厝崙是她的村莊。名字由來她們從未去探索過,她們無視歷史,也不畏懼歷史。不為任何歷史洪流存在的她們,一如墓誌銘不因石頭而改變其內涵。每個女人都是夏娃,世界以她始,以她終。在之前之後,在永不回歸的時間,許許多多的她是第一人也是最後一人,感性的女報信者,帶著傷痕奔赴述說的路途。有一頁書等著被翻開1.島嶼南方的日子開始在他們都還很年輕的時候,時間流逝還沒有清楚的刻痕,物件稀有,感情也稀有。番界不遠,寥落熾盛。南方的日子不好過,起先是苦熱蠻雨,惡寒酷...
»看全部
目錄
序曲一:南方的十字
序曲二:在原鄉,她站成了一個弧線
卷壹 她們醒來歌唱
有一頁書等著被翻開.春宵吟.寶島香蕉姑娘.墓仔埔也敢去.望春風.男性的純情.送君情淚.阮的故鄉南都.心酸酸.恰想也是你一人.我比誰都愛你.惜別海岸.流浪到台北.希望一點真情意.可憐彼個小姑娘.港都夜雨.艱苦相思.慈母淚痕.雨水落抹離.寄語夜霧裡.舊皮箱的流浪兒.可憐花再會吧.媽媽我也真勇健.望呀望 等呀等.妳著忍耐.何時再相會.補破網.心所愛的人.無情之夢.台北發的尾班車.雨夜之花蕊.假情假愛.中山北路行七擺.離別的月台...
序曲二:在原鄉,她站成了一個弧線
卷壹 她們醒來歌唱
有一頁書等著被翻開.春宵吟.寶島香蕉姑娘.墓仔埔也敢去.望春風.男性的純情.送君情淚.阮的故鄉南都.心酸酸.恰想也是你一人.我比誰都愛你.惜別海岸.流浪到台北.希望一點真情意.可憐彼個小姑娘.港都夜雨.艱苦相思.慈母淚痕.雨水落抹離.寄語夜霧裡.舊皮箱的流浪兒.可憐花再會吧.媽媽我也真勇健.望呀望 等呀等.妳著忍耐.何時再相會.補破網.心所愛的人.無情之夢.台北發的尾班車.雨夜之花蕊.假情假愛.中山北路行七擺.離別的月台...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鍾文音
- 出版社: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07-30 ISBN/ISSN:978986179216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528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